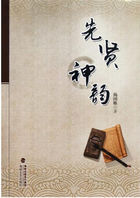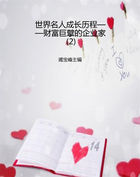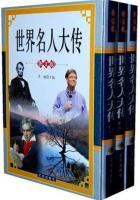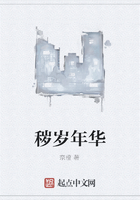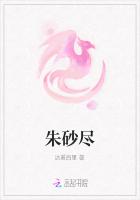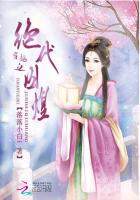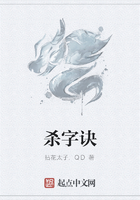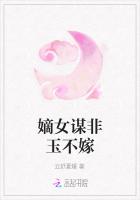李叔同(弘一法师)
在中国现代艺术上的“第一”
1.中国人第一批东京美术学校留学生
1906年,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师从留法归来的画家黑田清辉学习油画。在当时小有轰动,受到当地媒体关注。
2.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音乐杂志
1906年,李叔同集编辑、撰稿于一身,在东京独自创办了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寄回中国发行。
3.最早绘制贝多芬像的中国人
1906年,李叔同在《音乐小杂志》的扉页用炭笔画了贝多芬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绘制的贝多芬像。
4.春柳社: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话剧团体
1906年冬天,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的支持下,李叔同与曾孝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春柳社”在东京神田骏河台的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演话剧《茶花女遗事》,李叔同则以“息霜”的名字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
5.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11年在天津,李叔同应老友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之邀,担任该校绘图员。他大胆创意,将西洋美术理念融入工业产品外观设计,广受好评,成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6.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第一人
1912年,李叔同担任《太平洋报》编辑,亲自设计报纸广告和文案,且负责画报副刊,在上面开设《西洋画法》专栏,以连载的形式介绍石膏写生、木炭、油画等画法。中国的绘画艺术界将李叔同推崇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第一人”。
7.中国最早的现代木刻版画集
李叔同倡导木刻艺术,他和夏丏尊成立漫画会和乐石社,指导学生研习木刻和金石技法。1912年到1913年间,刻印《木刻画集》,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木刻版画集。
8.中国第一堂人体写生课
1914年,李叔同将一位裸体男模带入课堂,开创了中国第一堂人体写生课。这比首次开设女裸模写生课的刘海粟早了三年。
9.创作中国第一首分声部合唱歌曲
在浙一师期间,是李叔同创作了《西湖》,以及中国第一首分声部合唱歌曲《春游》。他还根据自己在日本时非常喜欢的《旅愁》的旋律填词,成了当今传唱不衰的《送别》。
10.最早撰写欧洲文学史的中国人
在浙一师期间,李叔同创办《白阳》杂志,以此阵地广泛介绍西洋文学艺术,撰写欧洲文学史。其中,《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是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关于欧洲文学史的文章。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的原因
被众多大家尊称为“中国近代艺术先驱”的李叔同遁入空门,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实在令人不解。再有的是,他曾对好友夏丏尊表示,只做居士。突然剃度出家,好像一次即兴之作。作为天津富商后裔,一个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近代艺术推广和教育上创下数个“第一”的李叔同,难道出家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场行为艺术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叔同这样一个多才多艺、前途远大的才子落发为僧呢?在大千世界中,人生的取向、人生价值是多种多样的,并非说李叔同成为僧人后,就是他人生前途的终点,只是很多人都认为,与同时代、同类型的人相比,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作为一代艺术先驱,不必选取和他们相同的人生道路。他之所以“入山为僧”,其中必有其他深层的原因。为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考察李叔同的一生,不难发现其最终为僧的蛛丝马迹。
父母亲属之中不乏佛信徒
其实可以这样说,李叔同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佛教信仰浓郁的家庭。他出生的天津河东陆家竖胡同二号,附近就有一个地藏庵,从小就能看见和尚踪影,其声其香,耳濡目染。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字筱楼)虽然是一位儒家门徒,但也信佛,而且还被人们称为“李善人”。就在李叔同出生那天,为庆祝晚年得子,李世珍就买下无数鱼虾,举办放生仪式。此后,每逢爱子生日,他都大办放生仪式。李世珍的这种做法,对孩子造成不小的影响,与其说是庆祝生日,不如说是在感谢佛祖送子,暗示这孩子源于佛门,给李叔同植入了一种佛缘因子。
到了李叔同五岁那年,李世珍突然染病不起,自知寿命将尽,他就提出请高僧到床榻边助诵《金刚经》,在诵经声中安详去世,办丧事期间,灵柩停在家中七天,也是每天有和尚来诵经不绝。年幼的李叔同觉得好玩,还跟着念。此后他时常带着侄儿李圣章等一群小孩玩“放焰火”的佛教仪式,自己披着床单扮演和尚。
李叔同的母亲王风玲,据说粗识文字,笃信佛教。李叔同的大侄媳早寡,生活悲苦。就在他七岁多时,大侄媳向曾到普陀山出家的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李叔同听见她念,觉得喜欢,也跟着她一起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李叔同自小对佛事不但不排斥,还表现出天生的亲近,在日后他再接触与了解佛教时,这些儿时记忆,必定给他形成一种“命中注定”的使命感。
天生佛门根器,性格怪异深感人生无常
从性格上讲,李叔同是一个性格孤僻、孤傲清高的人。他不适应繁复的人际关系,喜欢清静独处,顾一尘在《纪念弘一法师》中如此评价李叔同:一个具有“二重性格”的“极端主义”艺术家。
李叔同一生所用名字甚多,根据他的俗家子弟丰子恺考证,足足有二百多个。除了李同、文涛之外,比较常用的俗家用名还有成蹊、李息、李哀、息霜等,可见他性格中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心性内向的他很少表白自己的心迹,后人无法确知他内心在想什么。当年在日本演话剧,正是春风得意时,因为有人议论批评,他就不再演了。可见其才华高,自视亦高。
与李叔同有过深接触的,都认为他的性格古怪。有一次,李叔同与欧阳予倩相约八点在上野不忍池畔自己的住所处见面。由于欧阳予倩迟到了五分钟,李叔同便不给他开门:“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欧阳予倩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
五岁丧父,不能说没给李叔同留下挫折感。首先,他的生活发生巨变,虽然有母亲看护他,但毕竟是庶出,总免不了一些冷眼和不公。每当他烦闷不开心,能背诵《名贤集》的乳母刘氏就教他读“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的警句。李叔同出家之后曾自述:“七八岁之时,常有无常空苦之感,乳母每戒之,以为非童年所宜。及慈母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蔡冠洛《戒珠苑一夕谈》)
人生中的每一次波折,都会给李叔同留下不小的心灵伤痕。母亲去世时,二十六岁的李叔同悲不自禁,在她的葬礼上抚琴长歌:“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这不似其他的挽词,为仙逝的母亲歌功颂德,更多是倾诉自己的悲痛和孤寂,以此来感亲恩。后来,他向弟子丰子恺回忆起母亲,说:“我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丰子恺《法味》)他的这种哀愁,与其说是对母亲的依恋,不如说是在为安身立命的思考而苦恼,以及独自面对生存的一种彷徨。
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改名“李哀”,与其说是寄托母亲的哀思,不如说是表达内心的悲伤和对人生又一次重大转折的感叹。后来他出家,也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难以理解了。
李叔同的哀伤色彩,更多地在他的诗词中体现。就拿他填词的《送别》来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其中包含着一种“悲不直说愁满怀”的情绪,接近佛教禅宗的意境,与被称为“诗佛”的唐朝诗人王维的作品意境如出一辙。
慈悲是一个佛子必备的素质,而李叔同的慈悲是天生的。他自小喜欢养猫,敬猫如敬人。少年时,李叔同见兄长李文熙接人待物,礼仪常随人的贵贱而有差别,他对此愤愤不平,赌气地与兄长反其道而行之,对穷人敬重,对富人轻视。
在浙一师任教期间,李叔同被学生们形容为“温而厉”,对他是既怕又爱。在他的课堂上,碰到学生做其他小动作,他并不当场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的学生都走后,他才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说“下次吐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完,再微微鞠躬,表示“你可以出去了”。李叔同从不打骂、责备学生,他用谦恭的态度去教育他们,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慈爱。
当初章士钊化名烁楼十一郎为名妓李蘋香立传正名,而李叔同也化名惜霜为《李蘋香》作序,不仅是出于他们的感情关系,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悲悯的同情心。
而对于国家动荡、政治腐败,李叔同常常抒发出“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金缕曲?别人好东》)”的感慨。从佛家眼光看,李叔同天生就有了“视世事如霜露闪电、人生如西山落日”等一类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
环境因素,社会上浓郁的宗教风气
清末至民国初期和中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精神上充满了失望和空虚。加上佛教教义更加神化,人们便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出家为僧和在家供佛的越来越多,甚至在政界里也有不少人信佛。在1937年1月杭州《赵风》杂志增刊《西湖》上发表的根据1936年春李叔同在厦门南普陀寺口述整理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看。
不仅寺院就在家门口,李叔同的交际圈中,还有研究佛学的人。那就是在十六岁时,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一起考县试,一举夺魁的马一浮。
李叔同结识马一浮是在南洋公学时期,其后十余年未曾相见。直到李叔同在杭州任教后,两人才复相过从。这时候的马一浮已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儒学家和佛学家,而且自身出现了佛化倾向。马一浮来杭州寄住广化寺内,打算用三年时间阅读文澜阁《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卷。李叔同时常到寺中探望他,有时还在隔壁为客人准备的痘神祠小住几天,偶尔也到广化寺内僧人的住所去走走看看,感觉出家人的生活挺有意思。
马一浮先后寄《起信论笔削记》、《三藏法数》、《天亲菩萨发菩提心论》、《净土论》、《清凉疏抄》给李叔同,对他的熏陶不浅。李叔同在1917年3月给弟子刘质平的信中说:“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平淡,职务多荒。”后来,他在撰写《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时,再次提及马一浮对他确立佛学信仰的影响:“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仪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阅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
在浙一师的好友夏丏尊给的不经意的暗示也不少。有一次,学校请一位名士来演讲,他们俩就溜去湖心亭吃茶,看见对面马路上一位和尚走过,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李叔同频频点头,觉得夏丏尊说得“很有意思”。
在没见过李叔同受到的种种苦行之前,夏丏尊是不反对李叔同出家的,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这样说: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夏丏尊和李叔同的关系不一般,并且出家后为他筹建“晚晴山房”,送他真白金水晶眼镜等资助。朋友的真心话,对李叔同的触动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早年的佛教倾向的暗示和支持肯定。在后来的1920年,成为了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在践行席间,指着夏丏尊对大家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亲身体验,弘法度生一直是夙愿
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之中,还必须看到他身体病理的影响。李叔同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由此还染上了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有如当今的癌症,不能治愈,只能靠在幽静清新的环境中调养,远离嚣尘的山谷丛林是理想去处。再则,李叔同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也曾出国留学,受过近代科学的熏陶,但在对待疾病这件事上,却和同时代不少迷信的人一样,以为生病是前世有孽,今生有罪而来,吃斋念佛则是消魔祛灾的好办法。
他从夏丏尊那得到关于断食的文章后,对其中“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深信不疑,将此当作治疗神经衰弱症的唯一办法。于是他开始筹办断食,为计划能成功实施,甚至连好友夏丏尊也不事先告知。1941年2月20日在澳门出版的《觉音》上刊登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夏丏尊这样说:
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几乎”之意,改名李婴……
在虎跑寺方丈楼断食期间,李叔同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后来知道他是弘祥法师)在他的窗前经过,见他总是十分欣喜自得的样子。李叔同便时常找他相互交谈,这位出家人也常送来佛经给他阅读。李叔同亲眼所见僧人和寺庙生活的情景,影响了他的看法,不但解除了他对佛僧的一些误解,还加深了那些埋在记忆深处的对佛教的好感,回来后还对夏丏尊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热情。
李叔同自己也说,他幼年也见过一些出家人,“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在一起……也不知寺中的内容是怎么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而且羡慕起来。我虽在那里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喜欢吃。及至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