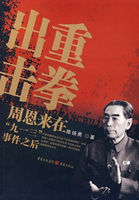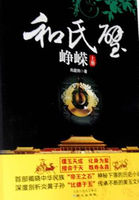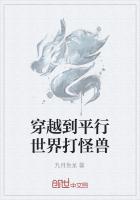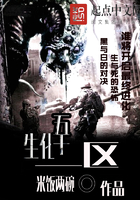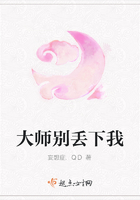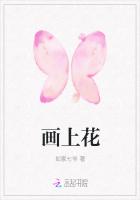记者:解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解玺璋:好的。
记者: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新闻系这个专业呢?后来为什么会走入文学评论这个行业呢?只是因为喜欢吗?
解玺璋:这样吧,我选择新闻专业呢,首先我原来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厂报,而我曾经在工厂里办报。所以当时厂里的一些师傅建议我既然办了这报,而1978年考大学,就干脆报新闻系吧。出来可以有个固定的工作。当时这么考虑的,所以报了新闻系。其实我个人呢,更喜欢古典文献,喜欢翻翻古书,整理收集材料那样的工作。但是后来学了这一行,分配到了报社就干了这一行。
我做评论确实是因为我爱好。可以说从小学的时候,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当时批判三家村,1966年在《北京晚报》有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由三个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撰稿。当时批判三家村,他们还有一个专栏叫《三家村札记》。当时小学我就读到了他们的书,叫《燕山夜话》,这三个人写的杂文集。开始的时候我喜欢杂文,到工厂以后也是喜欢写杂文。包括上大学以后都是看杂文专栏的。后来搞文艺评论,是因为我毕业以后好多好多同学都分在报社,他们都需要这种文艺评论,电影啊,电视剧啊,戏剧啊什么的这些,那么我就开始给他们写稿,原来有一些写评论的基础,写杂文的基础,所以很容易写这种短评。参加工作以后写的第一篇稿子,是一篇评论,是有关当时的电影的,文章名字是《锅碗瓢盆交响曲》。然后慢慢地就写多了,那应该是在1983年或1984年时。这些年再加上我毕业分配工作在副刊,在副刊也负责文艺评论这一块,接触的人也是这一方面的人。以后也就写得比较多,电影、电视剧、话剧、戏剧、小说这一方面,包括美术方面的评论都写过。因为有的是工作上的需要,而我也确实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包括古典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我都很系统地做过准备。在学校也喜欢这方面的课程。
其实是这样,我的个人兴趣更偏重于评论。后来虽然到了新闻单位,其实我做记者的时间很少。我偏重于副刊,做副刊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做编辑。实际上我的工作和我的爱好结合在一起了。从1985年在《北京晚报》编《五色土副刊》一直编到1998年,十几年时间。然后在晚报上开了一个专版,也是一个副刊,是以介绍图书为主的。还在《北京晚报》编过《文艺副刊》,在《北京日报》编过《文艺周刊》。
记者:《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一张报纸吗?
解玺璋:《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两张报纸,一个单位。
记者:在工厂工作是在大学之前吗?
解玺璋:初中毕业以后在工厂工作,16岁进工厂,到了25岁、26岁考大学。因为在“文革”当中,在工厂工作了八年半,之后考大学的。
记者:最近忙什么呢?可否透露一下?
解玺璋:以前是在出版社工作,后来我给辞了。至今已经有两年了。现在在家主要是看书,大多还是为了写书评。看的是一些朋友的书,我喜欢的一些书。更多的还是朋友的书给我寄过来,推荐过来,让我写书评。我侧重点一个是文史方面,一个是小说方面。书评大多就是这两方面。然后就是看电影、看戏剧比较多,包括话剧。也写评论,大约每年我写三十篇戏剧评论。电影评论十来篇,而电影这几年好片子特别少,值得说的很少,所以有时候写得就少一点儿。包括电视剧值得写的很少。这两年写得比较多的是书和戏剧方面的评论。
记者:对现当代文学您是怎么看待的?不少人认为文学已经死亡,您是怎么认为的?
解玺璋:呵呵,老是有人出来说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东西死亡不死亡不是谁出来宣布一下就行了。我以前在我的文章里也表达过这个意思。我觉得文学是不是死亡了,那要看读者,就是说读者有没有愿望来读文学。如果读者没有愿望来读文学,那文学可能就要死亡了。如果读者有愿望来读文学,我觉得文学不会死亡。也许文学会换一种形态,比如在网上阅读。网上阅读也是一种对文学的需求,是吧?只不过传播的方式变了。就和我们以前看线装书,后来我们看铅版书是一个道理。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语,还是喜欢说这样的话“文学已经死亡了”。或者由于激愤,就是对现在的文学不满。我们看不到强有力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生气。所以我们就会说文学已经死亡了。有时候是一种情绪化的话。
记者:您认为现当代文学最缺失的是什么?
解玺璋:我觉得现当代文学最缺失的第一是精神,第二就是骨头。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我们可以不说现代文学,就说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软骨病,就是平庸。我们不用和别人比,就和俄罗斯的作家比,就能够比较出来,同样一个体制下的国家,就能比较出来。当然,两个国家的文学传统不一样,可是你能感觉到中国作家在这方面比较弱。
记者:有些作品里有大段的性描写,不少普通读者接受不了,您是怎么看待的?解玺璋:其实我觉得性描写要看你是故意的还是必须的。而有些性描写是必要的,要看描写在作品里性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说你是一种玩味的、展示的,还是说是一个人生命中必需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名著里都有性描写。在很有力量的作品中也有性描写,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当然可能中国人的国情对于性的敏感度会比西方国家强烈一些。但是我觉得自打改革开放以后,这么多年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关键是一些作品的性描写不是很高级。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官场小说,一些通俗的流行小说。他是把性描写当成一个噱头来处理,他是为了满足一些人的低级趣味。他不是把性当成一个人的本质来表达,所以有时候性描写会很肮脏。
记者:您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差距大吗?您认为这是怎么造成的?
能有所改观吗?
解玺璋:那我当然是觉得差距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不是说差一星半点儿。这个差距一个是由于它的历史背景,比如说现代的文学方式,长篇小说。这个首先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中国是有几部古典长篇小说,但我觉得不能算。欧洲的、西方的小说是一个现代性的表现方式。我们中国是从“五四”以后才学着写长篇小说,你看“五四”时期很少有作家写长篇小说的。比如鲁迅,没有长篇小说,包括像郁达夫他们也很少有现在意义上我们所说的长篇小说。当时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一些通俗小说,像张恨水他们在写。而真正意义上的有这种长篇意识的,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可能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才有一些作家带有长篇意识。所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本来就很弱,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特殊时期的政治环境下一些人丧失了一个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这东西如果落实在小说上,实际上就会变成一种模仿,就会看着别人眼色来写,慢慢养成了这种习惯。说老实话,到现在这仍然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大问题。我们的很多作品描写的并不是自身对于生命的感触,而是对于某一种形式的估计,一种揣摩。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不会有太大的进步和太大的改善。这是很悲观的看法。其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批作家,包括余华、刘震云、刘恒等一批先锋作家,我觉得有可能会有成为大作家出来的。但是很可惜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包括现在市场概念的引入,我觉得也使得他们产生很多惶惑的地方。我以前很感兴趣很寄希望的作家后来都不太令人满意。你比如说余华就是一个例子。以前我认为特别有力量、有分量的写作慢慢被市场收买。我觉得是一种收买,把他们都弄得弱化下去了。
记者:这是不是作协造成的呢?
解玺璋:这可不是作协造成的,作协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体制里只是一个很边缘的机制。他没有任何权利和影响力。特别是有名气的作家不会拿作协当回事的。而作协也从来不发任何指令应该怎么去写。我们国家的宣传和管理是通过中央宣传部,各省市级的宣传部这样的一种机制往下管的。作协虽然也要受中宣部领导,但对于作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作协不会限制作家自由表达的权力。但,作协里的部分作家肯定会看着别人的眼色说一些话、表一些态。
记者:网络文学发展得很快,也受到很多质疑,您是怎么评价的?
解玺璋:我觉得网络文学不是一种文学样式,至少目前看不出来。所有的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他们的思维和非网络文学创作基本上一致,大同小异。实际上网络只是提供了一个传播的机制,一个传播的平台,不同于以前的纸质媒介的方式。当然有可能对写作带来影响。在网络中写作的影响,我觉得至今还没有定型,还在慢慢地体会之中。究竟会给写作带来什么影响,我觉得到现在还看不出来。所谓网络文学它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你不能说网上的一部小说和纸质的一部小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当然它们高下有区别,但是从小说本质来讲,没有什么差别。它的叙述方式、语言都是一样的。
记者:有些网络写手作品产量惊人,年产百万字,而且有很大的读者量,很多人认为他们这是粗制滥造,您怎么看待?
解玺璋:他们的作品确实是粗制滥造的。我也接触过这样的一些人,比如有的网络写手写出名了,他会组织一个班子在那写。再一个呢,他们那种写法因为是商业性的,商业包装策划的,那么他所提供的东西呢,主要是为了人的一种即时性的满足。比如说今天我在网上读完这一段不一定能产生什么感触什么收获,他也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今天过完瘾也就过去了。这东西并不要求很高的文学写作水平,他只需要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一个很强的悬念。其实他是在翻来覆去地说一点事情,有时候大量地重复,这都不要紧,这和我们以前在茶馆里听说书一样,他们也是大量地重复,其实他们的故事核很少。加了很多的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他的观察,遇见过的一些事情,他把这些东西穿插在里面。比如同样一个《水浒》,他可能展开比《水浒》大几倍的东西,也就是把《水浒》给稀释了。他有了一个故事核,就不断地稀释,再啰嗦地瞎讲很多。可是网络阅读不讲究这些,他是浏览式的阅读,而不是欣赏式的阅读。所以也就不要求这些,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一样的东西。
记者:最近谷歌搞了一个数字图书馆,很多作家都对此不满,其实很早以前就有网站可以随意下载,您是怎么看待的?很少人注意到作家的权益保护,您觉得呢?
解玺璋:这个问题其实是网络存在以后一直有的问题。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件事,你在博客里提出来以后我也注意了一下报道什么的。但是我看他们还在重新谈判,可能还要一个很规范的东西出来。谷歌说还要单独和中国谈判,而且作协也组织了一个专家团、律师团和美国谈判。我想不久以后就会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因为我觉得网络这一块呢,比如说对于版权的问题、对于作家的权益保护可能它要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混乱,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嘛!而具体怎么做,双方的责任、义务等等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现在大家都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不管是谷歌还是作协在维护作家权益方面都是向一个方向上努力。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趋势。
记者:在中国好像很多人总是认为作家拿很少很少的钱就能写出很好很好的作品,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解玺璋:哦,呵呵。大家都觉得中国文人挣钱比较少。我觉得看和谁比,当你和房地产大老板比,和做生意的人比,相对而言,收入的确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真正搞文学创作的话,那么出发点不能是拿多少钱。如果这样想,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创作就走到邪路上了。我觉得作家拿到钱只是你的结果之一,你写的小说有可能被读者接受,也有些作家带有自身的独特表达的时候在当时不被读者接受。这个在中国、在西方那就太多的例子了。他不被读者接受,他可能会很惨,会吃不上饭,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不能说明他的作品的质量或者他的作品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而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作品的价值。一个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一定当时就能被认识的,所以说一个文学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不能仅仅用发行量、码洋、钱来衡量。当然大家呼吁作家提高收入实际上是好事。我们都是码字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码的字更值钱。可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我们的期望,不是我们写作的前提。如果把这个当成我们写作的前提那就坏了。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写作是垃圾写作的一个原因。我们过分地把钱当一回事了,我们过于把写作当成了一个挣钱的机器了。这样你的写作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你想讨好你的读者,我觉得一个作家是不能讨好你的读者的。讨好读者必然是媚俗的。
记者:网络词汇的大量出现,如“打酱油”、“雷人”,您认为对现当代文学有何改变?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益?
解玺璋: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新的词汇。这些词汇会不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文学家会不会把他利用下来,我们要看这些词汇介入生活的程度。有些词汇可能在网络上很流行,但实际上并没有介入到生活中来。作家写的是人的生活,不管你是用现代派的笔法,还是现实主义笔法等等,你写的总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是要通过你的语言来表现的。你的生活中不常用的肯定写不到作品中来。就算是写也只是一种调侃式的、借用式的。没有进入生活本身,我觉得语言流传不下来。也有一些语言经过多年的磨合,被大众接受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了,那么肯定会影响到文学,也肯定会被文学借用,文学也会描述这些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网络上的这些语言,还不可能产生那些直接的影响。只能当成一个玩笑,说说而已。
记者:80后写作、“新概念”写作似乎有点儿“过气”,您认为他们会被时间淘汰吗?为什么?
解玺璋:今天还看到一个报道,他们作了一个调查,80后作家自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都认为前面的作家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也不值得他们学习了。这一两年我也看了一些80后作家的书,包括一些他们在社会上的表现和发言。我觉得80后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他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群体。80后和上和下都不来往。比如说他和90后有很多的隔阂,也有很多的论战,而和50后、60后、70后也有一种代沟吧。在观念上是有一些差异,互相不认同。50后、60后、70后还在试图理解80后,而80后却在拒绝和这些人沟通。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见现在出了这么多的80后作家,那我没有看见一个80后群体的人对自身的一种思考和描述。80后也拒绝别人对他的评论。那么他就变成一个自生自灭的机制。因为没有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永恒的。任何群体都是一个时间上的环节。不管你是几零后的,你都要走过这个历史阶段。那么走过之后,你会发现80后没有留下一点足迹。我觉得这是令人担忧的。
在一次会议上,我说80后自身对自己应该有一种描述,而他现在没有。都是自己写自己的,他们自己也是封闭的,他们之间很少来往。而50后、60后、70后都有互相的阐释。文学是需要互相阐释的。文学没有被阐释,那么文学不能算是最终完成。不是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文学的实践就完成了。他要经过读者的阐释之后我觉得才能完成。这就是创作和评论互动的关系。现在80后的创作就遇到了这个麻烦。他缺少这样一种阐释。缺少反思、认识,这是很麻烦的事。
记者:韩白(韩寒和白烨)之争当年红极一时,作为参与者的您,对那次争论有什么遗憾吗?是什么?您对韩寒讨厌吗?
解玺璋:呵呵,我其实挺喜欢这小孩的,就像你这样。韩寒的第一本小说《三重门》,可能我是第一批读者,而且我在第一时间采访了韩寒。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给他写过一篇文章,介绍韩寒的,文章题目叫《放飞一只自由鸟》。我昨天晚上还写了一篇文章。上个礼拜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批评韩寒的。韩寒在一次采访中说郭敬明的价值观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这个作者就不太同意韩寒的看法。我找到了韩寒的那个采访,看了一下,我觉得韩寒没有说错,对郭敬明的批评很准确。我写了一篇文章《韩寒的话没有说错》,稿子在下个礼拜发。用来回应一下那个作者。我觉得我和韩寒有很相通的地方,我也是一个对体制格格不入的人。当然我有我的方式,他有他的方式。
至于当年的那个韩白之争,我记得我和你说过,后来有点后悔。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完全掉在了一个被别人策划好的推广活动里了。我很后悔的是,我们被别人策划的一个东西当工具了,这让我很不痛快。因为当时他们的目标还是要推动韩寒的新书,他们策划了这个东西,后来我了解到白烨这篇文章不是针对韩寒写的,是一篇研究80后的论文。在谈到80后时,只是举了韩寒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搞营销策划的人利用了这件事,然后让韩寒写了这个东西来骂白烨。而我写白烨的那篇文章是在这件事情的三年前,就是吹捧白烨的文章(笑),我们的关系确实很好。我也觉得他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韩寒文章的推出,其实和他都有关系。他在80后作品推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要读很多很多的80后作品。所以我觉得韩寒这么说白烨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当然要替白烨说一些话。再加上大家吵起来以后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网络吵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再加上我这种脾气和性格,工厂出来的人不在意。你看白烨后来就跑了,人家就是纯粹的文人。我就不一样,我管你是谁,我就是要说自己想说的意思。
这件事到现在来反思吧,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显示出两代人对文学的理解的差距和矛盾。它把问题公开化了,揭露了,但是实际上没有深入下去,并没有把问题讲透。
记者: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解玺璋: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从私人关系上讲可以成为朋友,也可以成为对头。
这都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大家的文学观不一样,那么可能对一些事情一些作品的看法就不一样。而从理想的角度讲,我觉得评论家和文学家是相互独立的。文学评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并不是依附于作家的行业。现在有人说搞评论的人就是依附于作家的。没有作家你搞什么评论呢?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评论是一个独立文体。你要把评论当成一种创作来搞。我是谈你这部作品,是以你的作品为素材,来表达我自己的意见。所以我很少就一部作品谈一部作品。我都要在一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可能你作品中没有,是我生发出来的。因为有些作家和我说他小说里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读到了这个意思。那么我就按照我读出来的意思来写。我觉得理想的文艺评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或一个文体。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我们的文艺评论才有出路。而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把评论当成一个营销策划的工具。我们出一本书,出一个电影,出一个戏剧,需要评论家出来说两句好话,给你两个钱。我觉得这个和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是不搭界的。这个不能算是文艺批评。当然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刚才说的目标。我们原来讲的是独立批评,比如说电影,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电影的批评小组。我觉得批评界要保持自身的尊严,就是要有自身的独立性,表明你的意见和你的声音,不依附于别人的。
记者:您本人是一个记者,在您的博客上也看到您说现在文化新闻越来越娱乐,越来越八卦,您觉得这是什么造成的?长此以往对文化有何伤害?您认为能够解决吗?
解玺璋:我觉得至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有这种倾向,就是大家要求新闻读起来更轻松,更好玩。慢慢地走到现在这种状况,包括以前我们叫做文化新闻版,文艺新闻版,现在改成文娱版,甚至有的干脆就叫做娱乐新闻版。那么他就改换了新闻的本质。其实新闻的本质就是最直接地介入社会,包括文化新闻也是这样,就是传达一种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一种价值观念。但是现在变成了娱乐的一种方式,就是逗大众一乐,所以显得很轻松。这实际上掏空了新闻的内核,变成一种很空洞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的根源就是这些年来把所谓的商品和市场引入了新闻的领域。市场不是一个通用的概念,不是什么都可以市场化。新闻如果市场化,那么带来的问题可能不只是娱乐化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有钱权交易新闻?就是拿钱来购买新闻,就是市场化造成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把握得不好。而且我也不是很乐观,现在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往好的方向上发展的苗头,实际上我们遇到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记者: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打扰您了!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看过不少书,能给读者推荐一位您最喜欢的中国现当代的一位作家和一部作品吗?只要是您喜欢的就可以。
解玺璋:那我还是想推荐余华,他的作品《活着》。原来我想推荐《光荣与梦想》,美国作家作品。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了四十年,说的就是他怎么做记者的。我对很多同学推荐过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是很值得大家看的一本书,包括他的文体,他的精神,他的工作方式。对于我们学新闻的是非常受启发的。而文学上我觉得余华还是值得关注的。
记者:呵呵,谢谢解老师接受我的采访!祝您在文化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解玺璋:谢谢!
(注:本文由许多余采访,刀仔整理)
备注:除特别标注采写作者之外,其他均为许多余本人采写。均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