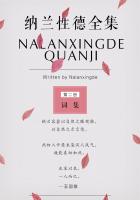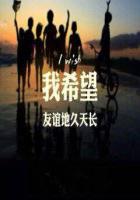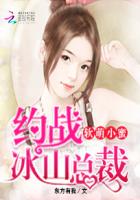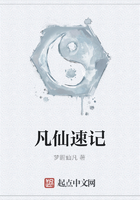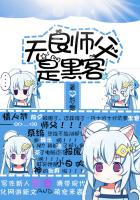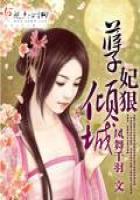一
回族除了过开斋节、古尔邦节、阿述拉节、圣纪节等大型公众节日外,平素也会干“尔麦里”。“尔麦里”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指各种功修和善行,特指为纪念伊斯兰教先贤、哲人和门宦教主的主要宗教仪式,平常人家也在直系亲属亡人的祭日里以此形式做祭祀。干“尔麦里”也叫“锅里倒油”或“念索尔”。
这天,诗人单永珍家里“念索尔”,我抱着好奇的心理陪他回到了西吉县兴平乡堡子村的老家。他换了整齐的素装,戴了洁白的回族白帽,一到家,他就和家中所有的男士们先去了一趟坟上,然后站在大门口等着迎接阿訇。阿訇和满拉骑着摩托车来了之后,大家开始保持肃静,接着焚香,由阿訇带着满拉和会诵经的人诵经。诵经的过程中夹杂着一种“接都哇”的议程。这种议程和诵经衔接得非常严谨又非常自然,所有人都伸出双手,手心向上,目光向上,目光中心充满了无尽的祈愿和祝福,屋里屋外一片静穆。有大化生息,天人合一的气氛。接毕都哇,再异口同声地轻呼“安拉乎……”
据说,这时他们虔心向上,把最真、最美的心愿传给安拉,然后接受安拉神圣的信息回馈。
诵经之后,气氛转缓,开始散乜贴,请阿訇和客人吃油香。“念索尔”,条件好或祭祀规模大的还会宰牛、宰羊。他们今天宰了鸡。在我品尝单永珍母亲亲手下厨烩制的烩菜时,单永珍的大哥单永华说:“宰牛、宰骆驼和宰羊宰鸡没啥两样,贫苦人家为亡人举念一颗枣、一粒花生也一样神圣,也能表达一颗虔诚的心。”
这是一座非常自然的自然村,没有楼房,也少有砖房,沿着依山的崖面看,这里人原来住的基本上全是窑洞,现在都从窑洞里搬出来了,但依地势而建的砖土混建房屋并不整齐划一。听村里人讲,一部分农户迁移到有水的川区去了,一部分留在这里的住户,到了开春以后青壮劳力全出门打工去了,村里剩下的全是老年人和孩子。一旦谁家有个紧急事,满村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劳力。
我沿着农户间的斜坡上了单永珍家的崖背,在那里一眼就可以俯瞰这个村子。山谷里有水库,清洌洌的,微风吹过,水面生出一道道银色的皱褶,微风过后,整个村庄一片寂静。倒是不远处一家门前有两位妇女携着一名小孩在摊场,她们把头年收回来的胡麻散开,然后跪坐在胡麻上用木棍开始捶打起来。这在其他地方可能叫碾场或碾粮食,他们会使用一些现代化机械,最不行也会使用拖拉机。拖拉机拉着一柱石碾在麦场上转圈,腾起一股迷人的尘雾。而我所看到的这种用木棍敲打粮食的情景只能叫作打场。原来我对“打场”和“打粮食”不甚明白,现在终于知道,粮食欠产了、种植太少了、家里缺乏劳力了,碾子根本转不起来,“打”便是一个最准确的表达形式。粮食在地里长了一季,成熟了,成了可以供人们粉碎,从中获取养料之前,还得经得起捶打。这和一块铁要成为一颗有用的铁钉的经历没什么大的区别。于是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常念叨的一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当时我便构思了一句诗:“奶奶对谷穗喊,钢啊/人和飞禽走兽都吃饭/你一定要长成/能够煮出熟饭的生米。”此后我把这个句子写在了《谷子》这首诗里。
我边走边看,不觉就走到了山顶,其间我心里还在想着那些被捶打的胡麻。它们都有一颗赤裸得发亮的身体,内里满含着香喷喷的油脂。人们把它从小灯笼一样的果壳里敲打出来,再榨出它的油水,为自己增添热量。这是不是也算杀生呢?
每粒胡麻中一定有一个生命体,它从果壳里一跃而出,大概就像人加入了新队伍,获得了重生一样。有的,人们把它撒在地里,长出青苗,生出一大群孩子。有的为更高尚的事业献身,赴汤蹈火,化作了油泥,最后登上了祭坛。油香,不就是用胡麻油炸出来的吗?我记起单永珍的大哥那句话,我知道了举念一峰骆驼和举念一粒芝麻是同样的心理。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们都在“接都哇”,而盛大的祭坛上有一粒粒胡麻,胡麻睁着丹凤眼,胡麻有平常而又甘愿献身的心。
我本来还想把胡麻和吃斋念佛再联系起来好好想想,可山顶的风突然吹醒了我,杂思全被吹散了。
二
我选择上山的途径,是片退耕后闲下来的荒坡。前人走过的小路就在不远处,可我由于精力集中于那粒胡麻,竟走了没有脚印的荒地。其实从荒坡爬山路途最近,不过前人是怕踩伤了田地,才选泽田边临崖的险要处行走。农夫都这样,把平整利己的地方留给庄稼生长,自己走坡埂,他们天生有一颗毫不利己的心。
由于精力集中,由于荒坡比较陡峭,我出了汗,也有点眩晕。于是,我选择了一块平整的土坎坐下。记得十多年前去越南旅游,乘船经过亚龙湾时也这么眩晕。大海上不仅有一座座小岛、沙洲,还有因风而起的层层浪涛,那是大海的本真。现在坐在山巅上,看一座座丘陵和土峁,便也觉得看到了西海固地区大地的本真。如果那次去越南算是我成年以后的“忆苦思甜”,那么现在坐在山巅上就算是回味“忆苦思甜”了。
越南人民当年还过着“大生产”的日子,排队下地,集体唱着他们歌颂社会主义的革命歌曲,我们去的人全都是外国佬,全都是大款。那时我们国家正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去的人大都是“万元户”。我们走在河内大街上,个个昂首阔步,我们不仅是大中国的子民,还因为一元人民币可以兑换上千元越南币,我们人人怀揣上千元人民币,我们都是百万富翁。
后来听说越南也在仿照中国搞改革开放,不知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否已经富裕。看看面前的层峦叠嶂的山峁,心里不觉又有些舒然。现在别说“万元户”,按固原市现时的房价来估算,有两套房子的人,都是百万富翁。当然,有山峁就有沟壑,贫困线上的人也很多。
在此同时,我看到了独立在山峁上的古堡,它们大都生于民国民不聊生的岁月。那个年月有钱人家不建能够自保的土堡不行,土匪和强盗猖行,随时都会有强盗出没。国民党政府也想清除这些祸害,以此博得人心,但力所不及的不是他们没有武器和军队,而是没有真正为民着想的意识。因此才有了土匪和强盗,人们不得不寻求自我保护的办法。
那些古堡也许叫张家堡,也许叫李家堡,反正走遍西海固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这些挺立在山巅上的堡子,像一艘艘浪尖上飘摇不定的船。它们曾经都是富豪和富豪坐卧不安的象征。
我突然想起刚才“念索尔”时夹在诵经中间的“接都哇”,人们双手伸出来,默默地承接着上苍最美好的赐予。这些古堡假如是山峁伸出来空空如也的双手,它们在承接着什么?如果是一张张向上苍祈求的大口,它们在祈祷着什么?我没有得到答案。顺着山峁向下看,沟壑里有零零落落的民宅,我把这些古堡的祈愿缩移到了村里,缩移到一个个人上,又缩进一粒粒胡麻,我觉出了这粒胡麻的巨大。
如果这些在山峁上栉风沐雨的古堡是正在与风浪搏击的大船,那建在村落中,已经半颓的堡子或使人一眼不能望见的堡子就算是沉船了。他们被新建的砖土房逼到了一个狭小的角落,将被遗忘、将被淹没。
据单永珍讲,他们家所在的堡子村里就有这样一座沉船似的古堡,叫王家堡子。这也是他家所在的自然村名字的由来。他为了让我得到确实的文字依据,还带来了一本《固原史话》。其中有关于回民起义的记述:“1940年冬,马思义、冶巨仓、王德成等征得马国的同意,暗中聚集,秘密商议复仇,准备第三次起义。马思义等在二林沟起誓结盟后,开始进行剪除‘黑燕麦’(山区农田里一种杂草,用它比喻勾结敌人、残害农民起义的内奸)活动。……(5月)6日晚,起义军从泉沟垴出发西进,经沐家营到达兴平。7日,攻打联保主任王瑞林的堡子,并击溃前来增援的隆德保安队。8日,返回泉沟垴。”我查阅过《固原历史纪要》也有同样的记述。这里所说的“王瑞林的堡子”就是现在还在民房中沉默的王家堡。
王瑞林作为当年的联保主任,自然维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讲,也不为奇怪。那回民义军剪除“黑燕麦”,攻打这座堡子也是势在必行。到了现在再看,这座堡子确实为当年的联保主任保了驾,也算是一种侥幸和万幸。
事情在变化中变化,国民党当时把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叫“共匪”,马思义带领的革命义军受共产党领导,这位担着时事担子的联保主任,躲在自己堡宅里不敢出来,引人同情。现在这座古堡里走出了一位党的基层干部,他叫王永明。他自小接受了共产党教育,痛恨国民党当年的反动宣传,通过考学、干部培训,肩负起新时期乡镇建设的重担,在工作中干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不得不令人赞叹。古人说得好,老虎不下狼儿子。在这座堡子里,走出了两个乡长,爷爷是国民党的乡长,孙子是共产党的乡长,都是为民跑腿的人。听老年人讲,当年的王乡长可威风了,骑着高头大马,在烂泥河一带,人人皆知。那些给地主王乡长拉过长工的,都赞念着他的好处。虽然现在的王乡长坐着小卧车,但坐小卧车的人多了,就显不出一个人的威望了。
看来,同样的一座古堡,会走出不同的人来,就像许多革命领导毅然走出自己家庭,一粒胡麻可以作为种子,也可以作为贡献油脂的原料一样。
现在,是百舟竞发的时代,古船在日日下沉,新帆在迎风远航。
三
坐在山巅上的人都会有远眺的习惯,我在远眺。
我看见了一棵夹在两峁中间的树。它大概是一棵柳树,不,柳树没有那样坚硬的枝条,它大概是一棵杏树,不,杏树没有那么挺拔。它一定是一棵榆树,榆树有坚挺的身躯,有婆娑的树冠,榆树耐旱、抗风沙,能令人看到它生在常态中的陌生。
单永珍是个既结实又情感丰富的诗人。从他的诗中能读到怀古的沧桑,也能体味到似水的柔媚。在生活中,他不拘小节,与他同行,宛如走在森林中,与他站立,身边俨然立着一株大树。记得前两年他没有动笔,只一味地读书,我问他怎么忘了写作,他只默默地摇了摇头。有一次我开车路过十字路口,见他一个人站在道边望着穿行的人群,他一直这样看着,我把车靠在他看不见的路边,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
据说这株立于两峁之间的榆树,是整个堡子村的形象树,在包产到户哄抢树木的时节,堡子村大大小小、村里村外的树都被砍光了,单是这株树没人去砍。大家都盯着这棵树,假设着这棵树的未来,也许它能成为一个栋梁之才,也许有朝一日将被大风吹散。
我看着这棵树,越看越陌生。单永珍作为诗人,在与新华社宁夏分社杜社长的谈话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诗歌,首先,是语言的熟练程度。其次,是情感的丰富程度。再就是在熟悉的事物中,写出了陌生。”他的这句话使人觉得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
看来这株树在两峁之间已经站了许久,前面是一座座山巅,背后是一座贫困但又焕发着新气象的堡子村。村里人都去打工赚钱了,这株树还坚守着山脊上的苍白,蹲候着一场场风。
我默默地望着它,仿佛祷告。它也祷告,也仰着脸,伸出手臂,承接着阳光。
山上没有路,是本真的,胡麻有颗静默的心,也是本真的。我举念一粒胡麻,举念一棵树,也举念这一座城堡,举念这西海固一座座苦旱的山。
举念一棵树
举念一棵大树——
发出声响,奔跑,行走——
举念它原地飞升
举念大树,相当于已经把自己打扫干净
相当于知道它胸中无鸟
无蝉,无尘
立于山冈,我举念着一棵大树——
扬起头颅
安静,又抓地有根
举念一声巨响,一阵隐痛,举念树上生满羽绒
但我不举念雷鸣、掌声
我举念一棵大树——
我手臂伸入长空
举念一粒胡麻发出树的怒吼
我的举念,如同一根游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