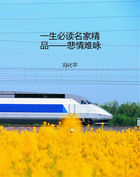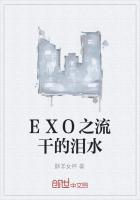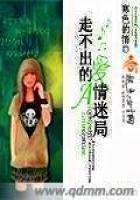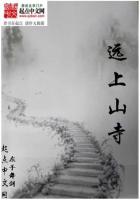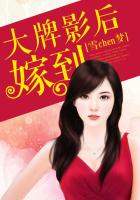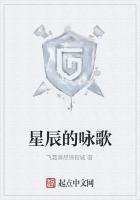扁担与城堡,两种材质,没有母子连心的关系。
如果,当初扁担有过为城墙的建立而输送黄土的历史,那扁担的身子骨一定会像老人的寒腿和倦腰,弯曲着,疼痛着。城堡一定绵蜒着,如同一直沿用的扁担,保持着永远的神态,延伸在西海固每一户普通农户的日常生活当中。
宁夏固原头营梁西坡下1922年夯筑的古堡,依然在挺立着。堡门边上的那根扁担,照旧立着,弓着腰,向人们致意。
这座古堡叫胡家堡。这根扁担是榆木扁担。最初,我看到高达十米的堡墙,却忽略了这根单腿独立的扁担。
我一步步走近古堡,古堡中有人抓起扁担,用扁担钩起两个空水桶,再一步步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扁担也是一种存在。它的身子是弯曲的,形状是扁的。它有没有面目,究竟以什么做面部,它行走在这个世上,何为它的腿脚?日落时分,天色渐渐昏暗,我不得而知。
借着黄昏,这扁担弯曲的程度,足能令人浮想联翩。联想它的年龄,联想它与人的关系。它与人肩傍着肩,走了一百年,一千年,或许更长时间。一代代人的腰椎,弯曲了,一代代不甘弯曲的脊骨竖直,又被它压弯了。
扁担,简直像庄户人的导师,像庄户人的心,像庄户人的命。
这位挺胸做人的挑担人,无畏地、傻乎乎地挑着陪他取水的扁担,笑呵呵地和我搭起讪来。他安心、自信,根本没考虑扁担与他的关系,也没有留意身后堡门里已经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腰身略有弯曲,是他的叔父。他们都不急不躁,都想把胸膛挺得像堵墙,笑容都灿烂得像墙上的霞光。他们父子俩熟知到不用相互照面,不用言语和用身体某个部位传递一下信息。这位挑着扁担的晚辈,两手把住摇晃的扁担钩,止住了铁桶的“吱扭”声,但这位叔父没有借此而说什么。这位晚辈只好攥住抡在一起的汲水绳,去了沟底,去了望着天空的井边。我进入了茫然,随这位叔父进了古堡。
这位叔父名字叫胡俊珠,62岁了,属虎。他告诉我,堡前这条柏油路,是条新修的乡道,从头营梁下去经猴(侯)磨,可以直达现在管辖他们里沟村的彭堡镇。我不觉联想到类人猿。人在猿猴阶段一定不会使用扁担,因为扁担在人能以肩膀挑东西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扁担像原子弹一样,也是人类的一大发明,也像天平一样能够显示一种平衡。也许天平的诞生正是源于扁担与担钩上的两桶水。也许人们所说的“生态平衡”正是需要扁担两头的重量相等。
人是猿猴的时节,还不会装腔作势地挺腰杆。人还在蒙昧阶段生活的时候,一切由大自然本身来掌控。土也不会站立为墙,榆木也不会因刀斧而成为椭圆,欲望也不会促使一部分人去抢夺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战争也不会此起彼伏。
走进幽深的堡门(虽然堡门门洞只三米多深,但过道很狭长),这位叔父的女儿已经嫁人,儿子外出打工了,儿媳在镇上开了理发店,只有他和他的老伴在家里,守着几亩地。从他的口里得知,刚才挑水去的小伙,是他三老人(叔父)胡元生的孙子,叫胡金云,住在古堡的侧面。他父亲为老二,叫胡元清,早在1961年47岁时就去了,母亲1999年离开了人世,伯父胡元满1997年也去世了。他说这座土堡是他爷爷胡老爷唯一留在这个世上的遗迹。在猪年(1935年)爷爷请来筑堡匠人,蒸好馒头,杀了猪,奠了白酒,敬了土地爷才动的土。那时,人们运土虽然只有背篓和扁担,但不停歇。他说:“扁担扁担,不怕慢,单怕站。”那时人的体格偏瘦,很瓷实,偷奸耍滑的也很少。四个月下来,堡子打好了,攒下的粮食吃完了,民工肩上的皮肉也都磨出老茧了。
堡子打好了,土匪只能望洋兴叹,国民党的部队却大摇大摆地来搜刮了。唯有共产党的部队来了不抢粮食不杀牲畜,亲亲热热地讨口饭(粗米黑面土豆糊糊从不嫌弃)就走了。解放以后这座堡子当过头营乡政府,作过生产队的库房。1959年到1960年生产队吃食堂在堡内架过集体灶,那口大铁锅,可以装下近十担水,挑水的人把水倒进锅里,每一个人都长出一口气。
刚才挑水去的胡金云已经放回扁担来到古堡进了屋,他一屁股塌在热乎乎的炕边上。他没有说话,仿佛刚才扁担一部分压力还残留在肩上。说不上,那根扁担的铁钩在摇晃,说不上,我走以后,那根扁担还会落到他肩上。说不上的是明天,说不上的是今夜,说不上的是,永远放不下肩负扁担的受苦人。
走进里沟,凝望胡堡
土堡摆好架势,立于高地
像一头牛,跟着一头犊
我看见,堡门洞开
少东家的瞳孔里,人丁林立
少东家刀刃犀利,一扫三百亩果园
五百匹马和十里水地
少东家站着,南山的土匪
北川的癞皮,只悻悻地远处转悠着
少东家站着,民国进入了晚年
大风落地,喑喑哑哑地走着
我看着少东家的画像
我看着风——
刮得一座古堡满地打滚
我不敢确信,只好再揉揉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