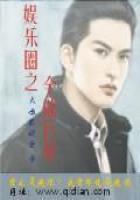问题在于,格罗并不满足于默默地执行任务,他要将所做过的事都拿来夸口,是个口风不紧的人。“如果不能对朋友们吹嘘,”他曾说,“去找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共度良宵有什么意义?万一事情出了差错,老虎乐团或蒂华纳大嘴鸟乐团把你当成了毒枭,在酒馆与汽车上的收音机里歌颂你的故事。Chale(好样的)!你就变成货真价实的传奇了啊,来点节拍吧。”
很多次,他们一块在酒吧里、派对上喝酒,或是在摩洛哥大厅两支舞曲间的休息时间里,她蜷缩着靠在格罗的肩膀上,他右手拿着太平洋啤酒,而她的鼻子上沾着一层可卡因粉末,她内心五味杂陈地看着男友对任何聪明男人都知道该闭嘴的事情高谈阔论。特蕾莎没念过什么书,格罗是她唯一的知识来源;但是她明白所谓的朋友,就是同甘苦共患难,他们会在你住院、坐牢或临死时来看你。这也就是说,朋友就是朋友,直到有一天不再互相往来。
她头也不回地走过三个小区。没办法,她穿的高跟鞋鞋跟太高,如果突然跑起来,必定会扭伤脚踝。于是,她脱掉鞋子,放入袋子里,光着脚走到下一个街角右转,直到来到华雷斯街。她停在一个小饭馆门口,看看自己是否被跟踪,还好,并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为了能稍微思考一下,并且舒缓一下剧烈的心跳,她推开大门走进去,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
她的后背紧贴墙壁,双眼盯着大街上的动静。就像老爱玩双关语的格罗说的,观察情势,或者试图观察情势。湿漉漉的发丝散落在脸上,她只拨开过一次,后来她觉得还是披头散发好,这样可以稍稍伪装一下。服务员端来仙人掌混合饮料。有那么一会儿她动弹不得,无法将思绪连贯起来,直到犯了烟瘾,才发现自己在匆忙离开时忘记带香烟了。她向女服务员要了根烟,借用打火机点火。她没注意到服务员见她打赤脚时露出的疑惑目光,只是非常安静地吞云吐雾,同时整理思绪。
现在总算好多了。从肺里吐出的烟雾,让她拾回些许理智,足够用实际的感觉分析目前的情况。在那些野狼抓到她、强迫她沦为毒枭次要人质之前,她必须到另一处房子去,一处安全的秘密基地,那曾是格罗一直梦想着老虎或大嘴鸟乐团能够为他演唱的故事情节。钱和文件都藏在那里,不管她多擅长逃跑,没有这些东西,就哪里也去不了。格罗的笔记本也放在那儿,上面记载了电话、住址、联络人、秘密飞行航线,其中包括下加利福尼亚州、索诺拉州、奇瓦瓦州、科阿韦拉,以及散布在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朋友与敌手的数据—要分辨清楚敌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布拉沃河的两畔则有埃尔帕索市、华雷斯市、圣安东尼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