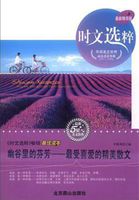高艳
晨曦,从窗帘的缝隙流进,我闻到了天亮与天黑不同的味道。尤其是今天,立春,是我的生日,它似乎更让我的感觉敏锐。我不能不想到母亲,还有父亲。
其实,这样想并不始于此刻,自从他们离去,尤其孤独或夜深时,巨大的静围裹我,世间的伤痛就会轻易浮出,他们的身影微凉地滑过。父亲,三十几岁的他不在时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而母亲已然衰老,但他们,同样激起我心底的痛楚,一波一波,荡漾不绝。去年,母亲离世,父母得以合墓而居,可是,在刻墓碑时,父亲的生辰与逝去的时间,作为子女,我们竟不能得知。因为我和弟弟妹妹那时的过于年少,成为不能修补的遗憾。那留下的空白,是痛和惘然。他们在路上了,我在张望,长长地驻足。生死无法穿越,而我更确信村上的话,“死并非在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于生之中”。
所有的生命都始于母亲,甚至,我以为,包括写作,同样来自于父母的给予,这如同宿命。我相信。细弱的生命,当我们攥紧,却仍被世界以无足轻重的理由任意修改。
立春,在北方却没有任何关于春天的迹象。雪,细碎,纷乱,弥漫成雾。寒冷依然无处不侵袭,包括梦境。这样的生辰,我以为是一种暗示,冰在,雪在,草木暗藏生机,只是,等待,似乎显得漫长。
暖意,不是冬衣里的棉絮带来的。对未来的期许,星星点点的,也会让人熬过许多不安与忐忑。梦里纠结的事物,总与寻找有关,寒冷与焦虑,比白天更肆意地在我体内穿行。混沌的梦境隐喻了怎样的生活真相,就像母亲在世时,总说起梦到悬崖,然后惊醒。我现在才能深切感受母亲那时生活的焦虑与不安,没有父亲在,全凭一个女人担当的日子,何其无望与无助。
其实,对于生活,我并没有奢求,活着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件圆满的事,只要不费心力,只要有暖,便安心。
时间,义无反顾地笔直向前,生活,却在枝枝蔓蔓中,疲倦着晨昏。
母亲走动在客厅里,苍老,瘦削,轻微,或重的叹息,只这一瞬的回忆,我已心碎。那时,她年轻,她寂寞,她愁苦,她一个人拉扯我们三个孩子,灰暗着生活,而后,是病的她,失忆烦躁的她……这些片断模糊而忙乱地向我挤进。即使回忆她的笑意,也会让我不由得揪心。我曾怀疑,母亲的一生是否有过短暂的幸福,这样的想法更让我难以自制的心痛。母亲的生活充斥的冷从不消失,她好像自己看穿了自己的一生,她对生之悲观的想象,遮蔽了可能存在的暖与好,她从不知道,这可以间接地影响到我。她说,没有父亲的孩子,被人小看,没有人要……心智尚在模糊的我,内心便永久地埋下了不可抹去的痛与卑微,一度因恐惧而牵强潦草度日,倔强地敏感而自尊。那时是这样,而今,经历过一些跌宕,我依然是,没人知道。
而关于父亲,除了一张笑着的面孔,烟熏的微黄的手指,他的影像已呈现不出更多。这样倾斜的记忆,不是不公,于我,是时间留在身体深处还在隐隐痛着的疤痕。他年轻时的笔记本上,留下一些不多的诗句和未完的剧本,激情与火热,像他年轻繁盛却不长久的生命。他不知道,现在,我,他的女儿,有时也会用文字复述自己,这是不是也根源于他呢。
窗外,巨大的黑色树枝粗鲁而干硬,上面有些微的落雪,它横斜于窗口,甚至你都怀疑它是否会生长出绿意。一只鸟飞落枝上,不过片刻,便振翅离去,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它。
春天,显然还没有来临。
而在立春的日子,幻想中的明亮和暖意,总应该在不远处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