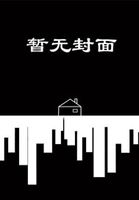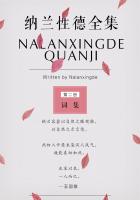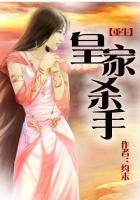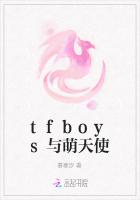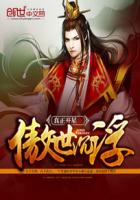朱谱清
1
水滴不断穿过石头。我听到耳边一声声轻响,无形的时光变成具体的小而晶亮的圆窝形状。这一个或一组动作,在信念和岁月面前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回到生活中来,从一边走向另一边,从此地到彼地。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穿越?穿过门、穿过房间,穿过街巷。从故乡到异乡,从异乡到故乡。
人啊,没有谁不在穿越自己和周遭的生活。
从记忆出发,我想说说这条常常穿过的街。惭愧的是,我是最近才仔细注意它的,更准确地说,是半条街。
场景是深秋。随着秋天往成熟里渗透,天空的蓝色达到一定深度和纯度,这条街的凡俗、杂乱被某种东西掩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美好。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这街边的七八棵银杏树。一年之中,除了冬天和半个秋天,那些树们夹杂在一起,除了银杏,行道树大部分是香樟树。或浓绿,或碧绿,或浅绿,都是一个色系和气息,显不出特别的景致来。现在那些银杏的叶片,因为时光的催化,渐渐变得金黄。扇形的小叶脉拢在一起,顶在树梢,给趋向冬天的街道增添了几许温暖明亮的气息。
“树木永远不会是世界的核心,而是世界的陪衬,这就是本世界的真理。所以,当周围的树木越来越少,我们从不注意(于坚语)。”后来,当我咀嚼着跳入视野的这句话,内心有微微的共鸣。在那一瞬,我庆幸自己终于在习以为常中,感受到一种植物的血液,汩汩流淌着,去赶赴生命的盛开,然后老去回归到大地。
季节好似渐渐滑向冬天了。现在不大查日历。我记得纸质的小开本日历,在我父亲那里总是被小心翼翼地一张张翻过,用夹子夹好,不舍得撕掉一页。一年过去了,还有整本的日历在卷曲的纸间见证着流过的岁月。这种日历,在大多数城里装饰考究的新宅那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而我们,就在这翻卷的纸页间,渐渐远离了故土和双亲。
翻手机,方知节气“小雪”已过。在皖南,深秋的日子若天气晴好,总是和节气慢半个拍子。这时节这条街,这些金黄的银杏树,仿佛一只只温暖柔美的双手,遮掩着、抚摸着质感坚硬的水泥街道和高楼,使之变得美好。顺着银杏树朝东看,街道不是一味的直来直往,而是一个稍微的转折,仿佛书写者的一个意态悠然的顿笔。仔细感觉,空气中仿佛漾出一股清甜醇厚的味道,但它从何而来,却莫可名辨。
2
这是条很普通的街,叫北园路。我每天打这条路经过,循着这样的路线:从居住的5楼,下到一条6米宽的巷子;向北,折进东西向大约30米宽的津河东路;然后越过鸿韦路,到达北园路;再转个弯继续向北,往上班的地方赶去。这几条不相干宽宽窄窄的线路,占据着我的很大一部分私人空间。因为生活的方向,我的足迹将它们串联在一起。当然,在其上流逝的,也包括过往的青葱岁月,以及往中年里迈步的无声无息。
大多时候,我骑一辆紫色的轻便自行车。因为赶时间,我尽量将车子骑得快点,大多时候是匆匆忙忙的,耳畔是风声,却没有电影里或年少时代兜风的畅爽感觉。
车后座上有一只篮子,那是儿子三岁时装上去的。黑色,网状,金属质感的,靠近坐凳处有绿色的握把,小家伙可以将小手抓住它(可惜没过几天,那绿色的唯一带有装饰性的把手外壳,下落不明),可以靠着、歪着、斜着,我不用担心他摔倒在车流中。他在这只篮子里坐了将近五年,直到那个黑色的网状物断了好几根铁丝,与坐凳连接处出现了裂痕,变得摇摇晃晃。同时,我抱他上去的时候也明显费力多了。
“那时,我坐在妈妈身后,她柔弱并不宽阔的身体挡住太阳和风。若是深秋,我喜欢坐在车上看流动的树,看金黄的银杏树叶飞舞。冬天,逆风而行的妈妈让我将手放进她的后腰衣襟深处。她骑得很慢,只有呼呼的风。这是一段缓慢的路途……”多年以后,那个小名叫澄澄的男孩渐渐长大,会不会在纸间这样回忆?
二年级上半学期的时候,腼腆的儿子给我建议:妈妈,把那只篮子拆掉吧,我已经不是小宝宝了,再坐在后座篮子里,怕不好吧?
你是不是有些怕丑?我问。
嗯,我的同学,一年级时都不坐在篮子里了。
于是,那个曾经带着儿子体温的黑色金属物,被拆下来,放在墙角。我用枕头做了个垫子,外面套上彩色塑料袋,绑在自行车坐凳坚硬冰凉的白铁上,放在外面即使淋雨也不怕了。
儿子说,坐在后面,不杠屁股了。
我看到,他可以抬腿轻巧地跨上车。
儿子在长大,我在衰老。我和他互为镜像。他通过不断更新时间的信物,诸如奶瓶、米糊、婴儿装、识字卡片、玩具等具体事物,告别他的幼年。我则通过身边的小家伙,感受到了表象上的容颜渐老,及莫可名状的时光流变。
也有不骑车的时候。遇上下雨天,或许上班的时间还充裕,我便走路到办公室去,慢慢地走。有时看看路边的店铺,有时看看车流,有时只是无目的地走。
3
这条街的东半段,没有高大豪华的酒店或饭店,是一条生活性的次要街道。以宁城北路为界,将道路分为东西两段。因为上班和回家的缘故,我经常循着东半条街走。这里,挤着眼镜店、社区医院、发廊、歌舞厅、窗帘店、橱柜店、手机店、日杂店、自行车铺子、大排档,还有摆在人行道上简易的炒货摊……这些店规模大小不一,格局及布置都各不相同,挤在同一条街上,使你觉得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去得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实验小学。每周再忙,我尽量抽出两三个中午的时间,去接儿子放学。和他一起吃饭,带他回家。然后到点再送他上学。另一个,是街边简陋杂乱的自行车修理铺子。我的自行车似乎老了,总是发生破胎或掉链子的现象。
现在,也许是开私家车的多了,要寻个修自行车的,反倒有些难。离我最近的自行车铺,过红绿灯大约50米,就在必经的这条路上。修车铺子是租用的一层门面,狭小、逼仄、杂乱、沾满油污,多少有些破坏街道的形象。铺子不大,墙面堆满了车轱辘、车胎及其配件,人行道上散落着各种钉子、螺丝,连那一方空气,也散发着油污的味道。
“哎,我的车胎破了,放你这,补一下,等下来拿。”
“老板,换个轮胎。”
“脚踏子坏了,换一个多少钱?”
“师傅,借气筒子打下气。”
据我观察,修自行车的,总共有三四个人。一对夫妇,大约五十多岁。男人瘦高个,由于常年屈膝躬身,背微微有些驼。女人稍胖,个子中等,短发,黑脸膛。秋冬季节,常年穿一件紫红的上衣。那上衣,在右侧腋下咧着大嘴,只在衣服下摆两寸处还连缀着,否则就该迎风飞舞了。黄绿色的裤子,膝盖处早已磨破,露出黑色浑圆的补丁,仿佛膝盖处顶了个圆球,在双腿间滚动。有时,她将这球压在身下,伏了身子到人力车底部,用力拧螺丝,一下,一下,再一下。然后,一阵沉闷的敲打声,将身边喧嚣的车流,自我的耳边拨弄开去。
还有个头发乱蓬蓬的青年,显然是个徒弟。他总在一声不响地低头做事,夏天穿一条短裤,光着上身。油污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黑亮的光。冬天则是一件灰夹克,沾满油污和灰尘,双手总也洗不净。
有次中午我去修自行车,他在低头做事,大约被老板喊去干另一件事,可手头上还有活等着他。“一天累到晚,还嫌不够,就是过去地主家的,也不会这样吧。”他低声恼怒地朝女人喊道。
我看到女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怔怔地,将本想说的话压下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昆德拉说:“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他们每日每日重复着枯燥简单的手工劳动,内心是忍耐还是感谢?
每次路过那条街,我不禁想:那个头发乱蓬蓬的青年,他会抬起头来看看蓝天,看看深秋街道上的银杏树吗?他是否会对此产生过诗意的联想?每天面对自行车,他是否会梦见飞翔?或者像对门理发店的小年轻一样,烫奇怪的发型,骑锃亮的单车飞驰过大街小巷?
终归要穿过生活,流水的日子看似平易。我只能从表面、从周围窥见别人的生活片影,无法深入其内核。
4
记得是12月4日,差三天进入“大雪”的时候,冷空气袭击了南方,气温一下子下降了8度。风猛力地吹着,在季节里守候的银杏叶子,大约也抵挡不住了,纷纷落了一地的金黄。仿佛一个声音低低地说:到大地中去,到大地中去。
那天中午,骑车去接儿子放学,他看到一地的落叶,惊喜喊道:“妈妈,快停下,快停下。多美的树叶,我要捡一些回去做树叶贴画。”
第二天,我打北园路走过,特意观察了那些银杏树,一片叶子也没有了,唯有黑褐色的枝干伸展在风中。季节流变,真正的寒冬来了。
我再瞟一眼缩在风中的自行车铺子,那几个身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