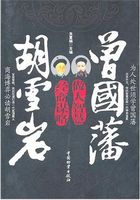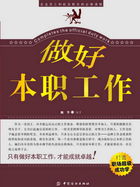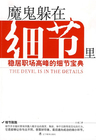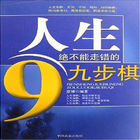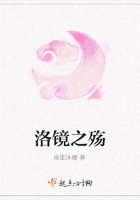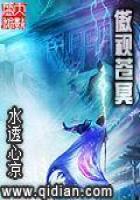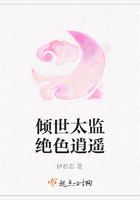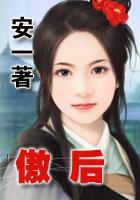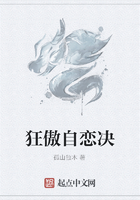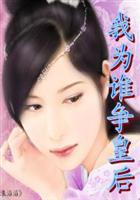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命运难以琢磨,命运弄人……无论什么人,无论生于什么时代,生命过程与生存环境,都会充满各种挑战,充满各种危机。因此,要想生存下去,要想使生命得以延续,忍耐几乎就是生活的常态。
1.生存的常态一一忍耐
说到忍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难以忍受和痛苦不堪。人降临到世间,就注定了要和忍耐结伴而行。忍耐作为生存的常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却又不尽相同,可谓千姿百态。
忍耐有大有小,大小之间得失尽现。寸土必争,见利就夺,不能让他人有所得,小便宜常占,功劳据为己有,搞得和周围人关系紧张,弄得自己工作和心情都不顺畅,真有点得不偿失。甚而有的人,就因一言不和而大打出手,造成的恶果有时十分严重。这不难看出,忍耐是何等重要又是何等不平常。
忍耐是无可奈何,是信念的坚守,是对人生感受的体悟,是艰苦和漫长的等待。
在忍耐过程中,不做出努力和付出的回应无疑等于承认自己失败,这种忍耐是十分消极的。忍耐常常又是无可奈何的。明明是自己上司的提议不对,不遵从就是不服从管理,且面临失职的危险;遵从了又面临着理性判断和人格尊严的双重考验。信念的坚守常常会在现实生活中面临残酷的问答。俗语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道理多数人都懂得,可真要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艰苦的忍耐和漫长的等待,常常是人为追求既定目标而做出的努力。
这种努力有的终成正果,有的却无功而返,这不能不说是人的造化和上帝眷顾垂青的所谓定数。机遇总是给有所准备的人,倘真如此,艰苦的忍耐和漫长的等待所做出的巨大付出,都终将云开见日。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其问的忍耐可想而知。从古至今有多少读书人曾在灯下苦读,孜孜以求,为的就是博取功名和出人头地。可在任何时代成功的总是少数人。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一个人已走向了成功,可多少人却在考取功名的漫长岁月中未建寸功,终身穷困潦倒。
社会发达的今天又如何呢?我身边就有一位仁兄。他在高考成绩揭晓之日,得知自己离本科分数线仅差几分时,自此智力急剧下降,后来参加工作当了光荣的工人。可上下班连过马路时都要让自己的父亲领着,可叹啊!可叹!还有一位为了考上大学连续复读了三年,总算梦想成真。后来在企业里从工程师成为中层正职。他们读书时都吃过苦,下过工夫,可自身对人生的理解及性格原因,又让他们走上不同的方向。忍耐是可贵的,可我们忍耐过程中所有付出得不到回报又当如何呢?做成任何事情都需有不同程度的忍耐,前提是必须有面对出现事与愿违结果时的心理准备。这就需要我们日常从多方位加强自身,包括学识、修养和身体等的修炼。
忍耐是有意的,又是无意的。昔日张良在桥上遇见黄石公,黄石公觉得张良是个人才,为了考验张良的耐性而故意把鞋子脱下来扔到了桥下,而张良若不是看他是个老头就要揍他一顿,而忍了怒气把鞋子捡回来给他穿上,黄石公验证了自己的眼光没错,便把兵书送给了张良,张良终成一位军事家,帮助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
当然,无心之忍,也是建立在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上。如果说忍耐是有意的,他又无不和功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现在的许多人发愤读书,农村的希望走出山沟,摆脱贫困;城市的希望将来考上名牌大学,面对当今竞争更趋激烈的社会,为日后谋得一份好的工作。
忍耐就是要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忍受常人不能受的罪。战国时候的苏秦去游说秦王,把身上的钱花光了,衣服也穿破了,却没被重用,家里的亲人见他回家也不予理睬。他发愤读书,头悬梁,锥刺股,日夜苦读,终于换来了荣华富贵。家里的亲人对他敬若神明,连老婆也害怕他的权势和富贵。可见人活在世上权势和富贵、贫困和无名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人生有了明确的目标,这过程中所受的苦和累,所受的耻辱就会在信念的光亮中坚持住。越王勾践成了吴王夫差的阶下囚,勾践把美女西施送给了夫差,并且自己和妻子给吴王夫差做奴仆,其间三年中从不倦怠。在夫差得病时亲尝夫差的粪便。忍耐,终于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夫差的信任和松懈让勾践得到了喘息乃至复仇的机会,最终把吴国彻底消灭。昔日刘备在种菜时,曹操还是看出了奇巧,试探说:论当今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事后也正如曹操的预言,刘备的隐忍和等待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反,而刘备却在不该用兵的时刻为了替自己的结义兄弟报私仇,不顾时机和诸葛亮的劝说,大兵出动,最后惨遭败绩,使蜀国受到沉重的打击,正所谓忍与不忍,祸福自现。
忍常人所难忍,最终目标得以实现,该忍时不忍最终酿成祸患。
忍耐常常和逆境为兄弟。人处在顺境时常常是踌躇满志,在想着下一步怎样大展宏图,在忙于和社会中的人交往和应酬,根本无暇顾及那寂寞的忍耐和对人生的冷静思考。当人生的轨迹发生质的改变,不由得让人产生新的思考和面对。说到忍辱负重,不由人不想到司马迁。司马迁在汉武帝朝议李陵的事时直言以谏,而招来劫难。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决然选择宫刑,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这种忍耐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留存的伟大,成就了人类不朽的著作《史记》。
司马迁的直言以谏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一时不忍惨遭厄运;他又用忍耐屈辱的极限,书写了历史和人生。难道人生的辉煌注定要和祸患结合在一起?
忍耐,是人生路上一个无法回避却又令人难解的命题。
2.国君生存中的忍耐
忍耐是生命与生存的常态,它遍布于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可人总有耐心不够、心情不好的时候,于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话:“没办法,谁让咱是小百姓呢?我要是当了皇上,我……”其实,忍耐是无所不在的,它既在百姓的身上,也在帝王身上。聪明的人会运用忍耐,而不是抱怨忍耐;愚蠢的人经常抱怨,却不会运用忍耐。学会忍耐,会使顺利的事情变得更顺利,会使祸事变小。
而抱怨除了能使情绪更加急躁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作用了。
忍耐往往是令人难受和痛苦的,有些忍耐更是让人刻骨铭心的。
同是一母所生的郑庄公和共叔段,郑庄公眼看着自己的亲弟弟一步步滑向远处,却没有在事发的前端而加以制止,他一再忍让,纵容着共叔段走向深渊。待到时机成熟时,郑庄公一举把共叔段彻底击溃,其中的忍耐令人深思。
春秋时,郑国的郑武公娶了申国姜姓女子为妻,她名叫武姜,生下了后来的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二人。郑庄公出生时难产,惊吓到了姜氏,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寤生,姜氏因此讨厌郑庄公,而偏爱共叔段。姜氏总想立共叔段为太子。为此她曾多次向武公请求,但武公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后来,武公死去,郑庄公即位以后,姜氏又向郑庄公请求把制邑封给共叔段。郑庄公对母亲说:“制邑,是一个险要的地方,虢叔曾死在那里,要是其他地方的话,我完全可以听从您的吩咐封给弟弟,可是这个地方不行,”于是姜氏又请求郑庄公将京地封给共叔段,郑庄公这次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将京地封给了共叔段,允许共叔段住在那里。从那以后人们便称共叔段为京城太叔。
郑国大夫祭仲对郑庄公说:“一般城邑的城墙如果超过百雉,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先王时的制度,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城则不能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超过规定的数量,与国家的制度不合。将来您一定会因此而有祸患的。”郑庄公对祭仲说:“我的母亲姜氏要这样做,我又怎么能够避开这祸患呢!”祭仲说:“您的母亲姜氏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不如早点妥善处置了共叔,不要让他的势力滋生蔓延。一旦蔓延起来,那就难以控制了。
蔓延的荒草尚且不容易清除,更何况他是您的爱弟呢?”郑庄公想了想,回答说:“多干坏事的人必然会自取灭亡。先生姑且等待事情的发展结果吧。”
不久后,太叔又命令地处郑国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地区听命于自己。郑国很多大臣听说后都对太叔的做法不满。公子吕对郑庄公说:
“国家不能容忍这种土地两属的情况,您打算怎么办呢?如果您要是想把君位让给太叔,那么我就请求前去侍奉他;如果您不是要把自己的君位传给太叔,就请您尽早除掉他。不要让百姓有疑心。”郑庄公说:“你不必急于这样做,他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会有他倒霉那一天的。”
后来,太叔又公开把那些地区划归为自己的属邑,势力一直扩展到了廪延一带。公子吕又去对郑庄公说:“现在是该除掉太叔的时候了,他的势力雄厚了就会得到更多的人力。”郑庄公说:“他对我既不讲君臣大义,也不讲兄弟亲情,即使他的势力雄厚了,他也必然会自取灭亡。”
太叔在他自己的封地修建城墙,积蓄财物,修造铠甲兵器,又准备了大量兵卒战车,准备袭击郑国的国都,他的母亲姜氏也准备打开国都的城门做内应。郑庄公了解到了他们叛乱的日期,就对臣子们说:“他们要攻进国都,这是大逆不道呀,现在才真的可以动手了。”
于是郑庄公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城。京城的百姓知道太叔想与郑庄公作对,见到郑庄公的部队来,都叛离了太叔。
太叔失去人心,军队也不愿为他效力,他只好逃走,到了鄢地。郑庄公又亲自统兵到鄢地去讨伐太叔。五月辛丑日,太叔又逃亡到共地去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郑庄公非常生母亲的气,便把他的母亲姜氏安置在城颍,并且向她发誓说:“不到黄泉之下,决不再见面了。”
可是事后不久,郑庄公又对自己的这一举动感到后悔。郑国的大夫颍考叔负责掌管边邑颍谷,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便带着礼物到国都来拜见郑庄公。郑庄公赐给他食物,而他在吃的时候却把肉剩了下来。郑庄公见了询问他,他回答说:“小人家里有老母亲,已经吃遍了小人供应的食物了,只是还没有尝过君主的肉羹,请允许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我的母亲尝尝吧。”郑庄公听了,十分感慨地说:“你有老母可以孝敬,唯独我却没有啊!”
颍考叔听到郑庄公的感慨,借机问道:“我冒昧地问问您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郑庄公便把自己的母亲帮助自己的弟弟要攻打国都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向颍考叔表示自己已经感到后悔对母亲说的那句“不到黄泉,不再见面”的话了。颍考叔说:“您何必为这件事情忧愁呢?如果挖地一直挖到涌出了泉水,你们母子在地洞里相见,谁又能说这不是在黄泉相见呢?”郑庄公听了颍考叔的话大喜,他果然照颍考叔说的那么办了。地洞挖好之后,他命人将母亲姜氏请到地洞之中相见。郑庄公进入地洞后赋诗说:
“这个大地洞之中,非常和乐啊!”姜氏出洞以后也赋诗说:“大洞之外,非常舒畅啊!”
从此以后,郑庄公母子俩和好如初。
《春秋》里面记述这段故事时,故事的名字叫:“郑伯克段于鄢”。用这个名字是含有深义的,它意思是说,共叔段不能顺从兄长,所以不能称他为“弟弟”;而“克”字原本指两个国家的君主在战,既然共叔段不像弟弟,那么写郑庄公与共叔段便用了这个“克”字。在这个名字里,没有“郑庄公”三个字,而是将郑庄公称为“郑伯”,这是在讥刺他对弟弟共叔段过于放纵、疏于教诲。历史上很多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郑庄公是故意在纵容弟弟,等弟弟越陷越深之后,再起兵讨伐,完全没有兄长对于弟弟的爱护。
郑庄公继承父亲的君位之后,成为了一国之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却在忍耐中生活了多年,他要忍耐的是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弟弟的宠爱。母亲为弟弟讨封地,他就得依从母亲之命给封地;弟弟违反国家的制度,他也要忍耐。大臣们看不下去,请求他制裁共叔段,他只是劝解说:“不必制裁,他不义的事做得多了,必然会失败的。
直到共叔段起兵谋反,他才下定决心发兵,将弟弟共叔段驱逐。虽然他一时气愤说不再见母亲,可是很快他就后悔了。在孝子颍考叔的帮助下,他终于和母亲和好如初。
也许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郑庄公早一些阻止弟弟共叔段,有可能会出现兄弟残杀、母子反目的局面,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
郑庄公的忍耐免去了兄弟间的互相残杀,又能与偏心的母亲和好如初,这对于郑庄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了。
可见,忍耐也是一囤之君的生存状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