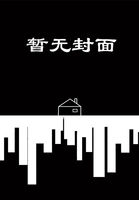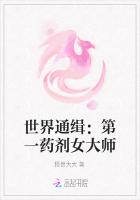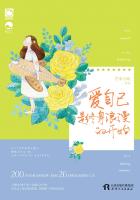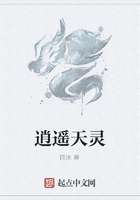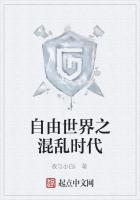三 俄苏文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
应该说,早期俄苏文论的译介形成了冯雪峰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对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冯雪峰来说有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认识其思想时不得不面对的。但应该指出的是,冯雪峰是在译介中学习,同时一边学习一边选择运用的,再加之俄苏和我国后来的社会形势复杂多变,这使其对俄苏文论的接受异常复杂,要准确地把握有比较大的难度。
比如就冯雪峰对托洛茨基的“同路人”思想的接受来看,柳传堆先生的论文《论冯雪峰与托洛茨基“同路人”文艺观之关联》【21】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清楚地揭示了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概括地说,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是可以想到的:
一方面是译介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即“影响源”本身并不单纯。就托洛茨基的“同路人”思想对冯雪峰的影响来看,这一思想在冯雪峰翻译的《新俄的文艺政策》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因为书中的内容之一《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部分的副标题是“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的议事速记录”。而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24年5月9日由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出版部长雅各武莱夫出面就文学艺术领域的政策问题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本身就是调解各方意见的会议,所以它最终形成的会议结论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要想清楚、准确地从中看出托洛茨基的思想来,难度很大。
另一方面是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即接受者的接受活动本身复杂。就冯雪峰来说,他接受托洛茨基的“同路人”观点在30年代初时就几经反复。“尤其是在译介《新俄的文艺政策》中,间接地或潜在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同路人’理论,并以之为武器,撰写过《革命与知识阶级》,用以回答中国‘革命文学’论争中必须解决的革命文学是否需要同盟者、谁是同盟者的问题。可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冯对‘同路人’理论的接受,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起伏的过程。在与‘自由人’的论争中,他开始偏离了‘同路人’理论,以更激进的‘革命’姿态审视对方。如以洛扬为笔名的《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原题为《‘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就彻底否定了第三种文学(即‘同路人’理论中承认的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存在的可能性。不仅批评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存在着‘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机械论’的错误,而且判定胡秋原的‘自由人’观点是‘反动的’‘托洛茨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等到论争快结束时,由于张闻天发表了《文艺上的关门主义》,他随即推出《并非浪费的论争》一文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左翼一向以来的态度,是并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并非要包办文学,它只要领导一切左翼的以及爱光明的人的文学去和一切黑暗的势力和文学斗争;他比任何人都最欢迎一切爱光明的人同路走;在清算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也决不肯忽视真正的朋友的意见。’尽管后来在政治观上是个彻底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是,‘同路人’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承认事物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他还是终身都坚守着,无论对敌对友,他的批评都较少简单化的论断。”我们之所以要引述上面一大段,是为了说明此问题的复杂性。但这一复杂性还不仅如此,因为后来由于托洛茨基的特殊命运,他在我国也成了不能提及的人物,因而冯雪峰在谈及自己对他的思想接受时,也有了可以想象的顾虑,这就更增加了讨论的难度。其实如果深入追究下去,牵涉到的问题还会更多。比如冯雪峰最早接受“同路人”的思想,与他彼时和施蛰存、戴望舒、苏汶等人的私人友谊有无关系?提及这一问题十分必要,因为冯雪峰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译介、学习俄苏的文艺理论的。诸如此类问题,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
这里,我们限于学养还无法进行如此复杂的讨论,只想以冯雪峰对俄苏文论中部分内容的接受,简单地提及俄苏文论对其影响的正反两个方面。
比如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的接受。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创始人之一,也是俄苏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于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人,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水平,一生写下了众多相当富有影响力的文艺理论著作。但其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理论上,普列汉诺夫主张从社会意义和美学特点两方面来评价作品,但是在实践中,他常常只强调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方面,而不能给作品应有的审美和艺术的评价。这种实际上的理论与实际的脱钩,导致了他过分地强调批评中的审美趣味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
对于普列汉诺夫本人,冯雪峰有很高的评价:“我们不妨说,现在俄国及世界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差不多都是从他那儿出来的。”【22】可见,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及其理论著作是非常欣赏和推崇的。具体到影响内容来看,首先,普列汉诺夫影响了冯雪峰革命文艺功利观的形成。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强调文学艺术思想内容的重要性,高度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比如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普列汉诺夫以大量事实说明,“文艺的功利性是普遍恒久地存在着的,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23】。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阶级社会里“没有一种文学艺术不是出于它的社会的某个阶级或阶层的自觉表现”,超阶级社会的艺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24】。而这种文艺观深深影响着冯雪峰,给其具体的文艺批评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基础。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这篇文章中,冯雪峰就是以普列汉诺夫在《文艺与生活》中的相关理论对苏汶的“文艺自由论”来进行批驳,从而也树立了自己坚定的革命功利观的。冯雪峰认为:“一般所说的‘一切的文艺都不是超阶级同时都不是超利害的,都是直接间接地做阶级的武器’的理论,是文艺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然而就是作者们主观上要超利害的,反对利害观点的如艺术至上派的文学——例如骂人生派为流俗、为愚人、为患瘰疬病的法兰西的戈谛野一派,实际上也依然一则并不能超阶级的,二则仍是利害的、功利的党派的。”【25】从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话就是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拿来批驳“纯艺术者”,证明文艺的功利性是普遍恒久存在的相关的观点和论证。
其次,在现实主义的真实观上,普列汉诺夫强调文艺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但真实又不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不能仅停留在“现象外壳的真实”,真实必须深入到“现象外壳”内部。也就是说,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深刻地描写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从而反映生活的本质,并指出,“当虚伪荒谬的思想成为艺术作品的基础的时候,它就给这部作品带来内的矛盾,因而必然使作品的美学价值受到损害”①。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见解,冯雪峰也是给予了充分肯定,如他在《论形象》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普列汉诺夫以为虚伪的思想是和艺术的形象不相宜,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艺术所追求的正是现实的客观的真实”②。正是这种主观上的认同才使得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类似于普列汉诺夫的现实主义理论,即偏重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真实的强调,重视文学的阶级性,重视其革命实践功能。也正是基于这种生活真实观,冯雪峰针砭了当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也使自己的文艺思想有别于当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左倾”机械论,为自己与概念化创作的理论斗争打下了最初的思想桩基。
自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中过于强调文艺与生产力、经济的密切联系,过于重视文艺的阶级性质,也具有一定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这些都对冯雪峰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因为还有苏俄的其他机械唯物主义文艺理论家也共同影响着冯雪峰,这就更使冯雪峰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了机械唯物论等的消极因素。
总之,以普列汉诺夫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苏文论对冯雪峰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积极意义来讲,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功利观,提高了冯雪峰的马列文艺理论水平和对文艺现象的正确评价能力,提供了对敌的有力武器。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些俄苏文论对其的消极、负面影响。
对这些内容,我们不准备详细去讨论具体的历史细节。只想进一步从宏观上提出一点:普列汉诺夫对冯雪峰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制约了冯雪峰一生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最终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其根本性的不足,这就是普氏没有完整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在马克思那里,文艺的阶级性质、革命功能不是只由文艺的真实性来决定的。在马克思的思想导师黑格尔那里,艺术创造是天才的活动,天才是借由对世界本体发展规律的理性直觉才把握到了美的。在马克思这里,最终扬弃私有制的革命活动,也不是只形成于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被剥削受压迫现实的清醒自觉和反抗要求,而是形成于无产阶级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地扬弃私有制的总过程的“理性直觉”。因而,文艺的阶级性和真实性并不只受制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现实、人的阶级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形成于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性直觉”。普列汉诺夫受制于当时对马、恩思想的认识水平,俄苏受制于其十月革命的成功源于偶然,并不源于对人类整个历史发展规律的理性直觉,这使俄苏的文学理论在根本上达不到马、恩的思想高度。这些也根本上决定了受俄苏文论深刻影响的冯雪峰的以及我国现代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最终高度。
注释:
【1】上海鲁迅纪念馆:《纪念与研究(8辑)》,上海:上海鲁迅纪念馆,1986年,第215页。
【2】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54页。
【3】冯雪峰:《创作随感》,见《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4】冯雪峰:《关于人物及其他》,见《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5】冯雪峰:《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学运动》,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6】冯雪峰:《题外的话》,见《冯雪峰论文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
【7】冯雪峰:《关于目前文学创作问题》,见《冯雪峰论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8】冯雪峰:《关于创作中的概念化问题》,见《冯雪峰论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6页。
【9】冯雪峰:《关于目前文学创作问题》,见《冯雪峰论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10】冯雪峰:《关于创作中的概念化问题》,见《冯雪峰论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
【11】冯雪峰:《论艺术力及其它》,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4-355页。
【12】冯雪峰:《论艺术力及其它》,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6页。
【13】冯雪峰:《民族性和民族形式》,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14】冯雪峰:《民族性和民族形式》,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1页。
【15】冯雪峰:《民族性和民族形式》,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2页。
【16】汪介之:《回望与深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17】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81页。
【18】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77页。
【19】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5页。
【20】艾晓明:《左翼文艺思潮探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21】柳传堆:《论冯雪峰与托洛茨基“同路人”文艺观之关联》,《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22】蔡清富:《冯雪峰文艺思想论稿》,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23】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0页。
【24】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9页。
【25】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