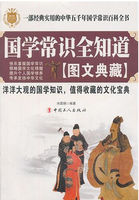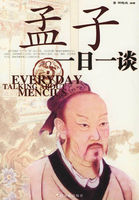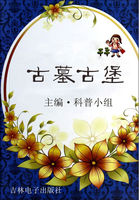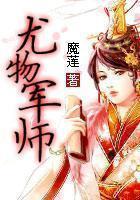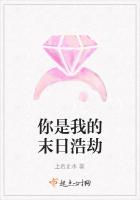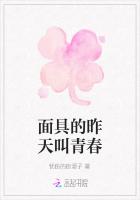第三节 传达鬼魅的中国传统文化含义
有学者对现代文学与中国鬼文化之关系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以为:“现代作家在社会思潮、个人观念等层面有鲜明的科学启蒙意识,只不过在文学的审美需要和民众的心理诉求方面对‘鬼’文化,有时不免采取扬弃与同情的文学态度。”【32】所言基本上符合文学事实,作家的现代观念与蒙昧鬼文化尖锐对立,一般来说,受制于科学精神,现代作家在思想上疏离、否定鬼文化,但在审美上作家又与中国鬼文化有血肉联系。具体到海派作家,应该说,他们在时代的大合唱中保留有自己的声音,或者说,这是一点杂音。虽然海派作家也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与启蒙意识,但他们并不是精英作家,他们对鬼文化有着民间式的理解,也就是说,在海派鬼文学里,作家无意于启蒙。譬如,邵洵美于1936年为他编辑的《论语》征“鬼故事”稿件,来稿居然以议论说理短文为多,这出乎他的意料。他最看好的稿件理当是《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一类的短文,一是《论语》适合登载这类小文章,二是市民读者爱好中国趣味的故事,三是他在《编辑随笔》中谈古人笔记,十分熟悉、喜欢说狐道鬼的故事。以上表明,邵洵美在意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艺术形式,而对鬼文化的保守性,他不倡导、也不反对。这或许能说明,海派作家无视科学启蒙与鬼文学审美之间的矛盾;其实,对他们来说,它也无所谓矛盾,因为他们不会将科学启蒙当作文学之重任,而神秘鬼文化则是文学的矿床。这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海派作家疏离并反拨了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新传统,以科学祛幻魅是新文学的一个特点,但海派文学延续了中国旧传统,叙述鬼的幻魅,可见,包容传统、反祛魅是海派鬼文学的一个基本倾向。
一、展现鬼文化的神秘
与科学拨开重重迷雾、探求事物的真相相反,鬼总是蒙着神秘面纱。鬼之所以神秘,在于它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中国人认为人死为鬼,如孔子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33】但对鬼的世界,人们其实很陌生,虽然人们往往按照人的意愿设计鬼社会,也有人言之凿凿,声称亲眼目睹过鬼,甚至与鬼打过交道,可飘渺的彼岸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这个彼岸就是冥界或阴间,它是一个包含了道教、佛教等在内的文化概念,确切地说,中国的鬼世界是一个基于世间又超越了世间的大杂烩。中国人又把鬼当作看不见摸不着的“气”,这在中国古代典籍如《淮南子》、《抱扑子》等多有记载。一些现代学者也以为,在古代,“气代表了鬼魂,气是魂魄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34】。“灵魂不是体内的‘小我’,也不是‘影子’,更不是‘蜜蜂’、‘白老鼠’、‘蜥蜴’等物,而是‘精’或‘精气’。”【35】鬼的精气说虽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可这无助于对鬼世界的把握,反之,在人们看来,鬼实有而虚幻。如袁枚《子不语·骷髅吹气》载:几位友人在下棋,一孙姓者困倦,就去东厢房睡觉。不久,众人听见他叫号,便去看他,发现他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喝过姜汁之后,他苏醒过来,说,在似睡似醒间,他看见一骷髅在向他吹气,并攻击他。【36】当然,鬼或许就在地底下,但鬼魂之类是气,气或魂魄的活动难觅踪迹,即使挖出了骷髅,可也奈何不了鬼气,总之,鬼是神秘的。
人在人世,鬼在冥界,但人与鬼仍可以交流、冲撞。叶灵凤小说《落雁》叙述:一个漂亮的少女因读过《茶花女》,当电影在上海上演时,她来到电影院看电影;她的交通工具是晚清期间流行的马车,而且,白马看起来很小;少年冯先生与她谈得很投机,电影散场后被邀约至她家里——一个十分幽僻的地方;被落雁称为父亲的人似乎对冯先生有他意,她设法让他出逃。冯先生终于逃到市区,坐人力车回到寓所,但在付车夫钱时,他终于发现手里拿的落雁所给的一块钱是冥币。鬼到闹市看电影,人到冥界与鬼交谈,这是一个现代传奇。这个故事或许不够神秘,徐讠于的《离魂》就很有鬼气。徐先生的妻子死于抗战之前,战后,徐先生回到上海。他遭遇车祸,失去知觉后,他遇上妻子,对他的到来,她很高兴,并为他准备了一间房子。当他躺在那间温暖的房里时,他又醒了,他在医院里。原来,所谓的房子,其实是妻子旁边的一块墓地,徐先生没死,代他而死的是同车的齐原香,她后来就埋在那里。出院以后,他去妻子的坟墓,发现鬼妻在哭泣。她在哀伤徐先生“来了”又“走了”,也就是他死而复活。人鬼相遇之际,天气转坏、下起大雨来,而且四周除了乱坟之外没有活物,妻子的手冰凉,七星婆一脸怪异,这是在冥界,还是在阴阳分际之处?还有,鬼妻居然要回苏州去,苏州是她的娘家,她是不是要去投胎呢?可见,鬼的世界,由于是人想象的,所以它类似于人世且与人世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人的丰富想象力又赋予它奇幻、神秘色彩,鬼终究还是鬼,是幽暗角落里的精怪。徐讠于小说《痴心井》虽然语言不离奇,但是,偌大一个园子,荒凉;一口痴心井,诡异;鬼虽然未曾露面,但游弋在园子里,隐藏在古井里。这份神秘感显然来自古代中国人对未知鬼魂的联想与想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它传承下来,海派作家以文学形式代言了民族文化。
《论语》“鬼故事”里的作者众多,且不都是海派文人,但作家在写稿时总得顾及杂志的海派风格。另外,除了约稿之外,作者所投稿件也不少,邵洵美从中选出了一些合胃口的短文登载。邵洵美选稿的标准是什么?有一段短文可以作为有价值的参考。“我生在一个旧式的家庭里,小时候又有一所很老很大的房子作为住宅;即使有相当的科学知识,但是环境却不由我对于‘鬼’不抱疑信参半的态度。我还有过几次极奇怪的经验,我曾经对不少朋友讲过,谁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答。”【37】在他看来,鬼或者有,所以,在“谈鬼”的《论语》里很难发现以科学精神否定鬼存在的文章。是意在启蒙的作者不屑写稿,还是写了而没有被采用?这两种情形都是可能的事实。以上论述能够说明,《论语》的“鬼故事”基本上没有超出海派文学的范围,将它们纳入海派加以论述不仅可能,而且也必要。
《论语》“鬼故事”多种多样,不少故事蕴藏有中国传统文化含义。如《鬼之种种》,作者讲述民间的各种鬼态,如鬼叫、鬼哭、鬼吃饭、鬼摸脑袋等,最活灵活现的是“鬼领路”。“我祖父”小的时候,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有一次他母亲生病,祖父月夜外出抓药,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迷失方向。后来,一盏蓝荧荧的灯引着他回家。这里的鬼通人性,他大约赞赏祖父之孝心,所以,好心有好报,祖父得到鬼的帮助。再如《小站》讲述一个前清官吏的鬼事,它寄寓有复仇、劝诫等含义。这名贪官受贿并按行贿人意志监斩一人,后来,他辞官回家,冤家路窄,他恰巧与受害人狭路相逢于一个小驿站。所谓受害人,也就是躺在棺材里的尸体。夜晚,鬼爬上楼来复仇,贪官十分惊恐,他跳到窗外,昏厥在树枝上。回家后,即使散尽钱财,他还是很快就死了。这些鬼参与人事、被赋予文化内涵,它们显然是人想象的结果:冥界的鬼能复仇、能以自己的方式助人,这神奇而魔幻。事实上,鬼总是奇幻的,人的想象力光顾过人不曾到过的领域,即便在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鬼怪却仍在想象力范围之内不减其丝毫魅力”【38】。古人幻想出神秘的人化鬼世界,《论语》“鬼故事”或许是一次有意图的鬼文化检视,至少,邵洵美的策划为各路鬼怪粉墨登场提供了机会,这在新文学中是很难得的。
鬼魂是气,所以,活人也可以离魂,但若离而不合,人就死定了。《离魂》里的徐先生在遭遇车祸后,那一口气本来已脱离躯体,但医院的抢救又把他的魂拉回来了,所以,他免于一死。鬼魂可离可合,这也意味着死人已发散的气能寄托在另一人的身上,古代中国有很多这类奇谈,《论语》“鬼故事”之一《一个女人》是它们的续写。学生吴的母亲死后7日,她的魂寄住在妹妹身上,妹妹的声音、举止皆如母亲。她又责备家里人太懒,一边骂人一边干活。做完,说了声“我去了”,妹妹就恢复原状,但妹妹对之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把离魂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当数徐讠于的《园内》。闹鬼的是一所老房子,以前花园里就有年轻漂亮的女鬼出没,在新主人进来之后,园内平静了一段时间。当主人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女亲戚——梁小姐寄住在这里时,园内又有幽魂。住在马路对面8楼上的现代书生李采枫,对梁小姐充满好奇、好感,不分白天、夜晚注视园内的梁小姐;他还用望远镜观察她、并给她拍照,又写信给她,但很可能因为生病的缘故对方没有理睬他。李采枫所看见的梁小姐可分为两种:一是白天的,她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是晚上的,就很神秘、虚幻。在她还活着的时候,不排除她于夜晚散步时被李采枫看见,但有时候极有可能是她的气——鬼魂脱离躯体溜进花园,因为她是那么轻盈、凄白,像薄纱、似淡雾。能够确证的一次是,她住进了医院,但于子夜,她又如轻风一般在花园里溜达。李采枫从英国留学回来,仍住在原处,仍夜夜看见梁小姐,但别人告诉他,她于半年前故去。综观小说,《园内》始终把梁小姐放置在神秘处,一是她从没有正面出场过,她只出现在李采枫的所见与他人的所说里;二是她夜晚的显身有如幽灵;三是她本来就是鬼魂。
以中国特色的冥界之鬼、脱离躯体的气作为叙述对象,海派文学较成功地传达神秘的中国鬼文化。鬼是一种幽灵、是气,它在神秘的他处,但它又经常出入人世间,它跟人神奇地联系在一起,任意闯入世俗生活,人的悲欢离合也因此而奇幻。科学祛魅,就是以科学精神或思维拨开鬼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虚无,但海派鬼文学则无意延续五四文学的科学祛魅精神,也不曾剖析民俗鬼,如鲁迅《女吊》式的以鬼性来弥补国民性,海派文学大体承续传统,鬼气弥漫是其特色。
二、凸显鬼文化的恐惧
鬼神秘发端于人的想象,人们之所以想象是因为人恐惧。人惧怕死亡、黑暗等,据此,人们幻想出彼岸的幽灵、精怪。自然,它们有着邪恶一面,与死亡、黑暗等联系在一起的幽灵有丑恶嘴脸。中国鬼的类型众多,其中有许多厉鬼或恶鬼,如无头鬼、吊死鬼、勾魂鬼、溺死鬼等,它们都属于谈鬼色变的类型。在中国人心目中,骷髅是鬼的象征。在张爱玲小说《十八春》中,曼璐被形容为骷髅,有恶、害人的特性。为了笼络祝鸿才,她合计后者霸占曼桢,这固然满足了祝鸿才的淫欲,曼桢也生了一个在曼璐看来能套牢祝鸿才的儿子,但这一切于事无补,因此,曼璐的所为堪称损人不利己。有的鬼看似平常,其实也很凶残,如《落雁》里的“父亲”。还有名声不错的鬼也杀人,徐讠于小说《痴心井》叙述一大户人家代代出痴心女子,到头来她们都会精神失常,最终都跳入井中自杀。为什么总有人逃不脱因情而投井的命运,难道井里有痴心鬼?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人们不得不把井填埋掉。
或许因为鬼之恶、厉,所以,人有怕鬼的心理。邵洵美的《闻鬼》一是写老宅闹鬼,鬼就像一缕冷气一样飘在房间,这让人毛骨悚然;二是写在所租的住房里听见鬼的脚步声,每次听见这种无人的脚步,他头发似乎都竖了起来。在《论语》的一则小故事《一个女人》里,吴姓学生讲述鬼故事,到后来,讲者与听者都疑心鬼就在门外,以至他们一夜惊惶、未敢入睡。这些作品凸显了中国人的怕鬼心理,他们恐惧魂灵,它们或许会加害于人。
另外,中国人怕鬼还与他们将遇鬼视为不吉利的征兆有关。当然,这种心理或许与鬼之恶分不开,因为恶鬼伤害人,所以,人碰上鬼就倒霉。他们以为鬼或与鬼相关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先兆,它必然有应验,即霉运当头,这就是“人且吉凶,妖祥先见”【39】。这种鬼恐惧牵涉中国人的兆应文化心理,所谓“兆”,指的是前兆、预兆;“应”指的是应验。中国原始文化中的兆应往往是一种迷信,它指向的是:可能毫无联系的事物或人与物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兆是因,应是果,之所以如此,在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控一切。在这类鬼作品里,遇鬼是因,坏运气是果,所以,遇鬼使人恐慌。对这种心理的探求,施蛰存是一个有心人,他的几个小说与散文当推为代表之作。
在散文《鸦》中,施蛰存先记述自己先天性的闻鸦鸣而生悲凄;稍大一些,便将鸦当作生命终结之预兆。后来,他与一个行色凄惶的女子同路,她听见鸦叫而色变,不祥的先兆笼罩着她。接下来,他思考中国民间为什么将鸦作为不吉的鸟,他走的是文化考古的路子,用的是科学的方法;并且,他还进行中外比较,美国诗人爱仑·坡有一首《咏鸦诗》,也写得很凄寂。这篇文章创作于1930年,或许,他对鸦的理性分析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从他在思考问题时所运用的方法、所具有的开放意识来看,他是一个有潜质的民族文化研究者。他还将不祥的乌鸦写进几篇小说里,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篇是《鸠摩罗什》。大智鸠摩罗什是一个道行很高的僧人,但他放不下色,尤其依恋表妹的仪容。他们成婚之后,他的佛光暗淡。妻子深知其中缘故,她自哀自怨,以至在抑郁中死去。下面是她临终前的场景:“这时光,已经是垂暮了。傍晚的风吹动着木叶,簌簌地响个不停。乌鸦都在树上打着围,唶唶地乱噪着,一缕阳光从树叶缝中照下在她的残花的脸上。”乌鸦意味着死亡,是幽灵,这是散文《鸦》里多次出现的景象,现在,鸦是她死亡的前兆。由以上所述能发现,鸦之凶兆是施蛰存的一个心结,他以直觉感受它、以理性剖析它,他通过乌鸦来透视民族鬼文化心理的意图很明显。
当我们说“真是遇到鬼了”时,它表明当事人走霉运,也意味着鬼是一种恶兆,施蛰存的《魔道》再现了这种情况。一个男人坐火车外出旅行,在火车上,他遭遇鬼了,或者说他自以为遇上鬼了。这个黑衣老妇人看起来很像魔鬼,她的脸上有“邪气的皱纹”,五官里充满了凶险,她看人的眼光阴险,而且,她还很神秘。尤其使人恐怖的是,他和老妇人面对面坐着,其他人就不来这里的空位坐了,而且,老妇人也不去别的空位坐。这显然在暗示,鬼找到他了。它果然是凶兆。在小说的结尾,厄运终于降临,他三岁的女儿死了,这个时候,他“看见一个穿了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踅进小巷里去”,她在达到目的之后走开。还有,她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魔鬼,她有外国文化内涵,如欧美的、古埃及的,她的丰富性体现出施蛰存有开放的胸襟,但这显然也与施蛰存已有的文化心理有关,否则,面向现代的他未必会接纳陈腐的巫术文化。与《魔道》相反,《夜叉》里的“女鬼”一身白衣。夜叉来自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成为恶鬼,因此,当胆大的他撞上白衣“夜叉”之后,他力图剿灭对方,她是凶兆,可能还杀人,只有将她压垮,他才平安。不过,与《魔道》不同,夜叉其实是一个聋哑女人,这正如王充所言:“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40】或许,《魔道》里的黑衣老妇人也只是心魔,但为什么他三岁的女儿就死了?看来,鬼似乎存在,作为恶兆的鬼似乎也存在。
《魔道》将旅行人因不好的征兆而引起的恐慌、焦虑、等待等心理尽情地展现出来,显然,它运用了现代小说技巧。在惴惴不安中,他的思绪翻腾起伏,他幻想她是能攫取人灵魂的魔鬼、会魔法的妖婆。黑衣妇人无处不在,当他眺望窗外时,她在窗前面的一片竹林里,但她有可能是窗玻璃上一个黑点的幻化。他甚至将所见到的一切可疑女子都当作妖妇,在他的想象中,性感多媚的陈夫人也被老妖妇所控制,而都市里的咖啡女子则变成陈夫人,她也是老妖妇的化身。黑衣妇人从老而丑质变为埃及艳后、陈夫人及咖啡女的漂亮、性感,在他看来,这些变化都是妖妇的手段,是她诱惑人、从而扼杀人的伎俩。总之,自从他把黑衣妇人视为不祥的预兆以来,她就一直占据着他的内心,显然,他无法摆脱她的阴霾,这表明,他一直生活在恐慌中。他又因恐慌而焦虑,因焦虑而等待,“她会将怎样的厄运降给我呢?我会死吗?”黑衣妇人成为难以承受的心头之重,以至他不讳言死亡。综观《魔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征兆激发一个人内心的千层涟漪,先兆与精神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施蛰存将先兆引入现代语境下,人的精神错乱、意识与无意识冲撞、交织的导火索是先兆;另一方面,他又将精神分析置于兆应文化现象中,在史书或小说里,兆应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常常只是在故事的发展中得以凸显,而《魔道》里的兆应文化心理有可感而丰富的意识流程,这是精神分析的优势所致。可见,兆应借精神分析使得小说完成一次质变:由情节小说转换为心理小说。
滕固的《死后应验》是另一种类型的鬼恐惧。在不知情人看来,叔叔秀丁揭发了寡妇——侄媳四娘的婚外情,有孕在身的四娘被逐出。她无处可去,溺水而亡,而秀丁也不久病故。所以,村里人以为秀丁的死出于报应,也就是佛教的因缘果报。其实,这件事另有隐情,知情人只有秀丁与四娘,他们也是当事人,四娘为了保全秀丁而一个人承担罪责,他正是在四娘的鼓励之下检举的。秀丁因愧疚而自责、病亡。这个小说有较强的反礼教意义,但“死后应验”也揭示了中国人的蕴涵有佛教内涵的鬼恐惧心理,虽然在真相的映照之下它显得荒诞可笑。
上述鬼恐惧作品再现中国人怕鬼的心理,包容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含义,尽管个别作品也有一定的现代意义,但在整体倾向上,它们的精神是传统的。鬼恐惧表明,人对幽灵无知,他们更没有以科学思维来烛照幽暗处的鬼魂。科学不是万能的,“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自然现象尚未被人们所完全认识”【41】,但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弥补知识上的欠缺,如在古代,无鬼论者代代有人。可不少海派作家多少有些依恋中国鬼文化,无论出于作家本心还是艺术或媚俗的需要,鬼恐惧叙事体现海派文学对传统的包容。诚然,这有悖于现代思潮,但文学如果脱卸启蒙功能、专注于无功利的审美或消闲的娱乐,海派文学的有容乃大或许是一种优势。
三、再现鬼文化的可亲
作家邵洵美对鬼文学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中国的鬼故事和外国的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则是神话,或则是讽刺;而后者则能彻底表现鬼的恐怖。”【42】这或许能说明,中国的鬼有阴暗可憎的,但十足可亲的鬼也举不胜举。后者的集大成者为《聊斋志异》,它一是将人与鬼狐之情演绎得缠绵悱恻、美丽动人,二是以鬼话来反衬人世之黑暗,这类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难怪邵洵美说:“我国旧有笔记,谈鬼狐事者极多;谈狐的虽媚,而谈鬼的却并不可怕,翻遍《聊斋》,仅《画皮》一篇。”【43】中国鬼故事中的可爱鬼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神话形成的中介,就是鬼话,离开了这个中介,就没有了神话这较高一级的艺术形态。因为人死后,第一阶段是变成鬼,然后再从鬼中分化成善鬼(即神)和恶鬼”【44】。鬼话是否是神话的中介姑且不论,远古时期确有善鬼,如刑天、精卫等。这类有不屈意志的鬼常常以复仇的形象示于人,在民间颇受欢迎,如《聊斋》里的席方平、鲁迅先生所说的“女吊”、《小站》里的“冤鬼”等。随着道教、佛教思想的介入,“轮回”、“三界”等范畴扩大了鬼活动的空间,鬼跟人越走越近,至少,有时候鬼能较为自由地在阴阳两界活动,因此,在中国鬼话,善鬼可亲与厉鬼可恶一般相提并重。
海派文学中的鬼可爱叙述基本集中在人鬼恋情上。落雁是一个风雅多情的都市鬼。在九月深秋的静夜,她跑到人间来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她遇上少年诗人冯先生。或者,孤独多愁、百无聊赖的他正在等待一场艳遇,他惊诧于她美丽的脸庞、诱人的眼睛,她似乎也有意,故意掉下白手巾。诗人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手巾便成为他们结识的媒介。他们谈西洋小说、电影、诗歌,才郎貌女随即一见钟情,所以,她邀请冯先生去宅第叙谈。如果不是爱狎少年的雄鬼有劫掠冯先生之意,人鬼恋将有进一步发展。如果说落雁的美可以触摸,那徐讠于《园内》里的女鬼之美始终是虚幻、诗意的。李采枫似乎一相情愿,他能远观女孩或女鬼,但她不给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而且,小说主要描写月下花园里的她,美得奇异、脱俗、如梦似幻。另一方面,女鬼好像又跟李采枫心有灵犀,她常常在他需要的时候进入他梦中,出现在花园里。无疑,这两个女鬼又有共同点,她们既美丽多情,又心地善良,还与人演绎一段纯粹的爱情故事。这些(包括《鸠绿媚》、《鬼恋》等在内)人鬼恋小说展示了中国鬼文化中最精彩、最优雅、最浪漫的一面,即善鬼可亲、鬼能与人发生超越界限的畸恋。
叶灵凤的《鸠绿媚》讲述一种经过形变处理的人鬼恋。作家春野接受了朋友送的一个瓷质骷髅,据称,小头骨是原波斯公主头骨的仿制品。波斯公主鸠绿媚在生前与教师白灵斯相爱,但国王反对,他辞退了这位异域老师,并把她许配给亲王。在结婚的前夜,公主乘人不备自杀,后来,白灵斯千方百计带走了公主的骷髅;再后来,骷髅被带到巴黎,并被仿制,春野的朋友得到其中一个。小说的诡异在于,当春野把骷髅放在枕边,他能以白灵斯的身份进入梦境与公主见面。这表明,骷髅即便是仿品,公主的灵魂仿佛也寄住在上面,因此,一场超时空的人鬼恋奇迹般地得以出现。应该说,无论在精神或艺术形式上,《鸠绿媚》都有丰富的现代意义,但是,骷髅所凸显的中国鬼文化含义、鬼可亲的文化心理是作家展开想象、建构小说的基础。
施蛰存小说《将军的头》也是一种奇特的人鬼恋鬼话。花将军是一个有着复杂人格的人:他有藏人血统,但他是汉将且爱上汉族少女;他是将军,按军法杀了骚扰少女的士兵,但他也在骚扰少女。在认同的身份与汉人少女之间、在军法与爱欲之间,他都选择后者,理性无法掌控欲望,所以,他说即使自己被砍头、肉躯也要找到她。肉欲驱使下的话语,不是豪言,是谶言。因为有了这句话,故事的走向就已确定,小说的魔幻色彩也由此而来。显然,纯粹欲望驱使下的行为借助了巫文化,如果不是谶言,将军的话语就是无法落实的誓言,是谶言使得他完成誓愿。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一语成谶不能没有中国鬼文化,人死为鬼,无头将军是鬼,因此,可以下的结论是,他生前死后都爱汉人少女,死后之爱是生前之爱的延续。或许,与其说鬼可爱还不如说将军人可爱,他对少女痴情导致了无头将军的超凡行为,所以,《将军的头》毋宁说是人话而不是鬼话。
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人鬼恋”当数徐讠于的《鬼恋》。与上述小说不同的是,自称为鬼的是人而不是鬼,她把自己设计为鬼并按鬼的样子生活,她的奇异、高贵脱俗的美打动了徐先生。他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事实上,她也爱他,但她仍然愿意独自做“鬼”,不想回到人的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她竭力逃避这段“人鬼恋情”。这个特别的“鬼”为什么不愿做人?原来,她是一个经历非凡的女人,曾是革命者,杀过人、蹲过监狱、爱过人、又流亡国外,当她回国时,现实让她失望,告密的、卖友求荣的都得到升迁,真正骨头硬的都死了,这使得她宁可做鬼。鬼可爱而人世可鄙,作家的这种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谈鬼神》一文中就有所显露:“感到社会之到了绝境,尽量享受一时之快乐,极力探求鬼神之显灵。冤屈的求报应,惨毙的求超度,活人们要降福,这些都是社会问题的虚悬,人民的力量无发挥的地方,把一切依靠于渺茫的神鬼去了。这是目前的中国。”【45】做鬼的选择除了寄寓有作家的批判精神,它还体现出“女鬼”对人生的理解有一定的形而上意义,在她看来,她什么样的人都做过,也算“曾经沧海”,故而宁愿做鬼。所以,《鬼恋》是一个融浪漫人鬼恋情、现实批判、人生哲思于一体的通俗小说,从这个角度看,推它为现代鬼小说的杰作当不过分。
以上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鬼故事再现了中国人鬼可爱的文化心理,从科学精神上看,它们未免不够入时,但在审美趣味方面,这类故事承旧而创新,拓展了现代文学的审美空间。正如邵洵美所言,这类故事在中国古已有之,海派文学则在都市语境下继续展示中国鬼文化的独特之美。在上海,通俗的爱情——鸳鸯蝴蝶式的故事极为流行,鬼文化就如同作料,它的加入增强了小说的奇幻色彩,叶灵凤的《落雁》、《鸠绿媚》,施蛰存的《将军的头》,徐讠于的《园内》、《离魂》、《鬼恋》等把中国的“鬼可爱”演绎成现代传奇,自然它们莫不是市民读者的文学盛宴,尤其是《鬼恋》,风行一时。显然,鬼可爱作品在美学与市场方面都是成功的,美中不足的是,它有悖于时代精神。不过,以单一的科学精神来统御文学并不足取,虽然这在特定时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但科学思维在破解鬼魅之奇幻后,也消解了鬼魅所蕴涵的奇幻之美。而海派鬼文学则跳出了科学至上的怪圈,它宽容传统,在承续传统审美情趣的同时,还洒脱地超越了启蒙精神的夹缠,海派文学精神的混杂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语
诚然,海派鬼文学中也有一些以科学精神祛除鬼幻魅的作品,但这不是主流。从有影响的小说以及反响很大的《论语》鬼故事来看,海派鬼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拨了五四崇尚科学的精神,在作品里,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颇为紧密,它蕴涵有传统文化含义。如果说现代化存在有一个祛魅化过程,即“是指把神对人世和命运的责任发还给人,宗教的神学观念被人的理性观念所取代”【46】,在新文学里,五四确立了一个祛魅的传统,海派鬼文学则在特定程度上将人的命运交给了神鬼,这是反现代化,反祛魅、传统化的。上文三个方面的鬼幻魅论述可能简化了中国鬼文化的内涵,但由于论文无意对鬼文化做深刻而系统的剖析,而只是探讨海派鬼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包容,并由此探究海派鬼文学复杂的精神特征,所以,论述鬼魅的传统想象并未涉及中国深层次的鬼文化。但这也足以表明,海派鬼文学偏离了五四新文化轨道,在精神上它欠缺现代的理性,更没有科学之光,从实质上看,鬼文学没有剥离、批判民族的鬼文化心理,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仍与鬼魅混杂、纠缠,这种反现代、反祛魅的文学在最具现代性的都市盛行就值得研究了。
海派鬼文学之所以包容传统、反拨科学祛魅,在于海派文学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学,它的生产与存在基于市民的文学消费,而市民的文学趣味难以超越传统文化精神。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须历经漫长时间的积淀而成形,同样,它的解体也非片刻而就,新文化人自觉地以西学解构传统的实践轰轰烈烈,这也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体现,所以,鲁迅等许多人的鬼魅形象是现代想象,但市民文学就止于传统。邵洵美办《论语》杂志十分在意读者的趣味,连续两期的鬼故事是市民的文学大餐,所以,《论语》鬼故事多数是地道的中国鬼故事。
对海派鬼文学,不能以不科学或违背现代精神简单地予以抹杀。文学除了启蒙功能,还有审美与娱乐功能,这是海派鬼文学存在的理由,同时,科学祛魅,意味着奇幻之美的丧失,反之,反科学祛魅就是文学幻魅之美的复归。
注释:
【1】《大学·中庸》,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3】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4】贺仲明:《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第184页。
【5】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6】刘雨:《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与文学的精神还乡》,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96页。
【7】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冯仙丽、杨路红:《都市梦魇下的精神还乡》,载《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77页。
【9】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3页。
【10】旷新年、马芳芳:《从出走到回家》,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第62页。
【11】《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281页。
【12】《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390页。
【13】《孝经》,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
【15】《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页。
【16】《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页。
【17】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8】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19】朱晓进:《鲁迅的佛教文化观》,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1期,第8页。
【20】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21】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3页。
【22】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23】[瑞士]荣格著:《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卢晓晨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24】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3页。
【25】圣严法师:《拈花微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页。
【26】《杂阿含经》(上册),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27】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28】萧相恺:《宋元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29】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30】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4页。
【31】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103页。
【32】肖向明:《幻魅的现代想象》,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版,第43页。
【33】《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467页。
【34】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35】赖亚生:《神秘的鬼神世界》,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36】袁枚:《子不语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37】邵洵美:《闻鬼》,载《论语杂志》第91期(1936年),第921页。
【38】[英]艾仑·C.詹金斯:《鬼文化》,郝舫、金淑琴、杨卫民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39】王充:《论衡》,岳麓书社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40】王充:《论衡》,岳麓书社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41】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2】邵洵美:《编辑随笔》,载《论语杂志》第92期(1936年),第1018页。
【43】邵洵美:《编辑随笔》,载《论语杂志》第91期(1936年),第938页。
【44】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45】徐讠于:《文学家的脸孔》,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46】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