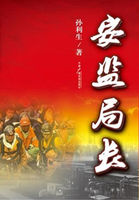大宝回学校后,心情非常沉重,仿佛雪萍家的不幸就象自己家的不幸一样。是的,他家也遇到过这样的不幸,也遇到过这样的悲痛,他把两个家庭的不幸联在了一起。那是在三年前的一天过午,妈妈被汽车撞死的噩耗传来,他一下子昏了过去,醒来之后,趴在妈妈的身上又哭昏过去。后来肇事者赔了四万元钱。父亲王有全以王大宝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一直没动。“爹,我想和你商量个事。”王大宝放弃了高考前紧张的自习,请了假。过午跑回家对爹说。爹问:“什么事?”“我有个同学他爹得了癌症,想借一万块钱治病。”王大宝没敢说出雪萍爹已经死了。爹说:“这钱不能借,这是你妈留给你的卖命钱。”“爹,咱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人家一年二年就还咱的。”话触起了爹的痛处,爹紧闭着嘴唇不语。大宝乞求地望着爹,眼里流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好久爹擦了擦眼,长叹一口气,点点头,把抽屉钥匙扔给大宝。大宝到银行提出了一万元钱,用李雪萍的名,存了活期。他把存折送到李雪萍家时,李雪萍守着昏迷不醒的娘。“雪萍,这是我借给你的,我没有母亲了,你无论如何可要把你母亲的病治好。”雪萍用泪眼望望大宝,摇摇头。“雪萍,你相信我,我没有恶意,我是借给你的。”说完,大宝把存折扔在床上,雪萍没说要也没说不要,泪水啪啦啪啦地落在盖着母亲的被上。大宝转过身,一言没发,象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挺起胸,大踏步地走出门去。
离开学校,离开了老师,离开了同学们,雪萍感到孤独。当母亲身体有所好转时,她的心在教室里。她恨不能马上回到学校堅读书,回到热闹的同学们中司去,可是她看看虚弱的母亲,想思家里欠的债,继续上学的心死了。几天来,不少男女同学都来看她,她很感激,并道谢。三天后,一个下午,王大宝又来了。雪萍投去感激的目光,并向母亲介绍说:“这是我的同班同学,就是他借给我们钱的。”母亲依在被上望着大宝那副憨样,心想,世上还真有好心人哪!她叫雪萍快拿板凳让大宝坐下,又催着给大宝倒水喝。大宝说:“雪萍,不用忙了,我来看看伯母,还要马上回学校。伯母,你好好养几天,我走了。”娘儿俩望着走出去的大宝,心里各自想着心事。娘想,有这么个好心人做女婿该有多好。雪萍则想,没想到平时不大善于表现自己的大宝心底这么善良,在别人危难之时会有这样的举动。而那些平时对自己甜言蜜语,甚至信誓旦旦的富有子弟却无声无息了。这使她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产生了新的衡量标准,对王大宝的认识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憨、不傻,他实在、善良。雪萍想起王大宝平时在学校里的表现,由感激到好感,还有一种暂时还说不出的爱慕意识在心里流动着。又过了几天,娘慢慢地下床走动了。她拿出一个小本子交给雪萍。“萍,这上边是你爹治病时借款单,既然大宝的钱不等着用,就先还别人的。”雪萍算了算,共八千多元,二十几户,她把大宝借给的钱从银行提出来,挨家挨户还款。雪萍到别人家还款时,人们都很奇怪,猜不出李家到底从哪弄来这么多钱。当还给西邻快嘴吕大婶钱时,吕大婶开口就问:“雪萍,你这是你娘给你要的彩礼钱吧。”当场把雪萍羞得满脸通红,她结结巴巴地说了声不是就回家了。第二天满街都从吕大婶嘴里知道雪萍用彩礼钱还债。这话从家长传到学生嘴里,传到学校里,几个同班同学就议论起来。一天,王大宝来雪萍家,大宝说:“雪萍,我今天是来给你送个信的。”雪萍问:“什么信?”大宝说:“我会考已过了关,不想参加高考了。”雪萍问:“为什么?”大宝说:“我爹那么大年纪了,身边没人照顾不行。”雪萍说:“你还是个大孝子呀。”大宝问:“大婶近来怎样了?”雪萍说:“托你的福好了,今天出去闯门去了。”大宝见雪萍母亲没在家,说话胆子就有点大了。“雪萍,听说你找婆家了?”雪萍问:“谁说的?”大宝说:“同学们都说你向婆家要了彩礼钱还债。”雪萍脸通地红了,说:“大宝,你信?”大宝说:认家都这么说。”雪萍说:“我问你信不?”大宝一时语塞,用手摸着后脑勺,两眼直瞪雪萍。雪萍用手指戳了一下大宝的脑门说:“傻样,那彩礼钱就是你借给我的那一万元。”大宝的脸也变成了紫茄子,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腔,爱情的火花突然在两双眼上碰撞。雪萍两手勾着大宝的脖子,象看陌生人一样看着他,然后把两片薄薄的小嘴唇放在那张宽厚而笨拙的嘴上。
娘儿俩回到家,雪萍把老黄牛和小花牛拴好,上了草料。娘就忙着做饭。刚坐下,快嘴吕大婶来了,说:“嫂子,上里屋和你商量个事。”雪萍看吕大婶和娘进了里屋,知道有秘密事要说,就坐下替娘烧火。边烧着火,雪萍脑子里边琢磨。吕大婶来,准又是为我和大宝结婚的事。想着想着,不由得脸红了。人一到了这个年龄,脑子就爱向这方面考虑,尤其是女青年,脑子特别敏感,心里也特别容易激动。其实吕大婶这次来,不是为雪萍的事,而是来给她娘柳树娥说媒的。吕大婶她娘家门上有个当教师的远房哥哥,因媳妇与校长通奸而办了离婚手续。他打听到树娥心底善良,人又漂亮,就托吕大婶来说媒。这人师范毕业,四十八岁,小树蛾一岁,按说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树娥考虑来考虑去,说定不下来,得和女儿商量商量再说。吕大婶一走,娘红着脸走出来,一看雪萍,脸色更红,雪萍预感到娘给她谈结婚的事。娘说:“雪萍,你知道你吕大婶刚才来说啥?”雪萍心里咚咚地跳,嘴有点发抖的间:“娘,她说啥?”娘说:“我不瞒你,她一个远房哥哥离了婚,托她来介绍我,你说,娘该咋办?”雪萍一听,脸嗖的一下冷下来:由红变白。说:“娘,你自己的事,你说了算,女儿不干涉!”雪萍说完,一腔悲哀涌上心头,跑进里间哭起来娘跟进来安慰说:“萍,娘话没说完哪,娘这辈子不想离开你,不会对不起你,也不会对不起你爹,娘不会走,这你就放心吧。”“娘!”雪萍望望娘那清秀的面孔,孩子似的扑进娘的怀里,娘抚摸着女儿的头,长长地叹了口气。“隆隆隆……”街门前,一阵摩托响雪萍去开门,见是大宝来予,有意地大声招呼一声:“娘,来客了。”娘理了理头,用小手巾抹了一下脸,迎出来,“大宝;快屋里坐。”大宝说:“不用,伯母,我先帮雪萍喂牛。”雪萍说:“你别牛头晒裤子——假充(角撑)好营生。”又小声对大宝说:“纠正多少遍了,怎就改不过称呼来,叫娘比上天还难。”大宝说:“叫顺口了,忘了”雪萍说:“重新叫去”。大宝只得到屋里去没话找话地说:“娘,别忙活了,简单吃点饭就行了。”娘说:“我烙了几张油饼,只是没有菜。昨天,南街上来了个烤烧鸡的,听人说是青岛那边的知了猴烤鸡,远近很有名的,我去买只尝尝。”说着,娘就走了。娘走之后,就是大宝和雪萍的天下。大宝急不可耐地跑到牛棚,搂着正在拌料的雪萍就亲。二人舌来舌去的亲着,象两只草蛇吐舌芯子。雪萍见小牛抬起头直瞪他俩,草也不吃,就笑着对大宝说: “快松开我,看,小花牛都笑你了”。说完小花牛真哞哞地叫了两声。大宝说:“你家的畜类也这么有灵性。”雪萍说:“是啊,快松手吧。”大宝说:“我不怕,我不怕,让它学学,其实牛更爱亲呢!”说着,又搂紧雪萍亲起来,两颗心,一左一右;咚咚地弹跳着。
自那次雪萍大宝定情之后,大宝来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毕业后,农时一有空,大宝就骑着那块“雅马哈”来了。雪萍对大宝的爱也越来越深。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缘故吧。过去在学校时,雪萍对大宝的言谈举止,形象肤色看不好的地方,现在都把弱点缺陷看成了优点。你说他脸黑,她说是黑是健壮的标志,白面书生,弱不禁风,在庄稼地里是不顶折腾的。你说他脸长,她说是长脸长寿,驴年马辈子嘛。你说他嘴大,她说嘴大吃四方,福相。有一次她问娘:“娘,你看王大宝这人怎样?”娘知道女儿的心思,就说:“人好,心眼也好,如今的青年人象大宝这样全美的,恐怕百里挑一。”雪萍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又说:“娘,你说的这是真心话?”娘说:“真心话,我若是摊上这么个好心底的闺女女婿,可就是天官赐福了。”娘怕雪萍嫌大宝长得丑,又嘱咐说:“为人过日子,就得靠心眼好,有个好模样也当不了吃喝,心眼好好一辈子,模样好几年就拉倒了。你看东疃西疃那些小白脸,三年结两茬婚。”雪萍说:“娘,你别絮了,这些我都知道了。”娘看出女儿愿意,就说:“你们虽是同学,可无媒不成亲,我去找西屋你吕大婶当当媒人,看人家他爹愿不愿意。不过,临提亲之前得还人家部分钱。不要让人家认为咱还不起钱来提亲的。”雪萍说:“上个月我想还大宝五千元,大宝不要。”娘说:“你和他说,亲是亲,钱是钱,借的是借的,给的是给的。茄子葫芦不能一锅煮。”雪萍说:“我也以大宝的名义给他存上了,剩下的到秋再还。”
快嘴吕大婶嘴快,腿快,耳朵长,有人背后叫她“快嘴驴”。早晨她睁开眼就中门子,全村鸡拉的狗屎的,都瞒不过她的耳朵,那嘴象把堵不住的漏勺,孬事好事经她一加工,满村里都能听到。可她又是个热心人,谁家有了事找她,动嘴动腿她都肯帮忙。树娥找到她,把雪萍和大宝的事一说,她立马追镫地去了王家。王有全说:“孩子的婚事我不管,他们自己愿意就行。”这戴双方老人没意见,婚事也就定下来了。雪萍大宝两人同岁,在农村按晚婚规定,女方满了二十三岁零一个月就可以登记结婚。不一会儿,树娥提着两只烤鸡回来了。大宝过完了吻瘾,板板正正地坐在小凳上。见丈母娘回来了,忙起身说:“娘,我又不是外人,买鸡干啥。”娘说:“正不是外人才自己吃呢。买了两只,这只咱吃,那一只给你爹捎去。”说着,就放在桌上。又问雪萍:“打鸡蛋了?”雪萍说:“没打,经常来,不用吃。”娘说:“你这孩子,常来也是客嘛!再说,图个吉利。”说着就添水烧锅,烧开后往锅里打了六个鸡蛋。胶东农村有个风俗,新女婿上门得吃荷包鸡蛋,未过门的女婿也享受这一待遇。树娥把六个荷包蛋盛给了大宝,大宝推让了让,几口就吃下去了。娘把烤鸡撕好,拿出沽河老烧,说:“走累了,喝点酒解乏。”大宝说:“我不会喝。”雪萍见他不喝,就把酒放起来。知了猴烤鸡,确实是名牌,配料除大姜、香椿为主外,其它料就不得而知了。据说有大茴、小茴、沙仁、白寇、豆蔻、桔皮、陈皮等十几种名贵中药配制。烤工讲究,皮焦而不糊,肉香而不腻,真是味美可口,丈母娘直捡好的部位给大宝,不一会儿,大宝就吃饱了肚子。树娥间:“你家种完花生了?”大宝说:“种完了,爹叫我来帮您种。”雪萍把眼一白,呛促说:“帮您种?您是谁?俺不用你帮您种。”守着丈母娘,大宝没反上腔来。“死闺女,真能挑字眼。”娘骂了一声,说着都笑了起来。
收拾完了碗筷,雪萍饮完了牛。这时远处响起沉沉的雷声。雪萍看看天,对娘说:“看样子,天快上来雨了。咱们早下手吧。种完了去了心事。”娘说:“好。”便牵着老牛、小牛前面走,大宝扛着独脚锄,雪萍背着花生种,跟在娘身后。头午起垅,过午下种,为了开沟深浅均匀,又套上了老黄牛拉锄。大宝牵牛,雪萍扶锄,娘在后面点种,配合得条理有序。和谐的劳动,温暖的亲情,一种幸福感掠过树娥的心头。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小时候母亲留在心头的伤痕,年青时婚姻造成的怨恨以及老来丧夫的痛苦,她已经远远地抛在了脑后,不再想,不再去重念。她脑子里在着力描绘着今后的生活,描绘着为女儿建立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也算是对自己前半生的补偿。
远处的雷声越来越大,这是入春以来的第一次惊雷。仰望西北山色如黛,雾蒙蒙地连成一片,黑云催着白云象天马,象海浪,朝东南滚滚飞奔。俗话说,黑云是风,白云是雨。看样这场大雨就要来临了。不一会儿,天就起了凉风,接着雨点由疏及密,啪啪啦啦地落下来。
“娘,下大雨了,别种了。”雪萍用衣襟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说。
树娥抬起头,这才觉出下雨来。刚才的痴想令她进入了忘我的状态。她看看女婿、女儿,自己有点害羞地说:“走,不种了,过了雨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