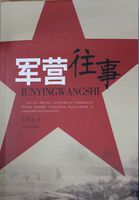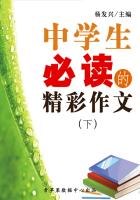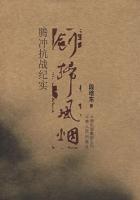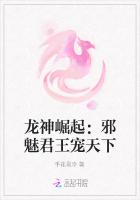在新中国临近“预产期”的时候,我父亲从老家赵城去过一次位于万山丛中的隰县。两地仅百余里路程,却赶死赶活走了两天多。全是曲折坎坷的羊肠小道,有时竟要从岩石下面弓腰钻行。沿途那些“猴娃儿牙叉骨”、“蒿圪枝顶泰山”一类的地名就使人胆战心惊。父亲回来腰酸腿疼,脚上打了泡,感慨地说,这回可把人遭死了,山里本来就没有路,那些路硬是人走出来的……父亲是文盲,竟然说出了鲁迅那句名言的意思,可见感受之深。据说绕临汾有一条能断断续续走牛车的路,可是有三百余里,远了一倍多,还要跋山涉水。所以父亲选择了走弓弦。父亲的出行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心想,我可不到那里去。
1964年,我大学毕业偏偏分配到隰县,不仅要去,还得在那里工作。这可把我熬煎坏了,整天皱着眉头,“万里边城远,千山行路难”一类的句子老在脑子里转。父亲却颇为知足地开导我说,现在好多了,隰县到临汾通了汽车,花五毛钱坐火车到临汾,还剩二百多里,再花三块多钱坐汽车,多省劲啊……
等我去报到时,才享受到那“好多了”的滋味。去隰县每天只发一趟车,旅客很多,却只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前一天晚上就要到走风漏气的候车室售票口排成长龙“熬票”。我通宵未眠熬到翌日拂晓才有幸买到上车的神圣权力(龙尾部分那十来个人被一刀切去了这种权力),被塞进车里,接受猛烈颠簸摇晃的“酷刑”式考验。这条等外公路,是比马车道宽不了多少的土路。汽车绕着千沟万壑和坎坷曲折的河道斗折蛇行,时而在厚厚浮土的河流中冲浪,时而在滚滚乱石的河床上挣扎,累得它一个劲呻吟和“放屁”,直到黄昏才跌跌撞撞地爬到目的地。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折腾,旅客都变成了刚出土的兵马俑,七窍之内都是黄泥。而我则被严重晕车蹂躏得半死不活,像一条装了粮食的麻袋似的,被人拖下车来……
首次赴任就给了我这样的下马威,使我对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描写有了更深的理解。当地人给我讲,全县就这条一根肠子通屁股的公路,还是1955年才修的,只有3米宽。因此不少村民,一生没进过县城并不罕见。即使城里人,终身没出过县的也比比皆是。
到“文革”结束时虽然有了长途客车,但道路依旧:晴天是“洋(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雪后则没有路。北面有一条孝午路可供绕行,但路况不好,行车颠簸,人们按谐音戏称“跳舞路”。从这些“雅号”还可以窥见人们出行难之一斑。
改革开放后,原有的路动了大手术,成了风雨无阻的油路。原来没有路的地方新修了油路。现在县内有东西两条大循环路把各乡镇串起来,不仅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而且有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多条公交车线路,村民可以随时进城。与周边县市之间,不但公路成网,四通八达,而且连通了一级路、高速路,进京出国也和进城一样方便。当年我父亲走的那条弓弦,两小时可到,我赴任绕的那条弓背,则三小时即达。飞速发展的公路,给山区插上了翅膀,可以快速飞向美好未来!近几年我去过不少山区,处处公路如织车似潮,使我深深体会到,今天是“万里边城近,千山行路易”了!
原载《临汾日报》2009年9月22日,并获“共和国与我”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