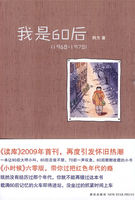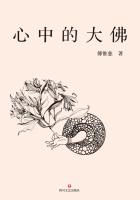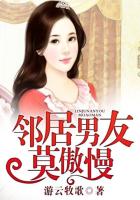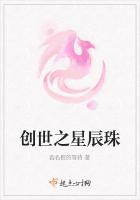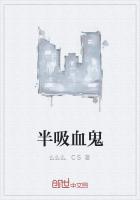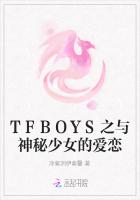我在业余写作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蓦然驻足,却见古稀界碑已在眼前,一股苍凉便袭上心头。许多圈内人士在此时都会有甜甜的成就感,而我却是一丝酸酸的“成败”感。回首往事,对“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更加深有同感。曾出过几本散文集,令人赧颜,发过几篇短篇小说,也自感羞愧……幸亏楚狂接舆唱的那句“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还给了我一点安慰。不然则会久久不安的。
如今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人权充分得到保障,政治环境也日益改善了。对我而言,能赶上这种夕阳无限好的末班车,也算幸运了。但又一想,毕竟已经近黄昏了。想写点什么弥补一下前半生的缺憾,又自觉力不从心。
周围如我之类够得上“老家伙”光荣称号的人,也时而好言相劝:“都秋后的蚂蚱了,还能蹦几下?辛辛苦苦半辈子了,好好享受几年吧……”
因此,便有点心灰意冷。心想,即使硬着头皮冲刺一下,也料定结果一定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得知,老年人不动脑子易患健忘症,甚至得老年痴呆症云云。以此推而广之,我悟出了写作既能动手,更能动脑,可以健身益寿的道理。又联想到巴金、冰心、季羡林等长寿作家,更觉得这种推想的可行性。出于这种动机,我不敢彻底搁笔了。情绪好的时候,将随时积淀于心的东西写出来,短则散文随笔,长则小说。
《辙痕》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就是我笔耕所得的“晚秋作物”之一。它反映的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天灾的洗礼,陷入十年“文革”人祸的考验,又步入改革初期社会转型、人心浮躁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抱着报效祖国人民的鸿鹄之志,顶着各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殚精竭虑,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然而时代对他们太不公平,待遇的低下、舆论的偏激、生活的清苦……给他们本已坎坷曲折的前进道路上,又设置了料不到、数不清的障碍。在如此艰辛的人生苦旅中升迁沉浮、拼搏挣扎、历尽艰难挫折……就是这样,他们仍然不改初衷,作出了不负良心、不辱使命的业绩,给那个非常年代留下了自己的生命印记。我是从这条布满荆棘的政治“雷区”艰难跋涉过来的。那时许多人的血泪经历、生离死别,时刻都会十分清晰地闪回我眼前。我想把这些告诉当今在风和日丽中幸福生活着的青少年,让他们像我们认识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认识那些哭泣的岁月……如果能起到一点警示和参考作用,我便十分欣慰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开始写《辙痕》。高兴的时候,就信马由缰地多写点,有事情或精神不好时,就少些或不写。起先定了个中篇的调子,但后来刹不住车,就成了长篇。
书出版后,从宋希祥、高秀云、刘秋祥、刘渊博、刘怀博等同志写的评论中,我看到了我奢望的那种反映。这对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通过这本书的创作,我觉得蚂蚱只要尚存一息,即使到了秋后仍应去蹦。尽管蹦的力度、距离、时间和成绩不会相同,但精神是相通的。鲁迅先生在《补白》中说得好:“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不过,如果要定目标的话,应因人而异,要留有余地,不可强求。最好将其作为休闲娱乐的内容之一,既顺其自然又科学安排。这样,在心态好的时候还可能突破目标。我的长篇小说《为啥抛弃我》就是未列入目标的另一“晚秋作物”。
我们的秋天是一种“暖秋”,言论自由,环境宽松,气候宜人,社会和谐,有如进了桃花源。在这个季节里,找不到欧阳修《秋声赋》里描写的那种凛冽和残酷,比较适宜蚂蚱们继续蹦蹦。
在这种秋高气爽,夕阳辉映的环境中,以可遇不可求的态度于闲室信笔,既可锻炼脑子,推迟衰老,又可反映生活,陶冶情操,是延年益寿,发挥余热的不错选择。
我国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各种为老年朋友们维权和服务的法规和措施不断出台,使“人活百岁不是梦”得到了有力的保证。古稀以后的人生旅程相对延长了,应当紧紧抓住“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大好形势继续笔耕,既不要使田园荒芜,也不要“以心为形役”,更不要辜负了这难得的秋景。
原载2007年第3期《山西作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