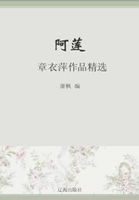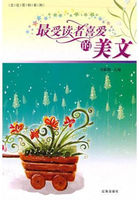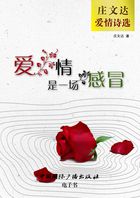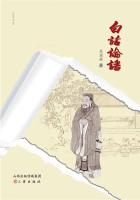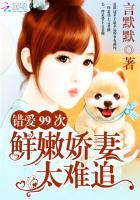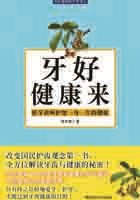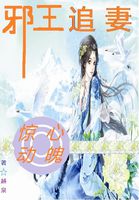交友往来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戏为六绝句》句)
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理不存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句)
我写文章,就像小孩学说话,都是一句一句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没有古今中外数不清的“别人”,就没有我自己,何谈我的文章。学他们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立意构思、剪裁修改、写作态度和方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拿来主义”。力争让被学者自己也认不出是从他们那里“拿来”的东西。我至今仍未达到这种程度,但我不因未达到而心灰意冷,也不因某些地方达到而忘乎所以。在我急需的关键时刻,许多文友不断主动慷慨赐予,在我陷入迷茫的时候,及时指点迷津,使我才有了今天……我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李国涛
《邈邈小路》是王双定十五年来散文的结集,也是集里一篇的篇名。这正是近来散文集或小说集题名的方式之一。只就这篇散文而言,短短千把字写得意趣盎然,很见功力。这篇散文里说“小路是热情的”,“小路是含蓄的”,“小路是坚毅的”。又说,“小路是一首短诗,也是一部巨著”。说得很好,很有诗意。这一篇是一首散文诗。这一篇里引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使我想到双定写散文这十五年来也正是这样,热情的、含蓄的、坚毅的。所以我想,此集以此篇作书名实在是有一番苦心苦意。
我没有同双定谈过这个想法,这是我下笔时才有的揣测。我不是望文生义。我想到集中收入的《赞潺潺流水》。那是1978年发在《汾水》上的一篇,其时我正在那里当编辑部主任。稿子是经我看过的(这次结集时有改动)。我从那一篇稿子记住了王双定这个名字,我还记得他当时在隰县工作。为什么记得清楚,因为当时山西散文作者很少,编辑部的同事们读到此文都说好,并说作者有写散文的笔致。这次摊开双定的稿件,我自然又仔细重读了这一篇。此次重读,并不算很出色。可见这十年来当代散文大大进步,读者的眼光也逐渐高起来,比较之下,也可看出双定的散文水平也达到一个新境界。要以单篇而言,此集中我最喜欢的是《陋室三叹》。此篇在作者下笔时并无一个明确的理念,不过写大半生以来住处的简陋。由于居于陋室之中感受到的不方便,或者说感受到的痛苦是深切的,刻骨铭心的,所以笔下的微妙动人之处甚多,有些地方我觉出一种人生的悲哀。村居(窑洞)里潮虫乱爬可以到什么可怕的地步,城郊破屋里群鼠可以猖獗到什么样子,不经受者无论如何不能想象。最后一节写最幸福的新居在铁路公路交叉的桥头,噪音终日,几乎使人发狂。这三叹之后作者又平静地说:“在忍受中都忍受了。”作者无意于教训,文章却实在有感染力。此作是1988年的作品,距《赞潺潺流水》整整十年。
中国当代散文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散文读者有超过小说读者的势头,在书店里,散文集也很多,且易销售。这种形势当然也对散文提出新的要求。
散文在五四时期有过辉煌的历史,后来渐弱。散文家在新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曾经群星灿烂。据学者说五四的散文源头有两个,一是明代小品,一是英国小品。五四以来的大家多数是得益于此的。像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等。当然这仅指五四以来的某些名家而言。散文源远,中外皆然。我觉得凡散文大家读书皆多皆广,有学问有见识。他们并不以明小品英小品为限。上面的意见鲁迅就说过,而且鲁迅受明小品的影响并不见得比受魏晋文章的影响更大。他受英国散文的影响也不如受尼采文风的影响大。这些事情一时说不清,不管如何,散文作家泛览精读总是必要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时代早已结束了,成为一种嘲弄人的说法。但是说书中自有艺术在,这大概错不到哪里去。
这话一说就远了。我所希望的是双定在写作之外还要苦读。现在书出得多了,名家的集子、中外古今的不妨尽力搜寻一些,细读一番。再经一番苦读,我相信双定的散文还可以有所进境。他不是说过小路是漫长的吗?要通往更宽广的路,不经历这种漫长怕是没有别的法子。好在双定原是“文革”前山西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读书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也许问题在于时间。时间要挤。作为一位业余作家,东挤西挤实在也艰苦。
原载《山西工人报》1993年5月13日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