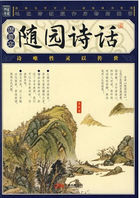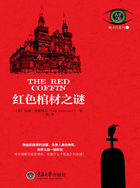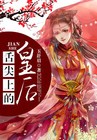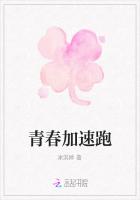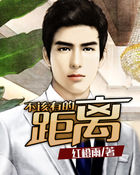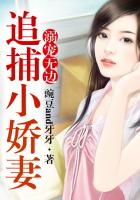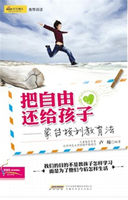梁寒冰长我十多岁,我以长辈待之。“文革”后期他被解放出来,安排在中科院历史所任书记。他对我说,林鹏,你到历史所来工作吧。我说,我一没学历,二没职称,我到历史所能干什么?相顾一笑而罢。
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寒冰、聂元素老两口每次来太原,必到寒舍,可以说无话不谈。梁寒冰要编一部中国古代史,叫阶级斗争史,我取笑说,你编一部阶级斗争史,我编一部儒法斗争史,说笑而已。后来有一次他问道,林鹏,你的儒法斗争史编得怎么样?我一下愣住了,老半天才醒悟过来,想起开过这么一个玩笑。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对人们的影响太深了,抹不掉秦始皇的阴影。我说,我开玩笑。他说,儒法斗争是值得一写的。等等,等等,漫谈一气。
儒法斗争是值得一谈的。春秋五霸开创了霸业时代,甚至后来的吴越也是以霸业为政治目标。他们打的旗号或说口号,依然是对当时天子的周王朝的辅佐。到春秋末期,王道和霸道就分道扬镳了。士君子坚持王道,而当权的诸侯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认为只有霸道才是出路。春秋诸侯竞相变法,只有变法才能称霸。而战国诸侯竞相称王,只有称王才能实行霸道。他们占住王道之名,而行霸道之实。可见此时王霸之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君子儒坚持王道,小人儒坚持霸道。商鞅变法使落后的秦国骤然强大起来,令人刮目相看。此时的秦国同秦穆公时的秦国相比,已经是一个全新的秦国了。此时的秦国已经坚决地走上了霸道之路。荀子说,“秦无儒”。秦国非常纯粹,它纯粹是法家的一套了。此时的山东六国已经是秦国的盘中之餐、俎上之肉了。不过,六国的士人也已经看清,秦国只是走上了死亡之路而已。所以山东六国的士人,都变成了坚决的反秦的战士。这就是战国末期儒法斗争的形势。儒家失势,法家得势,一时强弱,一目了然矣。
土地制度是一切经济制度的根本。在上古,也就是远古的原始社会,地广人稀,土地属于天有。谁种归谁,可以说是真正的私有制。这正是儒家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自然而然的耕者有其田。后来是家天下,才有了公田,公田就是公侯们的私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虽然后世解释纷纭特甚,但是,贡是一定数量的田租,助是在公田中劳动,公田收获归公,私田不再收税,这是各家都认同的。春秋变法就是取消公田,改八夫一井为九夫一井。没有公田了,只在私田中收税,这实际上是变私田为公田,也就是都成了公侯们的私田了。这个账非常好算,谁知学者们只是在文本里打转转,一辈子也说不清,道不明,无可奈何。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也就是到孟子的时代,人们还在贡与助上打不定主意,朝令夕改,各行其是。孟子是主张助,也就是提成,叫做什一之税,他甚至说,“虽周亦助也”,实际上是拿周压人。虽然有孟子的坚决反对,田税制度却是坚决地走向固定数量的田租了,《吕氏春秋》也是主张固定数量的田租,并且主张年初就应该定下来,不再更改。“先定准值,民乃不惑”(见《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而秦国上下根本不能接受这一套。秦从商鞅变法之后,采取的是一种变相的或说五花八门的彻法。“周人百亩而彻”,完全是为了战争。公刘“彻田为粮”,注家说行道为粮,可见是战争的军粮。“彻者彻也”,全部拿走,连锅端。秦人接受了周的地盘,实行彻就有历史的渊源,再加上一切为了战争,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谁能有什么可说。什么贡,什么助,什么十分之一,什么十分之二等等这些问题,这些争论在秦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在秦国,文化是非常落后的,而政治(统治之法)却是非常先进,秦孝公率先实行了郡县制,原因很简单,郡县也是为了战争。一切为了战争,“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力气”(《韩非子》)。秦国只管强盛,六国只管衰弱,历史有什么话说。但是历史也不客气,死亡之路就是死亡之路,任你挑选任你走,往下走吧,这就是历史。最后历史证明,仁者无敌。仁者无敌就证明,不仁者有敌,有敌就必有一败,其奈历史何。
中国古代文化是士人的文化。大舜就是一个典型的士人,并且是一个自耕农。正是他开创了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后来的伊尹、傅说、吕尚、周公、孔丘、孟轲、管仲、乐毅以及吕不韦,无非士也。
士们主张耕者有其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他们主张人人平等,维护个人尊严,“虽负贩亦有尊也”。在政治上,他们主张继承古老的政治传统,明堂议政,辟雍选贤。他们主张尊重血缘关系,顺应人的善良本性,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一切同后世的所谓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完全相通的,主张在私有制下建立道德社会。凡此种种都同非常自私的王侯们的利益相冲突。自从有了皇帝以后,一家一姓的皇权高于一切,而士人们的思想意识是仁,帝王是不仁,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没有一个帝王不好大喜功,实际是劳民伤财。法家只知为帝王服务,为王先驱,先意承旨。没有一个儒者不反对劳民伤财,这就成了帝王的眼中钉。儒家讲究遇到问题,反诸身求诸已,而法家是帝王的代表,绝不敢反诸身求诸已。
史云,孔子卒儒分八派,加上墨家、道家,杂七麻八,十家不止,号称百家。这不仅是儒家的阵容,这是整个士人群体的阵容。士人是四民之首。四民是士农工商,因为工商食官,可以除外。士和农界线不清,农人中的优秀青年人年年都有推荐为士者,当然士也有退而耕诸野的,也就是变为农人的,此即隐士。这样就可以看出,士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是整个古代社会的政治的基础,是统治者重要的依靠对象。
战国各国王侯及其重臣、贵胄都有养士的风气,比如四公子,养士多至三千。后来的合纵连横,都是为了统一中国。这正是士人们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李斯说,此乃布衣之秋也。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广大的士的阵容如下:
一、隐士,山林岩穴之士。“孔子死原宪亡在草泽”,他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
二、处士,不为官,不主事,却敢于横议(横者逆也);
三、为了养家糊口,出为小吏,即使提拔起来,随时都准备挂冠而去;
四、平生抱负非凡,想有所建树,这些人都是想以自己的理想影响朝廷,使社会生活走上正道,也就是实行仁政,以仁为己任,就是王道,实现天下太平;
五、最后是法家之徒,追求个人前途,统治者好什么,他就来什么,多半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严刑峻法,立竿见影之类。
这第五类是士人中的极少数,但是却是极容易得势的一类。历史上的所谓儒法斗争,就发生在这第四类士人和第五类士人之间。儒法斗争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斗争。
学者们一向把儒家算作百家之一,其实错了。孔子有删定六经之功,六经是儒家的经典。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各派都同六经有着渊源的关系。虽然如此,六经只属于传授六经的儒家,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一家。也有学者把隐士算做道家,其实,原宪亡在草泽,那就是隐士,原宪却不是道家。前述的士人的一、二、三类,算做哪家都行,但在儒法斗争中,他们都是站在儒者一边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从商鞅到王安石,变法都是以“复古”为托词的,只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或说只是《庄子》所说狙公赋予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而已,目的只是急功近利罢了。
历史上所有的变法都是因为遇到了危机,都是治表不治本,都是一步一步加深矛盾,形同饮鸩止渴而已。历史上所有的变法,总括起来,都是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农民变为农奴,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诗句,出自《诗经》,但不是后世所理解的意思。《孟子》早有解释,可是人们不予正视,王土、王臣居然成了天经地义,谁也莫可如何。
土地收归王有,号称国有。田税制度变为彻法,全部拿走,连锅端。秦是“口赋箕敛”,最彻底地彻了。秦始皇只管战争,老百姓饿死他不管。要按社会形态说,只能算最残酷的奴隶制。这是杀鸡取蛋,竭泽而渔。在短期效用看起来,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三年五年,小灾荒,十年八年,大灾荒,就贻害无穷了。所以统治者只要尚未亡国,他们最终都要把法家牺牲掉,就像曹操借粮官之头一样。然后请有儒家倾向的士人,或者干脆就请山中的高士出来收拾残局,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虽然法家大多以身首异处告终,统治者却深深知道,只有法家才是真正的忠臣,是有用之才,而儒家的仁者无敌的仁政王道一类的说词,只是空泛的教条,迂远而阔于事情,不顶用,指不上,远水不解近渴。而法家这种甘愿做鹰犬的人,什么时候都用得上。自从有了皇帝以后,无一不是迷信暴力的,所以随时都离不开法家,随时都离不开酷吏,一时一刻也少不了的。有统治阶级存在,有帝王存在,严刑峻法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造成一种政治态势,法家永远站在帝王一边,他们是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的实施者,他们的学说就是法、术、势,最后就只剩势而已,势者权势也。暴力是权势的标志,没有暴力就没有权势。权势在暴力中生,在暴力中亡。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至死不悟。同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相对立的,有能力有胆量敢于同帝王思想帝王文化对立的,对着干的只有儒家。他们的学说就是仁,仁慈,仁政,以仁为己任,仁者无敌。
后世的帝王,居安思危的也常有,声言同士人共治天下的也有,于是就把儒家的学说拿过来,拼命地装饰自己,尤其是三纲五常,所谓礼教,包括那些老掉牙的繁文缛节都拿来,用以维持帝王的威严,帝王的天命,帝王的事业。他们说起话来,仁义道德,振振有词,天理良心,头头是道,老百姓自然也得听。越是盛世,越是黑暗,隐士也就越多。虽然,朝中也有不少真正的儒者,也不都是摆设,也常常起草一些冠冕堂皇的文告,煞有介事,粉饰太平,不可否认这就是太平嘛……然而儒法之间的斗争,却是随时随地都在斗争着,如有关重赋和轻赋,如严刑和宽刑,如大赦与否,如滥用暴力和反对滥用暴力……内容多得很。只要帝王存在一天,帝王之术就存在一天,统治阶级存在一天,统治之术就存在一天。儒法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历史就是在各种矛盾中,曲折地,一溜歪斜地,出乎想象地,不尽如人意地这么发展下来,恐怕它也只能这么发展下去了。
前几年,梁寒冰、聂元素夫妇相继去世了。回想往日欢欣聚首,畅谈时事,令人难忘。谨以此文表达对他们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