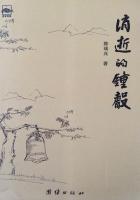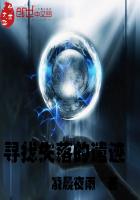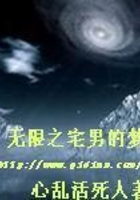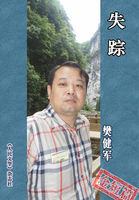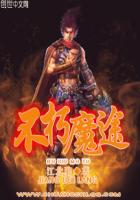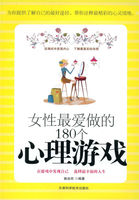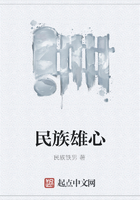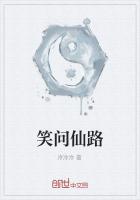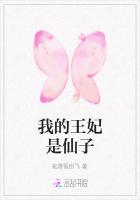今年(2003年)是袁毓明同志去世三十周年,他是1973年去世的。后人对他的评价是,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硬话,没有干过一件软事。这个评价非常中肯。当我听到这个评语的时候,我很感动,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人活一辈子,得到这么一个评价,对于一个真正的士人来说,也就足矣了。不过我一向对他的评价却较为具体,我认为他的知识非常渊博,谈吐非常风趣,而且他的文章更是流畅优美……在当时,无人可比。他对我说:“孔子曰,不能说。”意思是孔子是曰,不能说孔子说。闲谈中他常常引用这句话,我感到好笑,又觉得意蕴深沉。中国语言文字之丰富优美,不在其逻辑性如何,而在其蕴藉。话到其间,一笑了之。
袁毓明1962年在《火花》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洪洞风土志》。我看了觉得非常好,就打听作者其人。后来在“文革”中认识了他。一旦结识就常常见面,常常叙谈,非常投契。袁毓明是个老党员,却不带一点布尔什维克气。他原是《大公报》的主编,反右之时,遭打击报复,给他戴了个右派帽子。他不是老左,但也不右,只是一个诚笃君子而已,是个标准的士君子。当然,戴了右派帽子以后,他确实有点右了。然而他依然是一个诚笃君子。一位真正的士君子。我是一向右倾,所以我们颇有共同语言。我赞同成汤纲祝的思想。说来可叹,我国古代思想如此丰富,而现代知识分子却把古代看成一片荒芜。
袁毓明被打成右派,下放山西,后来摘了帽子,安排省文联副秘书长。摘帽右派,不是右派,还是右派,只是摘帽右派。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藏有一些破烂书籍,例如在旧书摊上买的丛书集成的零本。袁毓明经常借去看,然后我们就高谈阔论起来。
有一次谈到朱熹,新中国成立后沿袭清末民初的余风,把宋明理学说得一钱不值,尤其把古人分成唯心和唯物,殊属无谓。袁毓明便说,“孔子曰,不能说”。
《丛书集成》里面有一个小薄本的《朱子语类辑要》,他看了说好。我对他说,我所以看重此书,只有一点,就是朱熹在谈到秦始皇时说,虽然秦始皇很坏,可是自兹以后谁也不肯放弃皇帝的称号。他点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要害问题。袁毓明对我说:“你是个有思想的人。”当时一般人的口头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补充说:“你是心怀现实,放眼历史。不过,有些事,孔子曰,不能说。”我们相视一笑。他喜欢这么说,不过我也学着这么说,不过,仔细想来这确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使中国历史沦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大泥坑。他说,孔子曰,难矣哉。我也就付以哈哈一笑。同他闲谈,有一种乐趣。这种乐趣是什么,我说不清,我只知道,它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广大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们,也就是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士君子们参加了革命,才使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汤因比总是念念不忘“无产者”,仿佛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运动、重大的转折,都是“无产者”们造成的。他受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所谓思潮的影响过深,使他不能客观地对待历史,尤其不能看清中国的古代史。不能看清中国的古代史,也就不能看清中国的现代史,这是紧密相连的事情。只有中国拥有士人这个阶级,西方是没有的。士人这个群体,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且他们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者。袁毓明没有留下什么文集或选集,我觉得很惋惜。后来我想其实用不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伯夷、叔齐、颜回、原宪有什么文集和选集呢?
立德也就是立人。做一个真正的士人,一个真正的有觉悟的士君子,这就是一切。我又想,那些出了好几卷文集和选集的人又怎么样?他们敢说,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这倒也不难),一辈子没干过一件软事吗(这太难了)?
他发病是因为来看我,累着了。李束为同志同他说,去看看林鹏吧,他说,走。李束为身体好,走得快。到我家,我不在,锁着门。两人紧接着往回走,这一下累着了。当天夜里犯了冠心病。那时候正是曾山、陈正人刚刚去世不久的时候,他们都是犯了冠心病去世的。周总理指示,加紧对冠心病的防治进行研究。我问医生,这种病就没有特效病吗?他说,有,苏合香丸。人们急忙去找这种药,省城居然没有。当时省药材公司的经理是我的朋友,我请他想办法。他立刻派人坐飞机去上海买到了这种药。等药送来,袁毓明已经去世了。
袁毓明去世了。我非常难过。一则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谈友,一位同志,一位老师;再则,好人总是不能长寿,这是我最感到悲愤的事情。
2003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