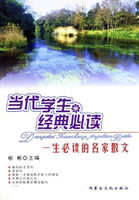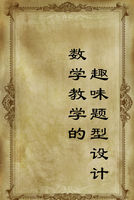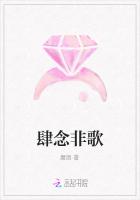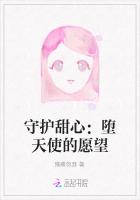我原名陈步翔,后改名为陈勉哉,祖籍浙江绍兴。1909年6月3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在江西省上饶县尊公桥乡出生。这里,先说一下改名字的来由。我是在江西出生的,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在江西生长和学习,在南昌读完初中和高中,其间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又接受了江西革命先驱袁玉冰、邹努等的培养,投身于当时的青年学生爱国活动,并参加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仍在共青团工作,担任过江西学生总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并被选入全国学生大会常务委员会。1927年,贺龙、叶挺大军抵达南昌,由江西学生总会负责接待和拥军事宜,我得以参加“八一”起义外围工作。“八一”起义胜利后,我参与了组织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和军民联合庆祝大会,并作为学生代表,被选为以贺龙为总主席的大会主席团成员。然后,我随起义军南征,抵达广东潮汕。军事失利后,根据周恩来指示:“就地隐蔽,自找出路。”我奉命隐藏,借机返回浙江老家。此时,国民党已下达紧急通缉令,江西《民国日报》《南京国民政府公报》头版首篇就是战犯通辑令,计17人,朱德、叶挺、贺龙、周恩来等赫赫在目,我的名字也排在其中。当时,通过远亲李骏初拜见从未谋面相交的远亲蔡元培兄弟(蔡元培当年为北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长),获得了读浙江大学的名额。不过,为了躲避通缉,借了一个同乡陈勉的师范毕业证书,并在勉后加了一个哉字,就这样进入了浙江大学读书。也就是这个名字,我一直沿用了下来。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说一说我的老家——绍兴花径。绍兴是浙江省一个文化名城,也是大文豪鲁迅的故乡。说到地名,原来是山阴和会稽两县。改名也有一段典故:南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南逃越州。越州官吏上表,求高宗乞赐府额,赵构随手写下“绍祚中兴”四字,并于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于是越州府就改称绍兴府了。当时的绍兴府辖有八个县,其中的山阴与会稽两县,历来与州府合城而治,就合并成新建的绍兴县。
1982年,国务院公布绍兴为中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我的老家绍兴凭借她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文化环境,宏大的历史舞台,造就出众多著名文人墨客及近现代伟人名流,可谓名人辈出,灿烂星汉。名闻全国乃至世界者,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淑文、王阳明、刘宗周;著名历史学家谢承、赵晔、范文澜;著名文学家贺知章、陆游、张岱、鲁迅;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著名画家徐渭、赵之谦、任颐;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陈建功、竺可桢;著名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民族英雄葛云飞等等。特别要提及的是一代伟人周恩来,他生于江苏淮安,但祖居绍兴县城保佑桥百岁堂(现劳动路19号),内有周恩来祖居“百岁堂”,现已改建成“周恩来事迹陈列室”。
我不仅出生在江西,大部分时光也都在江西渡过。我这一生只回过一趟浙江绍兴老家——马山镇坡塘花径村,也就是我被通缉归隐的时候。记得回浙江后,我第一个投靠的就是富戚李骏初。说他富,富不能敌国,但在绍兴一隅却有大富、首富之说。他父亲原在上海一个钱庄当跑堂的,一战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买回了一些油漆,发了财,掘到了第一桶金。就此返回绍兴老家开办了绸货庄、杂货店。发达了之后,又在嘉善县开设了“怡和钱庄”。以后,办成了当地最大的钱庄。父亲死后,李骏初三兄弟接管了家业,他本人负责经营嘉善的怡和钱庄。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以嘉善为总店,先后在松江、杭州等地开新钱庄,在上海储蓄银行也投了资,并在绍兴中正街置了一栋豪华六层大厦,成为浙江钱业巨头。
李骏初为人正义疏财,肯周济穷士。他和我家亲缘关系不近,是我舅父的姑表兄弟。我投奔他时,他从来不问我的历史来由,而是愉快地接受,满口答应给我找工作,亲切地视为自己的子侄。记得初到嘉善,盛宴给我洗尘,并带我到县图书馆借书读。当处理店务稍空闲时,便领我到上海拜见蔡元培,到杭州拜见蔡元培的弟弟蔡敷卿(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并在上海中央旅馆、杭州清泰(湖滨)旅馆设豪华盛宴招待蔡氏兄弟。李骏初告诉我,他和蔡氏兄弟也是姑表兄弟,我就依例称他们为舅舅,实际上都是远亲。蔡元培盛情难却,立即去信陈布雷(当时他是浙江省教育厅长,据称他只有一半时间在杭州,很多时间都是去南京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嘱陈布雷给我安排就学。
由于陈布雷很忙,安排需等时日才有结果。我便在李府做客。李骏初待我如自己人,每日陪他喝喝老酒,每餐要喝上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海聊。他到哪里都会带我去,今日上海,明日杭州,后日苏州。记得有一次我和他的儿子李富微去游西湖,富微的钱被小偷扒光了,我身上又没有几文钱,电报叫家里汇款又不到。当时住在旅馆有包房,用车费用由旅馆付,旅馆费用是按季结账,但吃饭要到外面餐馆,要自己掏钱。所以,吃饭就成问题了。于是租了小车到省交际处找蔡处长,被接待宴请,好在当晚怡和钱庄汇了款来,才解了难。
当我住在李骏初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我的堂兄陈步云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专程到中正街接我回老家——坡塘花径。实际上,我早就有这个心愿,回老家看看,于是很高兴地回了故乡一趟。
我的老家是在马山镇,离绍兴县城还有四十华里的水路。平时有绍兴到马山的大班航船,每日开航,但只能到坡塘码头上下旅客,然后转搭绍兴特有的交通工具——乌篷小船,可以直接在我老家大门口的石坡前停泊。后来听荣儿、棠儿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水路已经不通了,从绍兴县城到马山有一条平整宽敞的水泥大道,每天都有好多趟公共汽车开往马山,进出十分方便。
这次我回老家,步云兄也是雇了一条乌篷脚划船。这种脚划船,小而轻便。船舱中仅仅能坐三四个人,而且只能坐在船板上,如身材高大的人往往会碰到蓬顶。但船却灵活得很,稍有侧身,船就会摆动倾斜。船老板头戴无沿毡帽,就是鲁迅小说中所描述的阿Q所戴的帽一样。绍兴县乡都是水乡,大都前面临街,屋后就是河道,两岸都有大堤,舱面几乎与堤岸并高。上船很方便,一脚就可踏上船头。船头很狭小,上了船就需侧身进舱坐在舱板上,不能随便转身。我是在叔叔的店门口上船的,他所在的南货店就在绍兴县城昌安门外,三脚桥附近(他在这家南货店司账)。但是叔叔未同船回来,只是堂兄和我一块回家。
乌篷船的特点是没有舵的,而且是用脚划,不是用手划桨。上船后,我看到船老板手提一个木桨,桨好像不是很大,也不常用,仅在开船和转弯时用,以桨代舵。而用脚划的桨看起来很大,还很长,好像可以用双手托举起来。划桨时船老板两只脚用力举桨击水,船就向前行驶,用力越大,速度就越快,有时看起来比岸上行人走路还要快,是绍兴的独有行船方式。船老板告诉我说,这种脚划船很便宜,就是雇一天船也要不了几个钱。这里是水乡,不论城里或乡间,到处都是小河小溪,而且桥梁很少,桥也是拱桥,方便船只航行。你想从甲地走到乙地,即使是短距离,你如果不熟悉当地的桥梁的话,就会寸步难行,望河兴叹。因为溪河尽管不大,但至少也有两三米宽,而且水都较深,不可能涉水过河。所以,这里的居民出去就要坐脚划船,稍微富裕些的人家都有自备的脚划船,而一般人家就要坐这种业余待雇的脚划船了。另外还有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购置有供喜庆用的大船。至于较长距离的河流一般都有航运公司定期开放的班船,属于机动船,老百姓叫洋船。这种班船可坐几十人,相当于现在城里的公共汽车,能在大一点的村镇码头停靠,上下客人。据船老板告诉我,从绍兴到马山花径坐班船的话,要到坡塘码头换乘脚划船。如果从县城就坐脚划船的话,就无须绕道马山镇了,过坡塘后直接折向花径,直接停靠在我老家大门口。这次我从县城坐到花径,大约花了三个钟头,终于到达了老家。
花径原来没有村落,是高祖父首先在此居家。这里的百姓是以后陆续搬移来的,也是他命名的村名。村落很小,约有近30户村民,但环境优美,景致高雅。村三面环绕小河,柳树成荫,四望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每当春季油菜花开的季节,黄绿相映,村如在花坛中。全村多系砖泥砌成的小平屋,独我家用平砖到顶的砖木结构大屋,屋有四进,前面三进两层,第四进三层,大围墙用白石砌成,还有用白石砌成的八字大门。大门前有一宽大空坪,坪中竖有两个旗秆石。屋后面是一个大花园,翠竹丛生,并有小塘一口。我看的时候,似乎有年久失修残旧破败的感觉,大概是家道中落的缘故吧。
我曾听父亲讲过我们陈家家史,由于后来的子孙大都读书无成,又不善生计,很多人都是外出谋生,到我这一辈,仅有叔叔陈联庚(号辉堂)留守。他从小就在绍兴昌安门外三脚桥头南货店学徒,期满后任管账兼司库。他生有一个儿子叫步云,就是我这个堂兄,曾一度经营中达烟草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家产荡尽,艰难维持生计。这次,我还看到店里二楼上堆放有几十箱发了霉的香烟,不免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天,叔叔特地请假回来陪我这个从未归来过的侄儿。尽管生活拮据,仍然破费很多钱财,买了许多好菜,盛宴款待我。步云堂兄还带我到村里各家各户走了一走,认亲叙谊,到处游玩。好像大小祠堂都去了,还拜见了族长。但是,我长年在外,不仅不会说绍兴方言,就连全听懂也很困难,很难和他们亲近交流。叔叔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姑姑,嫁到附近的孙端镇,也就是鲁迅书中提到的他外婆的故乡。
我在家逗留的日子里,还有幸参加了族里举办的清明上坟大典。典礼由族长主持,全族的人都参加,而且每人都可分到一份祭祀猪肉供品。当然,我也不例外,同样领到了一份祭品肉。还有,在办祭祀仪式的同时,还有一个堂会,就是有困难的人可以申请借钱,期限为一年,第二年必须还清,还清后方可再举新债。堂兄步云去年就向族里借了款,只得在城里四出告贷,筹齐归还了这笔欠款。
在家里住了些时日,便又租了一条脚划船,由老家回到了绍兴叔叔家,又从绍兴购置汽车票回到了杭州,从杭州乘火车返回嘉善怡和钱庄李骏初那里,结束了这次可爱似乎又不可爱的老家之行。
记得当年我曾活剥杜甫的《客至》写了几句诗文:“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飞,花径祖地今已荒,断壁残垣留孙辈。”算是当留点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