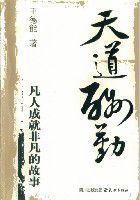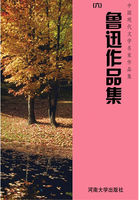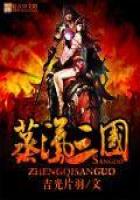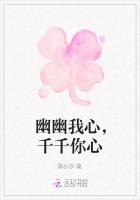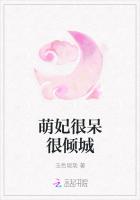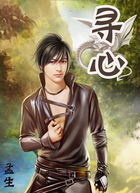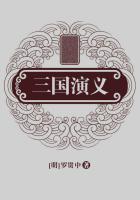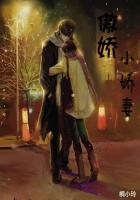九、午夜枪声,起义胜利
八一起义,在南昌响起了革命的第一枪,是惩罚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党领导下武装革命的创举,尽管在潮汕遭到失败,然而毕竟燃起了革命火种。从此星火燎原,革命火花燃红了全国大地。这次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虽已相隔六十七年,兹事体大,记忆犹新。
我是7月22日由武汉参加完全国第九届学生代表大会后返回南昌,见到与离去时的情况很不一样。以前,整个城市几如一潭死水,冷冷清清,到处静悄悄的,人人灰溜溜的。由于党群机关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多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剩下一些留守人员,不仅无法开展工作,而且到处呈现沉寂甚至僵化情况。这次离开南昌不过半个多月,整个城市却沸腾起来了,到处热火朝天,生机勃勃,各机关单位都恢复了活动。由于大军云集,却又夹着浓厚的烟火气息,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但变幻莫测。在武汉开会期间,国共分裂已由酝酿见诸事实,宋庆龄、邓演达先后出走时就留下了对时局的宣言,特别是邓演达最后通牒一句——“今后在战场上相见”,令人感慨以及此前鲍罗廷顾问被迫回苏联,散会后“到工农中去,到军队中去”已成为相互间临别赠言。返赣途中,大江中满载军队的帆船,由九江到南昌的列车上,都满载军队,而且增加了班次,军运频繁,战云密布。在九江、在南昌看见到处张贴的“欢迎铁军来江西”、“欢迎第二方面军东征”、“拥护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打倒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电线杆上、街头巷尾都贴有部队的各种番号,宿营路标,很多学校驻扎了军队。先后又听说,第二方面军张发奎,虽已到达庐山,但态度暧昧,好歹不知道。不少谣传,战火将重燃,鹤唳风声,人心惊惶,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到南昌后,并未回家,直到学总会,见到大家十分忙碌,紧张工作。与各方面人士频繁接触后,知道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十一军(新建),四军的李汉魂等却已来到了南昌,同时各省市在武汉流亡的革命领袖和前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的江西领导同志也来到南昌。现在是争取张发奎当机立决;或者是继续东征,直攻南京;或者是南下广东,重创基业。反正大家知道,江西是四面受敌之地,何况宁汉合作,敌势增强,而且朱培德现统率了两个军(三军与九军),屯在江西西南腹地,正与敌人配合对付我们。看来大军只是过境,不可久留,眼见反动势力气焰高涨,我们重新转入地下斗争。随着形势的紧张,在风雨满城的日子里,都有着“从军去”、“下乡去”的打算,心情都很沉重。但总以为,目前贺、叶大军正在这里,谅敌军不敢轻举妄动,总可以捱过一个时期。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战争竟发生在眼前,当地。
1927年8月31日凌晨,约莫三点钟左右,一阵密集枪声,把我们——住宿在东湖边退庐图书馆里的学总、学联干部从睡梦中惊醒。大家匆忙起了床,互相问讯,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枪声历久不息,而且越来越多、越响,间杂着不断的机枪声。时在深夜,偶尔大着胆子开门探望,只见火光冲天,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还隐约听见远远的冲锋号音。当时十分害怕,紧闭着大门,大家聚集在一起,预防不测。当时在场的计有刘仁、傅铭第、雷洪福、彭学遂外,还有专职秘书及干事。经过一段时间,枪声依旧激烈,大家既惊异也很紧张,事出突然,但也并不十分害怕,估计到贺叶大军都在这里,叶挺是自己同志,贺龙也和我们友好,而且朱德的教导队和曾振五(是曾天宇的哥哥)手下的警察队,一共有两三万人,朱培德驻城军为数很少,众寡悬殊,不会有多大的危险,要说危险那是今后的事。还有一点,能使我们保持镇静的事,那就是如果有危险,组织上不会不事先通知我们,而且靠近我们的有总工会、农民协会和南昌市党部,也会给我们通消息的。总之,这次不是小打,而是大打,左猜右想,谁也说不上,始终是一个谜。
好不容易啊,激烈的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枪声逐渐稀疏,直到天色明亮,枪声才全部停止。
天亮了,枪声停了,开门一望,湖边上人来人往,卖早点的、卖青菜的小贩照常叫卖。知道无甚大事,大家回家的回家,访友的访友,打探消息。我径奔团省委所在地,路过总工会,淦克鹤等站立在门口,刚卸职萍乡县长的张国也在那里,他们已知道夜来情况(当然是在事后),说是东征军缴朱培德的械并已完全解决。到团省委、吴季滨书记告昨夜战斗是党中央策划的,并且是由军委周恩来书记亲自主持的。详细情况,即将公告。至于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等待省委通知。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去青年部找郝鸿(号民器),就在省党部门口遇见当时负责的罗石冰,他说昨晚之战,是宣告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是一次武装起义,但这只是起义的开始,以后还要大干。同时,告诉我,他刚从省委来,汪泽楷(原湖北省委书记,后调江西)有事找我,可能有什么任务交代,我没有去找郝鸿也没有回家,回学总等他来。
回途中经过江西民国日报馆,顺便去发行组,获知今天报纸将会刊登起义消息,现在等稿,外印一、四两版,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回到学总,正在吃早饭,而且来了一些外客,大家笑逐颜开地谈论昨晚战事,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经过渲染的小道消息(以后证实的)。有的人住在圣公会宏道中学内,那是驻有贺龙部队,仅以一个连,翻过藩台后墙,将防守在省府里的守军全部缴械。有人说,昨天晚上,从武汉回来的朱德利用旧关系,把一些滇籍的三、九军高级军官请到他的寓所打麻将,枪响后即全部俘虏。他们的部队因群龙无首,不知怎么办,就此投降……今天,很多士兵在搬运缴获的枪械,听说朱培德的军火仓库也全部收缴。夜来沉重的心情,换来今朝胜利的喜悦。
早饭吃过不久,大胡子省委书记汪泽楷(满面胡须,像个老头子,后来看到他剃掉胡须竟是个中年人)亲自来到学总,交代我做三件工作(当时工会等组织领导都不在,只有学总保留原班人马):1立即赶拟一个电报稿,以江西省群众团体名义电请现尚逗留在庐山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速来南昌主持大计;2以群众团体名义欢宴各省来赣的革命领袖和起义军团级以上军官(当时还交给我一张邀请名单,包括转递单位);3和省市党部及总工会一起组织庆祝会,通知全体列名由学总发出。至于在大校场搭会台(南昌开大会一般须临时搭台)则由工会负责办理。大会筹备事宜由罗石冰(他有伤病)主持,我协助。布置完毕,他匆匆走了,我们就顿时忙了起来。面对汪书记交给我们几张军电纸(据说是一等电报,立时发出,记账不须出钱的)可不好办。那位专职吴懋锡秘书可能没有发过公电,只知道电报字少为佳,拟是拟好了,不到几十个字“……敬请我公从速莅临,以安闾阖……”我也就糊里糊涂送去,汪泽楷看了摇摇头,刘九峰却不客气地批评,怎么写些这样简单而又不中肯的电稿,于是他亲自拟写,写得长长的,署的是江西各界团体名义,仍由我送到电报局,刚一交上,就收取了。几位联系宴席的人也回来,江西大旅社说,这大规模的宴席要很多实物备用,这一两日内无法办到,须再过三四天。后到总工会,搭彩台的工人已经派定,马上就去搭台。我再去省党部向罗石冰汇报情况后,石冰指派了几个同志协助开展工作。并告,十点钟后要去省政府西花厅(即当年我被囚禁的所在)参加由国民党中监委(部分到达南昌者)和各省市代表(即流亡在武汉现到南昌的省市革命领袖)的联席会议(省政府和省党部后门畅通),并告江西代表出席者有姜济寰、肖炳璋、黄道、傅惠忠和他等几个人。事后知道这次会议由谭平山主持,主席团中有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以上三人均未到)、谭平山、贺龙、恽代英、郭沫若(尚未到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会,会上通过革命委员会和所属党务、宣传、农工三个委员会,参谋团、政治保卫处领导名单,组成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领导今后的国民革命工作。在第二天(即8月2日)南昌各报(江西民国日报、江西工商报……)刊载了《八一起义宣言书》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立革命机构和各单位领导成员的公告》。宣言指出,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解决土地问题,废除苛捐杂税,尽快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切完全继承以前国民党正统下国共合作,后来一般人认为缺乏改革精神,因而导致失败。这天晚上,我和邓鹤鸣等同志前往江西大旅社,探访新自武汉回来(前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的旧友,一则欢迎他们到来,二则闲谈形势,获悉邹努等已被派往河南去冯玉祥军中搞政治工作,有的如姜铁英则回安徽老家,李松风也不知何处去了。但由于傅惠忠介绍,就认识了几个浙江、安徽、河北的革命领袖如张曙时、朱蕴山(未南下即回安徽)及宋敬卿等,彼此都很热情,他们都将随部队行动。后来张曙时、宋敬卿都在南下时再相逢。
8月2日上午,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典礼和军民庆祝大会在广场举行。除全体委员、各省革命领导和华侨领袖参加外,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达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台上悬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职,军民庆祝大会”横额。先是革命委员会成立就职典礼,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所属各会处领导,排成几行,向总理遗像举手宣誓,由中央委员韩麟符监誓。誓毕,由韩麟符授印,谭平山接收,韩麟符在会上作了简单的讲话,谭平山接上致了答词。接上举行了军民庆祝大会,由贺龙主持,当时台上的主席团有贺龙、叶挺、肖炳璋、罗石冰、姜济寰、陈步翔、周治中(女)、肖素民、李小青、舒国蕾、李郁共十一人。总主席贺龙作了较长讲话,表示将继承总理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我在台上才第一次见到这位英雄汉子,发言是相当慷慨激昂,令人敬佩(详见1927年8月3日江西各报所载江西人民通讯社特讯,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有展列),以后是委员代表及省区、海外党部代表也相继讲了话。最后是呼口号,除了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继承总理遗志,实现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完成国民革命,还呼了中国国民党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这一次会,两个内容,连续开了好几个钟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大会,将永远载入史册。
就在这天下午,团省委接到通知,要动员部分团员干部及进步学生参军,同时通知学总学联准备到乡下工作。除了要我动员宣传外,提出我和傅铭第是今后负责乡下工作。至此,我已经打消了南下参军的念头。因为,组织上已作了决定,必须服从。
8月3日,上午还搞了一些座谈活动,宣传发动参军参干,其他单位也是如此。原定8月4日晚欢宴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省市海外革命领袖、部队团以上干部,由于局势紧张,革命委员会机关及部队即将撤离南昌(但已经不是东征,而是南下广东),有的部队已经准备开拔,欢宴之举,就作罢论。
从8月3日起,我们才知道,宁汉已经公开合作,在庐山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已经改变了态度,既不来南昌,也不东征另觅新路,形势起了很大变化。革命委员会和起义部队,不是“东征”而是“南下”,打回广东去,占领海口,迎接第三国际援助,重建革命基地,再次北伐。从4日起,就有些军队开拔南下,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也给人带来了沉郁的心情。主要是:胜利属于我们是毫无疑义,但是还需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当前,反动军阀即将重来,屠刀即将挥向我们,我们马上即将转入地下工作,那是很复杂,也很困难的。党组织已经作出了应变的准备,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根据组织指示,我和傅铭第留了下来,先在附近地区隐蔽居住,以后再作考虑。学总学联的刘仁、雷洪福、彭学遂、夏香明则随军南下,部队需要青年干部,更需要政工人员。我们当时就马上行动起来。学总原有一所秘密住房(在羊子巷,系当时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出境时租赁的,我在这里住过)虽未退租,但认为不适合(已为人知,不能再用)。照傅铭第意见是先到附近乡下一个亲戚家里先住下来,就此定下来,也把部分东西、个人生活用品整装准备雇人搬运出城。就在8月4日下午,由刘九峰(省委组织委员,他自己也将随军南下)带领着刘仁等二十几个同志前往驻皇殿侧一中的分校军委报到,全被接受,并都安排了担任连指导员及机关工作。刘仁回学总,笑嘻嘻地告诉我,他去的地方是军委会,由周恩来书记接见,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到军队来可要吃苦,你吃得了吗?”刘仁答:“革命不怕吃苦”。周书记连说:“好!好!好!”以后又送了一批,总工会也送了批,参军参干的还是不少。但也有临阵逃脱的,如学总的彭学遂、学联的雷洪福,可能是家庭所迫不让去,作了逃兵。彭学遂是管财务的,手头上还有几百元,后来吴季滨派人去他家要了款子回来(彭学遂的哥哥彭学沛后来做过国民党的外交部长),没有强迫他要去。这些人立被开除出团。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将我还留在南昌暂时在乡间隐蔽一个时期,可能不能回家。我的父母虽然疼爱我逾于其他兄弟,然而保全生命是重要的事,无可如之何。妈妈只嘱我小心谨慎。然而,谁又料到,这晚一别,我就在第四天早上意外地随军南下。
8月5日,迁乡工作已经准备完成。虽然简装,然而也有两挑子东西,包括我一个藤箱,一个皮箱,还一个网篮。转移到近团委的高安同乡会(傅铭第是高安人,以后又上大学,在中正大学当教授),并且已经雇好挑夫,准备6日早晨下乡。在8月5日那天,起义部队还是大批大批的撤离,南昌居民中有些也从城市搬到乡下去,逃避战争灾难,情况十分紧张。却没料到起义部队就在当晚撤得精光,这出人意料之外。从高安同乡会的管理员得知,朱培德军队返师已迫近南昌,谣传朱培德逃散军官就在当晚集结,回到了城内。一大清早,街已无行人,卖点心的小贩也没上街叫卖,而且不时响起了断续枪声,连雇的挑夫也失约不来。同乡会人告,此时再也无法看到人了,谁不怕死。急得无可奈何,正想前往团省委驻地,正好吴季滨派了组委汪继贤来到告知起义部队已在上半夜全部撤离,汪泽楷书记决定因为我年纪虽小,但在南昌红得发紫,留下很不安全,还要我随军南下。趁此荒乱时间,城门尚未关闭,于是,只身一人化装便衣,什么东西也没带,就此冲向顺化门,随着逃难的人群,逃向城外。
从此时起,我就开始了南下生活。别了,南昌。
附:领导机构
一、革命委员会
委员:邓演达(未到)、张发奎(后来除名)、谭平山、陈友仁(未到)、
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后到)、恽代英、
黄琪翔(后除名)、朱晖日(后除名)、周恩来、叶挺、
张国焘、张曙时、李立三、徐特立、彭湃、宋庆龄(未到)、何香凝(未到)、于右任(未到)
主席团主席:宋庆龄(未到)、邓演达(未到)、谭平山、贺龙、
张发奎(后除名)、恽代英
二、参谋团:
参谋长:刘伯承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楷(后除名)
三、秘书厅
秘书长:吴玉章
高语罕、许寰魂、肖炳章
三、财务委员会:
主席:林祖涵
恽代英、姜济寰、罗石冰(未到)
四、宣传委员会
主席:郭沫若(后到)副主席:恽代英
五、农工运动委员会:
主席:张国焘
彭湃、李立三、董方城、陈荫林、郭亮
六、政治保卫处
处长:李立达
七、党务委员会
主席:张曙时
彭泽民、韩麟符、徐特立
八、军事机构
前敌总指挥:前为黄琪翔(后除名),后改为叶挺(兼)
第十一军军长:叶挺 党代表聂荣臻
二十四师长:董朗
十师长:黄琪翔(到东乡后东逃)
十五师长:周士第
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
一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
二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
三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
第九军军长:原为韦杵(未到,后除名),由朱德担任。
离开南昌时实际兵力共十六个团四个营计三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