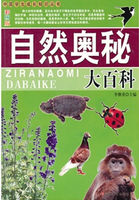一、抗日战起,上饶暂栖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八年的全面抗战。
杭州迫近淞沪,由于笕桥有国民党空军的重要机构,抗日一开始,日本木更津机群,连番轰炸我国空军基地。我当时是在杭州省民教馆工作,地滨西湖,突出湖心,虽然西湖湖光山色,此时已无心赏玩,但求重觅一暂得安全避难之所,虽有此心,终因家口众多,不能轻举妄动。但是,淞沪面临战火,杭市机关纷纷调整应变,或撤离,或紧缩,省民教馆属于后者。十月份起,我在被紧缩裁撤之列,虽想恋栈,实不可能。遂先将妻儿送到兰溪岳父家,衣物托存王文韶公府第,自己独身回到上饶,拜见了阔别七年的严父慈母,经与父母商酌,先将绮云与子女(绍贤、绍康)接到上饶,寄居父母处暂时安置,腾出身子另觅新路。
我是1938年10月间回到上饶的。当时,父亲正在上饶专署工作,专员萧炳章系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厅长,与我曾打过交道。我本来也想在上饶找个工作,无如萧炳章年老怕战火威胁,已上辞呈,因而落空。就在此时,叶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办事处涂振农(此人后被捕投敌)正与徐孔生(即徐先兆,后在江西师院任副教授)前来上饶召集红军旧部,旧友劫后重逢,略谈别后情况,相约到南昌再见。这就引起了我“重回革命阵营”的想法。根据自己的情况,只是暂隐,未曾投敌,当有重回可能。但此时我已成家,而且有一双儿女,自己当然没有什么,但妻儿如何生活,特别是绮云又是一个小学教师,无革命经历,难以同进革命行列,左右确实为难。此时我的大哥正在南昌保安司令部任电台长,我的三弟也携妻树春由西安回到南昌。南昌,这时正热闹非常,知名人士群集南昌,新四军正在组设军部。而我过去在大革命时期的同志同路人不少人在南昌,其中突出的是王枕心(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因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有共乳之谊,熊式辉正委托他在江西招收苏浙流亡知识青年组训。三弟大哥都一致认为我应立即来到南昌,估计能有所作为,坚决主张我立即前去。于是,只有这样,就坐火车来到南昌。
首先,在南昌去新四军办事处见到曾山和涂振农,当然我陈述了大革命、南下失败后的情况与家庭情况。可能当时是新组军队,叶挺又不在南昌,不得要领,仅仅是从涂振农口中透露:“愿望是值得同情的,但还须经过一段时期,自有人来主动找你。”当时不知内情,无法揣摩,但从涂振农语气中隐隐约约以革命者自居,我这个一度脱离革命者自是相形见绌,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但未见到主要人物,也只有听之任之,另做打算。倒是听了三弟的话,去找王枕心谈谈。那时他们正在工专举办知识流亡青年集训(已经临近结束,正好我的七弟也正参加受训),在挂着“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牌子里找到了实际负责的王枕心总干事,毕竟是民主人士,一见到我,十分热情,握手拥抱说:“想不到你还存在人世。”邀到他的办公室,大部分都是老战友,有和我南下的江西中共省委组织部长刘九峰、南昌市的傅惠忠,还有很多当年小干部如黄昆、郝鸿……齐聚一堂,相见倍相亲,全不像在新四军办那样的冷冷清清。王枕心并没经我叙述,一开口就说:“你来得正好,下星期分工,你就和我们一起干吧”,我此时正如涸泽之鱼,还有什么可说。尽管王枕心接上说,这是抗敌宣传服务性质,待遇不高,当然我决不会计较这些。回来后对三弟大哥一说(他们住在一起),也认为暂就是可以。然而,我还是跑到新四军办告诉涂振农,涂表示“也好,你就暂时在他那里,我们以后会有人找你。”(此后,一直无音讯)我也就脚踏实地,决心在青服团工作了。
青服团训练结束了,我应邀参加了结业分工大会,知道我不是留在省团工作,是到外区队搞副职。青服团将六千多人分成了十个队,一队队长何士德,留南昌驻团部,其余九队分往九个区,可能他知道我的妻儿与父母均在上饶,分到上饶的是第五队做副队长,我只提出将七弟步青派给我队,王枕心同意了。全队六十人,三分之二是江苏苏南流亡青年,分为三个组,每组二十人。是服务性质,每个组员仅有十五元伙食费(当时每月伙食约三元),组长30元,副队长50元,队长60元。分工不久,就出发奔赴上饶,一三组在上饶,二组驻玉山。我在全队中均系陌生人,既不能文,又不能武,乃只有分管总务和对外联络工作。工作倒也轻松,他们演剧、唱歌、画漫画、出壁报,忙得很,我无能为力,也无处着手。
开始我不清楚,这一队人马中很复杂,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国民党特务,也有中间人士,很不好相处,我是个外来人,也无法入手。但都不很明显。当然,我这时是心有所属,总是想到过去,也就夜夜梦归故国。在此时也,正当我频频往来于新四军部,思想行动渐次表现。此时也,一些旧日友人,如徐光栋等人,便以访旧为名,整日在我住所,谈天说地,动以利害,劝我别再蹈故辙,另寻新路。有如某人危言耸听,要我考虑妻室儿女;王枕心却一再嘱咐,处事时也应暂时中立,不左不右;而新四军军部一再告知有人联系,音讯毫无。处此时也,处此地也,小心为佳,暂得中立。到上饶后,处于双方对峙状态,更加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奈何,祸起矣。当我主持学生在抗敌宣传游艺大会上魔术表演“国旗历劫不毁”时,国旗数字被毁最后鲜艳夺目出现会场,特务们抓此国旗复失机会,书记长竟上台指出青服团毁我国旗,不由分说,立即破坏大会。事后,队部(当然是CP)支持我应付变乱。不料次日特务(包括外面的、青服团内部的第三组长刘国权)对我提出要挟。在身家、儿女生活的危险情况下,被迫表示态度,决心保持中立,不左不右,从此我在政治上销声匿迹,仅主管队部后勤事务。在国共日益尖锐斗争之下,我虽不右,但人不谅解,可能组织内部已经把我排在敌特一起了,有口难言。不久日本进犯马当,局势严谨,当局另施别计,将现有青服团半数(1到5队)实际上是左翼势力,送往武汉受训重新分工,我当然是去了。到武汉后,我自己并没有到训练营报到,途经第三厅,刚好值星是总政治部旧部,当即引我会见郭沫若。可能此时三厅已在撤退过程中,因郭沫若没有留我意图,但从值星官告,马当已陷落,如果进犯,归家无路,匆匆忙忙,星夜赶回上饶,与妻儿团聚。此时此情,一切都置之度外,任何一切,都在摒除之列。自念生平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仅此一次,中立偏右,是生命史上坎坷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