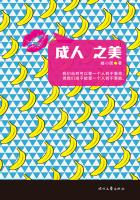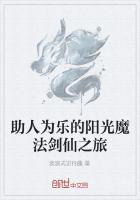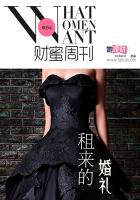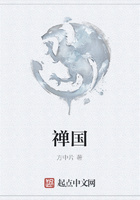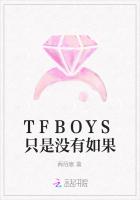一
来到这滨海小城已两天了,也就是说,我同海又相处了两个昼夜。这里,窗下过了马路就是一片海滩。不知什么地方在大兴土木,公社拖拉机成天往工地上运着石块。从远处开来时,柴油机的转动像是什么飞蛾在扑扇着翅膀。拖拉机来到我们窗下就该上陡坡了。这时,它发出尖细的呻吟,还夹杂着磨牙齿的声音。随着夏云的浮动,一牙残月倒挂夜空,时隐时现,海面上闪出微弱的青光。近处影影绰绰地泊了几条种植海带的作业船,舱口依稀还透出点光亮。整个海湾像一只弯曲着的臂肘,潮涨潮落,浪波有时斯文得像在悄悄叠着一巨匹软缎,忽灰忽绿,一折一折地轻轻叠过;有时又势如千军万马,龇着凶恶的牙齿,大声咆哮,真像是不依不饶地追赶着什么。一排接一排,一排催一排,最后都撞在褐色的巉岩上,溅成浪花,然后,重新归入大海。亘古以来一直重复着这过程,无止无休。每个波浪都各有它一段历程,但每个波浪最终都归入大海。浪波——斯文的也好,汹涌澎湃的也好——寿命再长,也是短暂的,包罗万象的大海却是永恒的。它随时准备浪波回到它的怀抱。
我仿佛看见自己的一生也是小小的一道浪波,它在海上奔驰了一段路程,如今,眼看接近海滩,就要撞到那褐色的巉岩上了。然而,也将像以前和以后的浪波一样,归入大海。
大海是永恒的,它将永远存在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希望自己病危时能把呻吟哼成心爱的曲调,弥留之际,脸上将带着笑容向这个世界告别。
我曾诅咒过生命,也悔恨过。当黑色的世界笼罩着我那黑色的心境时,我甚至一度把死亡看得比生命更美丽。但那仅仅是一九六六年八月里的一刹那。归根结底,我是热爱生命的。早年,在困苦中我爱过它。如今,我更爱它了。
我清醒地意识到“风烛”的短促,我和我那一辈人,将一浪接一浪,走到尽头。越是热爱它,珍惜它,就越不肯撒开这支秃笔,我手中唯一的工具。几十年来我都是用它和同时代的人交流思想感情,用它画出我的爱和恨、我的向往和我的噩梦。我知道这是一支拙笨的笔,一支并不生花的笔,但它是我仅有的。
二
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是崎岖的,但它毕竟是越走越宽。
就以收在这四卷集里的东西来说,一九四九年一到北京,我就颇有自知之明地把它们用旧报纸厚厚包起,用麻绳捆紧,高高吊在屋角上,唯恐被人瞥见。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两次作为自传的“附件”上交过。十年浩劫中,它们自然被抄走并作为毒草编了号。如今,在八十年代,居然这么体体面面地同新一代的读者见面了。这是它们的作者做梦也没敢想望过的事。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也可以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僵化的,静止的;革命的圈子并不是铁打或水泥砌成的。人的命运,书的命运,一切的命运都会有变化。因此,没有理由悲观。悲观者只会叹息,而叹息是世上最无用的东西,它不能把世界朝前推动一寸一分。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将会不断地向着合理境界前进——这种信心本身就是生活中的一种动力。有时也许还会倒退一下,还会偏离轨道,但总的来说,在历史长河中,它必然会顺着康庄大道向前推进。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除了一九五六年当了几个月有名无实的(因为还身兼两职)“专业作家”,我一直是个业余作者。我的小说全是我在上学及编副刊时写的,散文和特写则大都是记者生涯的副产品。一点评论不是编刊物时为了凑版面而写的,就是在大学教书时留下的。我有时替自己开脱说,我还当过那么多年记者,编了那么些年副刊,所以才写得少。其实,这只是辩解而已,还是应该怪自己生性疏懒和才具的局限。
即便从《蚕》发表的年月算起,这一行当我也足足干了半个世纪。我生长在黑暗的旧中国,脑袋里塞进过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生磕磕碰碰走了不少弯路,因而这四卷里的内容绝不是响当当的。但既然毕生从事了这个行当,此时做个小结,对人对己也算是有了个交代。我本可以用沉默代替序言,但想到大劫之后党的温暖,社会的温暖,读书界对三十年代文学的念旧之情,我还是鼓起了勇气,提笔同此书的读者推心置腹地谈上几句。
在我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小说仅仅占去五年(1933—1938年)时间。那以后,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小说艺术——不是泛泛地研究,而是认真地把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几位英国大师的全部作品、日记以及当时关于他们的评论都看了。但我自己却没再写小说。对这一点,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有时我想,研究工作和创作活动是相互排斥的。搜集资料,积累资料,在资料中打转转,会使人陶醉,那同更艰苦的创作活动是两码事。记得亡友陈梦家一回对我说,一搞起金石,就不大想写诗了。然而世上也颇有一些学术和创作双丰收的能手,而我则两方面都没什么建树可言,有时想起来不免为自己悲哀。
回想最初那五年,创作欲真是旺盛,仿佛遍地都是题材,拿起笔来就有人物和故事向我扑来。那时为了少交几元宿费,我住在临湖的六楼,屋友多而挤,我都是躲到图书馆或跑到石舫上去写。往往一篇没写完,另一篇的题材就在脑中冒了出来。当时我不懂什么概念,所以也没法从概念出发。我只是挑自己生活中感受最深的写,有时是我早年喜爱的人物,如邓山东和那位拉印子车的;在有些人物身上还投以自己的影子,如《篱下》、《落日》和《矮檐》里的少年。只有《道旁》这一篇可以说是从概念出发的。所以与其说它是篇小说,倒不如说是篇寓言。记得那是在我写完《论出路》那篇简短《答辞》之后,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观点:在大时代到来的前夕,不要光致力于经营个人小天地,整个局面一崩溃,个人那个小天地也就荡然无存了。正是由于从概念出发,通篇人物面目模糊,更糟的是我只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在一九三五年,我对大时代本身的认识是十分抽象的。大震动之后,世界和国家将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清楚。我仅仅不安于那种坐看被蚕食的局面而已。未带地图的旅人只能是个盲目的旅人。
我那时所抨击的社会不公正和宗教奴役都是我自己所亲身遭受的。这,我已经在《一本褪色的相册》里详细谈了。我曾见过一个九代世袭的天主教徒,她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认定生来就是属于梵蒂冈的。宗教就是这样用无形的刀子从东方人的灵魂里把民族感情挖个干净;然而不远万里来传教的人,却以本国的炮舰做后盾。当年就是这事实促使我写了《栗子》里那几篇小说。
写长篇小说需要具备许多本事,其中包括要长于布局,更得有股毅力。我老早就有了自知之明。《梦之谷》可以说是个偶然产物。最初我要写的是一篇回忆性质的散文。我是在骑虎难下的情势下把它写成小说的,而中途全面抗战又开始了。我思想上早把它放弃了,是老友巴金硬督促我把它完成的。然而这篇东西确实浸着我个人深切的感情,既可以作为小说,也可以作为我个人那段生活的记录来读。
看到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昌盛,我十分兴奋。里德、基希、斯诺这些外国人确曾为我们示范过,他们的著作很精辟,很重要,但那毕竟只是“报告”。由报告而发展成为文情并茂的大型文学作品,其产地还是我们中国。这么说一点也不含有文艺沙文主义。理由同志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可称为“散文大国”,散文写作的艺术传统深厚,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主流一直是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关切,这含义要比“干预”更广些,但在我心目中它是包括了干预的。“五四”以来的中国,问题一直太尖锐了,形势太紧迫了,文学不可能是生活的摆设,我认为报告文学的产生和昌盛,主要是由于作家们不能从容不迫地对现实生活仔细端详,慢慢咀嚼,然后,再以小说这个虚构的形式概括出来。正像抗战初期的活报剧一样,报告文学也是由于作家们迫不及待地要对现实生活发言而产生的。
特写(可不可以说是今天洋洋万言的报告文学的前身或初级形式)在我写作中占的位置相当大,我从一九三三年一直写到五十年代,这也许是由于新闻记者是我一生主要的职业。我出了校门就进报社的门,中间虽然穿插着教书工作,但解放前的十四年,在国内外我主要干的是记者这一行。那时我没有条件去从事深入的社会调查,除了《林炎发入狱》和《刘粹刚之死》,我也不大集中写一个人物。我那些特写,像鲁西和苏北的水灾,滇缅公路上的民工,用摄影界的术语,大多属于场景或群像的实地“抓拍”。今天,这个文学形式在成熟,在臻于完善。
当然,这种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文学样式在实际上所遇到的问题、困难和障碍,要远比一般诗歌、小说和散文多。“批判性的报告文学难写,颂扬之类的报告文学也难写了。”然而从这种创作形式所遇到的麻烦中,也正可以看到它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倘若一种写作能使好人扬名,坏人发抖,谁不举双手欢迎,尽力去保护它!因为那样它就“背负着人民的希望”了。只有在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学作品才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报告文学的昌兴,正体现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光大。这种文学形式不但在推动着我们的事业,它的成长对世界文学也是一大贡献。应该让它传播出去,尤其在创建家园的第三世界。让他们知道,我们这里发现了一种更能直接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形式。他们会拥抱它的。
散文同小说相比,除了不完整、不成形(指情节)之外,我认为它还有个特点,就是抒写本人的感受——前人神秘地称之为性灵。我自己的散文写得很平庸,往往眼高手低:动笔之前有一种憧憬,写成之后却很失望。但无论是《叹息的船》还是《破车上》,我都不是在客观地记录什么过程,而是想通过外在景物,抒写自己的一点心绪或感受。
由于有这种偏见,我一生出门交白卷的时候远比写出东西的时候为多。有时跑了一大遭,回来却对着白纸发愣。五十年代我曾写文推崇过何为同志写的那种“千字文”,近来也试写了几篇。这种袖珍文字没法言之无物,在指肚大小的天地里学雕刻,也是练刀法的最好场所。这是学习经济地使用文字的捷径,是值得提倡的一种文体。
人们看文章多看文采,我有时则对语气很为敏感。
我生平怕为人师——所以一向教不好书,我也不喜欢听别人训。不要说盛气凌人,连稍稍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也容易引起我的抵触。这个毛病也许同我早年的生活有关。十八岁前,我都是在寄人篱下或者当学徒,不管是在地毯房还是羊奶厂,我总是看见人们把脸绷得铁青,朝我鼻子抡着食指厉声申斥。我好容易摆脱了那种天天挨训的日子。不幸,中年沦为次等公民,又成为人尽可训的人。尤其在干校,有位小头目仿佛从这类训斥中感到一种优越,得到一种满足。但是我从来也没在训斥面前真正低过头。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感真是一种极为可贵的东西。这种心理关系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尤为重要。搞创作,这个问题不大,一到阐述或评论什么,它就来了。在《寄小读者》和《给青年十二封信》的启发下,我也曾努力同读者建立一种亲切些的关系。三十年代写的《答辞》和八十年代的《终身大事》,都属于这种尝试。
此外,我也曾试用散文来写“论文”性质的东西。三十年代的《欣赏的距离》和五十年代的《大象与大纲》都含有这种企图。我谈的内容不尽正确,文字也欠细腻。我把它保留下来,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深切的希望:写论文也不必绷了面孔,不必硬邦邦,最好也能亲切些,委婉些。
三十年代编《大公报·文艺》时,我曾干过一件傻事:利用编辑职权,花了好大力气,想提倡一下书评。那是我在没出大学门之前就热衷过的一项文化工作,《书评研究》是我那时的毕业论文。编《文艺》时,我曾努力组织起一个“书评网”,并得到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等不少朋友的支持。为了“独立”,我不接受出版商的赠书,那时每个星期我都跑两趟四马路,每次总抱回一大叠书。然后,按书的性质和评者的癖好,分寄出去。“书评”成为那个刊物的一个固定栏目。此外,我又连编过几个整版的“书评特辑”,一心想把这服务性质的文化工作开展下去。记得“八一三”那天,我还在出着这种特辑。
现在看来,这也许不大合国情。在外国,一本书出来后,好像总得有人评那么一下,才算有个交代。因此,他们那里有职业书评家。我们这里并不那样。就目前而言,书出来后,倘若政治上确有毛病,总会有人出来批判。一本来历不凡或特别出色的书出来,也不愁没人写文推荐。一般著作,除非作者自己去张罗,否则仿佛就没有一评的必要了。
我知道书评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不在政治和艺术之间划个界限,书评没法推广。然而随着整个革命事业的高涨,出版物的数量必然要与日俱增。八小时之外的那点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今天,广大读者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书评这个哨兵和向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