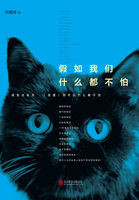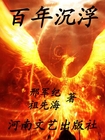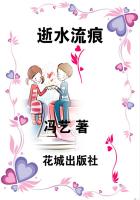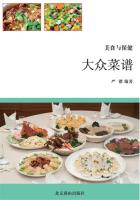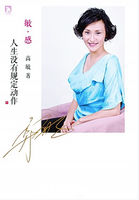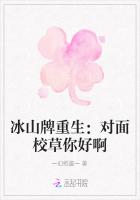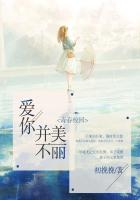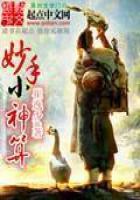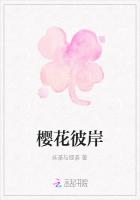七年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甘与苦
一、值得骄傲的特色
一九三三年九月,杨振声与沈从文两先生所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蚕》。不出两年,也即是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念完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进了天津《大公报》。先编一个娱乐性的《小公园》。两个月后,遂接手编《文艺》。转年,上海《大公报》出版,我被调往上海,同时负责沪津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全面抗战打响后,我曾短期离开《大公报》;其间,还曾从昆明为武汉《大公报》遥编过一阵子《文艺》。一九三八年,香港《大公报》出版了,《文艺》也随之而复刊。我一直编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赴英后,刊物由杨刚接编。一九四六年夏,我由欧返沪,《大公报》派给我的职务之一,仍是编《文艺》。不过,那时我的主要职务是撰写国际社评。《文艺》的许多具体工作是由刘北汜负责的。一九四八年香港《大公报》复刊时,《文艺》最初还是由我编,后来交给了袁水拍。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创刊文艺版(报社内通称“八版”)。我曾当过一阵子顾问,直到转年被扣上右派帽子为止。打那以后,我不但告别了报纸副刊,而且在一个时期内,甚至与文学工作也绝了缘。
以上是我一生同报纸副刊的瓜葛。说起来,时间不算短,而且跨越了抗战前夕、全面抗战展开后以及胜利初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刊物都是在洋人鼻子底下编的:天津的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香港那个英国殖民地。由于刊物登了不顺他们眼的文章,天津法租界的黄毛巡捕曾到编辑部来兴师问罪;在上海,曾受过工部局法院的传讯;在香港,刊物多次开过天窗。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没有了工部局,可是仍然有“书报审查处”,动辄就挨黄牌警告。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艺界的是非之地,仅仅两个口号问题,就论战得热火朝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方面急于把刊物编得热闹活泼,同时又在知友巴金的指引下,坚决避免卷入文艺界内部纷争,只当个逍遥派。
“副”刊也好,“附”刊也好,顾名思义,不外乎是“报屁股”。它在报馆内的地位,也许还不及体育版,因为它缺乏新闻性。然而,我一进天津《大公报》,就发现这家报纸懂得:读者要看的不仅仅是新闻,还得多方面充实版面,以满足知识界,使报纸在报道新闻的同时,还能传播知识。《大公报》那时出有不下十一种学术周刊,如司徒乔编的《艺术》,张其昀编的《地理》,张申府编的《哲学》,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这些刊物的编者和作者,大多是当时平津各大学的教授。再加上《大公报》所举办的“星期论文”,它与高校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分密切,从而也使它成为学术界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一道桥梁。通过与高等学府的合作,报纸本身的格调和价值均有所提高。
一九三三年以前,《大公报》的《文学》副刊是由已故诗人及著名学者吴宓主编的。他登过不少珍品,我很希望有人去认真研究一下。我料想《大公报》老板嫌他编得太“文绉绉”了,就交由杨、沈二位接手,改名《文艺》。由于这个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我至今把它看作是自己在文学上的摇篮。
每逢在国外谈起中国报纸的特色,我总首先提到文艺副刊。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辟一章。西方报纸自然也有文艺副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或美国的《纽约时报》,但他们主要登书评。而中国报纸副刊的特点则主要是刊登创作,并且首先是新人的创作。这样,它就具有了育苗的作用。报纸文艺副刊不但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它还影响到东南亚以至全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文学杂志寥寥无几的地方,报纸文艺副刊还成为当地的作家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我认为品评一个文学刊物的成就,主要不是看它发表过多少资深作家的文章,而是看它登过多少无名的。我编《大公报·文艺》期间,确实曾得到多位文艺界先辈的大力支持。这从李辉编的那本《书评面面观》以及林徽因所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可以看出。然而一接手这刊物,我思想里就很明确: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为新人新作提供园地。因此,我才以“文学保姆”自诩。
现在连我自己也难以想象当年我在天津的工作量了。眼下报社文艺部动辄二三十人,而那时非但只有我这个孤家寡人,没个助手,而且除了《文艺》版之外,最初老板要我兼管那十一种学术周刊:发排,校对,通读清样,同主编保持联系,以及寄奉稿酬等等。当时《大公报》还办有一个综合性周刊《国闻周刊》,它的文艺栏也由我兼管。在这情形下,我还能预编出若干期,以便挤出时间赴各地旅行,从事通讯特写。
至于环境,那更会使今天坐在高楼大厦,冬有暖气、夏有风扇的当代同行大吃一惊。当时报社编辑部就设在一间三米宽、三十几米长的大屋子里。一进门就是个长条案子,供国内及国际版合用,其他各版的编辑各占一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楼下是咣当咣当的机器房,对面是日夜喷乌烟和煤屑的法租界发电厂。
开头,所有不合用的来稿我不但一一退还,并且一律附一封信——有的还写得颇长。这种做法终于证明是力不从心的。有些带共同性的问题,后来就写入《答辞》了。一九三六年,巴金把我的《答辞》中的一部分,与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合编成一个集子,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我热爱这份“文学保姆”的工作。首先,它使我步入同辈青年朋友的精神世界,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苦恼与向往。他们寄来的文章,但凡能用的,即便还需要修修补补,我也千方百计让它们见天日。这给予我莫大的快乐。画版样时,我总想把版面设计得既严肃又热闹。上午发稿,下午就能看上大样。第二天黑早,机器房里报纸就像流水般地淌了出来。拿起头天自己设计的刊物,嗅着那未干的油墨气味,其喜悦几乎不亚于一个产妇搂抱自己那刚生下的婴儿。
在副标题上,我用了“甘与苦”。其实,我认为当“文学保姆”的甘,远多于苦。我是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来写这段回忆的。
二、从《小公园》到《文艺》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我戴着一顶黑绸方帽,身披黑袍,在燕京大学的大礼堂(当时称作贝公楼)领到了毕业文凭。春间我已由杨振声、沈从文两位先生推荐,在来今雨轩的茶会上,同《大公报》社长胡霖约好:学业一结束,即赴津上班。工作也谈妥了:编报纸的《小公园》,兼发包括《文艺》在内的其他副刊。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才由英文系转到新闻系的。那纯粹是为了混个新闻记者的资格。我经常旷新闻系的课去外文系旁听,但我渴望有一天能像美国老师斯诺那样跑遍世界各地,直接采访人生。
当胡霖社长要我坐在办公室里编刊物,而且还是个消遣性刊物时,只觉得身子仿佛冷了半截。然而我老早就意识到,在生活中一方面自己要有个鹄的,另一方面又得懂得通过妥协,一步步地争取。所以我丝毫也未露出难色,更没去讨价还价。如果有,那就是向他要求,在我完成编副刊的职责之余,准许我外出采访一下。既然我要求的是“额外”的工作,胡社长当然也立即欣然首肯了。
记得我是七月一日进的报馆。最近翻阅一下李辉编的《红毛长谈》,当月四日我就在《小公园》上发表了一篇《园例》,足足占了一整版,副标题是“致文艺生产者”。我对这篇文章的背景记忆犹新:它来自我同胡霖社长的一次谈话。
接编一个刊物,总是首先看看它原来是个什么样子,特别得翻翻它的家底——存稿。这一翻,可吓了我一跳!有谈京剧的,有谈昆曲、谈木偶戏的。另外,还有大量的旧诗词。天哪,我对这些简直一窍不通,可怎么来编呢?
这当儿,胡社长恰好从我桌边走过。他喜欢抽空在编辑部里转悠。看到我的狼狈相,就问我怎么啦。我向他无可奈何地摊一摊手。他邀我到他那只有六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小公园》这个刊物和我的路子太对不上了。他笑了笑说:“如果对路子,我就不必请你来了。这一版原是何心冷编的,登的全是些茶余酒后的小品。老年读者还爱看,可是青年们对它不大感兴趣。他们要看新文艺作品。你就放手干吧,照你的理想去编。报馆内外的闲言闲语你都别管,反正我完全支持你。”
多么幸运!刚刚走上社会就碰上一位对我如此信任的老板。我立即表示,凡是不便退的稿子,我还是统统把它们登完。只是今后我要另起炉灶了。
翻看一下过渡时期(一九三五年七、六两月)的《小公园》,一定感到十分不和谐,可也奇特有趣。芦焚的小说,缪崇群的散文,李健吾、张庚的评论旁边,却登着齐如山的《论皮黄》和刘澹云的《论昆曲》。魏深介绍路卜洵的《灰色马》,旁边刊着《思凡曲调考》和《清宫之月全承应戏》。
确定了方针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来稿的质量问题。天津爱好文艺的青年得知《大公报》的《小公园》改了方向,成为新文艺的园地,当然很高兴。于是,各方稿件,纷纷投来。我那办公桌所有的抽屉都塞满了,每天还源源不断地涌来。然而来稿大多思想幼稚,病句连篇,即便作为中学生的作文也属次等的。
在《园例》中,我首先设身处地地为投稿者着想:“天气是这样热,别人都寻凉快去了,他(投稿者)得独自躲在屋子的一角,对着一叠白纸发愁。(在那上面,一个建筑师不用砖瓦就盖起一所经得住风雨的房屋!)”声明自己昨天是个投稿人,既没当过屠夫,也不是善于挥斧的砍柴手。编者也有一颗绵软的心,他不甘心把来稿丢进黑暗所在,编者只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埋没可贵的贡献。只要印出来对读者多少有些好处,他永远不会埋没来稿。
第二天,我在刊物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流》的答辞,宣布我们将努力克服对名家的盲目崇拜。“我们的光荣将不在于曾刊登了某位‘老作家’的稿子。”我坚决反对把作家或作品分作几流,然而对于每篇文章得要求它在文字通顺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我在《园例》里还举了一个极为浅显的例子。“当一个地方通讯员踏访一座名塔时,他不可把塔的石阶的级数记错。但一个文艺者……重要的是记下自己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塔的印象’与生活另外的片段联系起来,选择、剪裁、编排,使它成为一完整的独立经验。”
《园例》发表后,果然引起各方面的反响。有的嫌刊物水准太高,有的要求还是刊登旧体诗,但也有不少来信对《园例》表示支持。七月九日,我开辟了一个“读者与编者”栏,就刊物内容和文学观点展开了讨论。与此同时,我又通过《答辞》(如《理发师·市场·典型》等文),一再强调要提高来稿的质量。
接着,我就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设计起刊物的内容来了。
当我编《大公报·文艺》的时候,靳以正在编着大型的《文学季刊》。每逢我抓耳挠腮地安排副刊版面时,对他的羡慕之情便油然而生。只觉得就手中掌握的篇幅而言,他简直像一位阔少,只消计算一下页码,而我则是个穷小子,得一行一行地算。编杂志有如在大圆桌上摆宴席,编副刊则好比在小托盘上拼凑快餐。最初,排字房师傅拼版时,我总站在旁边。有时少若干字,我当场就凑几句《答辞》来填补。最怕的是他说:“多出了几行!”怎么办?总不能砍人家的稿子呀。于是,只好临时另换上一篇。后来我才学会用短诗和版画来调整篇幅——后者尤其便当,因为制锌版时,尺寸大小可以灵活掌握。
编杂志当然也有长短结合的问题,然而五六千字也可作为“短”稿。在副刊上,那就有可能占去半版篇幅。我又是学过新闻的,懂得报纸副刊必须既要有分量,又得多样化。这就要求经常搭配些短诗。另外,我决定在刊物上,辟些专栏。
首先开辟的自然是书评专栏。
两年新闻系的教育,除了激发出我对旅行通讯的兴趣,还使我认识到书评的重要性。那也正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我认为书评最适宜刊登在报纸副刊上,因为又快又及时。既涉及文学,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我先从文艺界友人及投稿者中寻找肯干并擅长写书评的人。最早参加这个书评队伍的有黄照、李影心、宗珏、杨刚、刘荣恩、常风几位。根据他们各人所长,大致有个分工,比如洋书大多请杨刚或刘荣恩来评。有些评论既及时又有分量,例如,李影心评老舍的《离婚》,以及杨刚评斯诺的《活的中国》。
同时开辟的尚有《文艺新闻》。当时报刊上常登些“文坛消息”,谈的大多是一些私人琐事,其中也不乏捏造的谣言。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声明:这一栏中要摒除作家的私事,只报道与文艺有关的活动。今天,倘若有人关心三十年代各地文艺界的动态,诸如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刊以及文艺团体的情况,不妨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大公报·文艺》的这一栏。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小公园》,确实颇为热闹,既有严文井、张秀亚、田涛、蔺风萼(柳杞)等北方新秀,又刊登着南方知名作家叶圣陶、巴金、张天翼的近作。版面上各种专栏之间,夹着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和我那署名编者的《答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