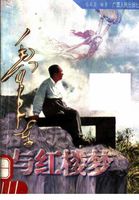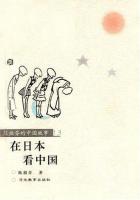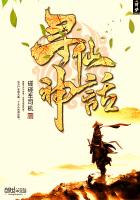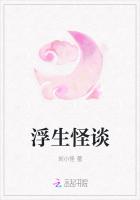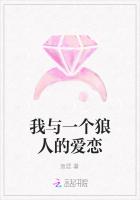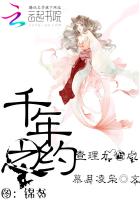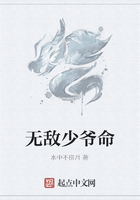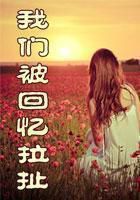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小公园》同《文艺》这两个副刊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八月间,杨振声、沈从文二位先生就向报馆建议,索性把他们两年来所编的半版《文艺》(每周三期)交给我,他们只编《星期文艺》。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起,就开始这么做了。转年上海《大公报》出版后,他们二位干脆连《星期文艺》也一并交给我来编了。因此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大公报·文艺》,实际上经历过这么三个阶段。
这样,一九三六年秋,我就全面负责沪、津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平时三个半版及《星期文艺》的整版)。在北平的杨振声、沈从文,上海的巴金、靳以以及许许多多知友的支持下,我就更加起劲地投身于这项工作了。
关于这期间的《大公报·文艺》,有四件事理应在此着重记述一下:
(1)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文艺》以整版篇幅出了悼念特辑,而报社总编辑王芸生却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写了不署名的短评攻击鲁迅。上海文艺界群情愤慨。那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向报社提出辞职。我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时,曾提及此事。然而我当年在《大公报》并不上夜班,对这篇恶毒文章的作者只能臆测,所以并未指名。张篷舟根据亲身经历,在《鲁迅逝世采访》(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〇年第一期)中,才披露出全部真相,可以参阅。
(2)关于一九三六年为纪念《大公报》复刊十周年而举办的“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经过及结果,以及评选委员会对获奖者的评价,均已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中写过了。胡霖社长在听取我的建议后,还同时提出举办“大公报科学奖金”,而且从数额上可以看出,报社显然对科学更为看重。为了增加这篇回忆录的史料性,我把当时《大公报》举办这两项奖金的启事补充如下:
敬启者本报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刊,中间曾于民国十四年底停刊数月,至十五年九月一日复刊,迄本年九月一日,适为复刊满十周年之期。兹为纪念起见,特举办科学及文艺两种奖金,定名为‘大公报科学奖金’及‘大公报文艺奖金’。由本报每年提存国币三千元,以二千元充科学奖金,一千元充文艺奖金。每年得奖人数:科学拟以一人至四人为限,文学以一人至三人为限,即自本学年开始,至学年终了为一年,每年评选一次,定期三年。如有变更,至期满另行通告。并经聘请学术界先进孙、严济慈、曾昭抡、杨钟健、胡先骕、刘咸诸先生担任科学奖金审查委员。秉志、杨今甫、朱佩弦、朱孟实、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诸先生担任文艺奖金审查委员。
关于文艺奖金详细办法,业经拟定。一俟科学将金办法由各委员商妥后,当再同时登报公布,兹值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之日,特先通告,资纪念并祝学术界进步。
(3)同样为了纪念十周年,还由林徽因编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这本早已绝版的集子,一九九〇年又由上海书店重印了,编入《京派文学作品专辑》。关于此书,可参看倪墨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启示》一文。
(4)由于刊物登了陈白尘所写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控诉在不抵抗主义的重压下,连带有抗日色彩的戏也不准上演的痛心事实,触怒了上海工部局,多次开庭传讯。此事经过我也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中写过了。
发生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这四件事,已各有另文记述,这里就从略。只说明刊物有过一些作为,但也并非一帆风顺。
三、活泼与分量
附在报纸上的副刊必须编得活泼有趣,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要使副刊在文艺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又必须同时有些分量。当然,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最好不过。接手《文艺》之后,我就是本着这一理想去干的。
为了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除了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及翻译外,我还不断地开辟专栏。《文艺新闻》列出后,不断收到有关外国文坛的报道稿,于是就创立了《海外文坛》。这一栏主要是由清华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毕树棠负责,有时也发表另外几位的,诸如黄源所写关于日本出版了《高尔基书简集》的报道。此栏对不少西方作家也作过简介,如德国的里尔克,法国的莫洛亚,西班牙的阿索林。当然,刊物也并未忽视当时被称作“弱小民族”的东欧。通常这一栏每篇只有几百字,但吴达元关于《费加罗的婚姻》、罗念生关于梵乐希,以及张香山关于日本文坛的鸟瞰式报道,均长达七八千字。
我一直认为,凡是外国出版的涉及我国的专著,以及单篇而有分量的论文,我们都应作出评论;正确的,应予以肯定;错误的,宜加以纠正。同时,我相信外国汉学界出了有关我国的著作,自然也渴望听到我国的反响。例如赛珍珠(当时称作勃克夫人)对三十年代中国创作界所作的评价,《李白诗集》的英译本,以及斯诺的《活的中国》,我都立即组织人写了评论。当然,还要让国内读者了解外间关于我们有些什么论著。例如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文学与用语》一文,就由朱自清译了出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的《文艺》副刊上。更为珍贵的是中外作家的交往。梁宗岱的《忆罗曼·罗兰》(见1936年6月17日的《文艺》),正如徐志摩关于曼殊斐尔的回忆,至今仍值得一读。
我是一个喜爱并尊崇诗歌、却不懂得更不会写诗的人。接手《文艺》后,我自知这是自己的致命弱点。然而刊物上又不能不登诗——文学金字塔的顶峰。我在刊物上经常不断地登载诗稿,甚至曾以整版篇幅发表过孙毓棠的长诗《宝马》,然而又觉得还应该请一位诗人来主持一个诗歌园地。于是,就开始了《文艺》的另一创举:刊中有刊。报社把刊物委托给我,我再抽出部分篇幅邀请名家来代编。最初的尝试是请梁宗岱主编“诗特刊”。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出版的创刊号的阵容是:何其芳的论文《论梦中道路》,毕奂午、林徽因、方敬、卞之琳、曹葆华、王辛笛和方敬的诗作。另有李健吾与卞之琳关于“你”的讨论,刘荣恩评阿克敦与陈世骧合译成英文的《现代中国诗选》。那以后,这个特刊不但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诗作,还登过不少关于新诗(如音节问题)的讨论。吾师郭绍虞的《从永明体到律诗》也曾发表在“诗特刊”上。这种“刊中有刊”的办法,很受读者欢迎。
另外,我还请黄源主编过《译文》。这个刊物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创刊的。首篇是鲁迅所译嘉尔陀尼·吉柴(匈牙利)的《画家在乡村里》。同期刊有金人所译良士果(苏联)的《金牙齿》以及丽尼译的哈尔斯特隆(瑞典)的《鹰》。
我对美术也完全是个外行。然而这又是刊物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当时赵望云正在探索用国画来描绘民间生活。我们二人曾一道去鲁西采访水灾,《文艺》发表了不少他所画的贵州少数民族速写。但用得更多的则是李桦、彦涵、古元、新波等人的版画。黄永玉的早期木刻就是在四十年代的《文艺》上登出的。记得木刻家木彬刻过一幅《日本侵略军》,在香港发表时,标题只好按照英殖民当局的规定,改成《×××××》。登出后,人人都能从蛮横形象猜出原题该是什么。漫画方面,还刊登过日本佐宗美邦画的《物资缺乏下的所谓节约》,那是属于自我嘲讽的。我个人对版画的兴趣也是通过那时编副刊而形成的。
对文学而言,一九三六年是个很不吉利的一年。中国失去了鲁迅,苏联失去了高尔基。《文艺》分别出了追悼特刊。为纪念高尔基而出的特刊上,记得黄源的题目是《高尔基是不死的》,而萧军的题目是《死了!我们伟大的母亲!》。
一种颇受瞩目的特辑是邀请多位来谈一部作品。曹禺的《日出》和孙毓棠的《宝马》都曾是这种集体评论的对象。这样讨论的出发点是避免由一位权威对作品一锤定音。集体讨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有时还会反映评者的某些生活体会。例如靳以对《日出》中陈白露的看法,就同经常在他的小说中出现的一个主题分不开。集体评《日出》时,我甚至曾和自己在燕京的老师——美国人谢迪克也组了稿。五十年代在《文艺报》工作时,一次侯金镜对我说,他对谢迪克那篇印象最深。接着,他赶紧小声叮嘱我说,这可是咱们个人之间的私话。我了解他的心情。好在这位可敬的评论家早已去见马克思了,而即便他依然健在,大概也不会由于这么一句话就成为大批判的对象了吧。
特辑中,较为系统的是围绕书评的那一系列讨论。感谢李辉和人民日报出版社,那几个整版的讨论已基本上反映在《书评面面观》里了。原计划分别请读者、作者、图书馆员、出版家以及评论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谈书评,可惜突然到来的“八一三”事变把这计划打乱了。但最重要的几个专辑(首先是作家论书评)还是登了出来。
在编报纸文艺副刊时,除了经常注意其他报纸的副刊(包括发现有无重复或抄袭)之外,还得留心文学杂志上的栏目和内容。自然,更要自己开动脑筋。三十年代常有作家现身说法,谈个人的创作经验和体会。这类文章多为人们所爱读:一是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文学青年在创作道路上的摸索。
《文艺》发表过曹禺的《我怎样写<;日出>;》和孙毓棠有关写《宝马》的自述。苏雪林在谈自己写《鸠那罗的眼睛》的经过时,就坦率地承认是受到沈从文《月下小景》的启发。对读者来说,这无疑是极为有益的提示。
这类由作家自己出来谈创作体会的文章近来少见了。这种文字也许不大合乎今日的中国国情,然而不论对读者还是对研究者,都是大有裨益的。这里就要看编辑的本事了:首先要弄准有哪些作品值得这么深入地去探讨,然后设法去劝说作家。一般说来,写了得意之作的人,是肯于向读者交交心的。
报纸文艺副刊上可不可以登点论文?我认为偶一为之是可以的,而且会有助于增加刊物的分量。《大公报·文艺》出过“小说选”,然而并没出过“论文选”,倘若出了,我相信其价值绝不会低于前者。例如沈从文的《穆时英论》,朱光潜的《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以及梁宗岱的《新诗的十字路口》,今天读了仍能给人以启发。有些论文现在虽已失去光辉,但在当时还是切合时宜的。例如李影心的《珍本与名著》就对当年的出版倾向及时地提出意见。
刊物始终游离于当时的文艺内部论争(如两个口号)之外,然而有时也并不躲避争论。只要争论的问题本身有意义,还既可增加刊物的深度和分量,又能使它活跃些。
在评论方面,卞之琳与李健吾(刘西渭)之间曾反复展开过争论,或者说,就《鱼目集》的评论进行了至少三次对话。如今评者李健吾虽已仙逝,但诗人卞之琳则仍健在。据我所知,尽管他们二位争论得那么激烈,但始终未伤到个人之间的和气。这比相互之间只要一争论就翻脸来得健康多了。
李健吾那篇对《鱼目集》的评论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的《文艺》上发表后,作者对李健吾在评论中所说“没有内容”,显然十分光火,认为那只是一句时髦的评语。“您(评者)翻开一本诗集,不必体会诗中的意义,一目十行地专心注意用字,倘若其中用风花雪月的字眼多,您不妨舍去其他字眼,单把这种字眼录下来,再挑一本用‘痛苦’、‘饥饿’、‘压迫’、‘奋斗’这一类字眼多的诗集,把其中用的这些字眼也录下来,比较一下,统计一下,就可以结论了,说前者‘没有内容’(或者,为的周到起见,不妨补充一句,说虽然技巧圆熟),不如后者。可是这个‘内容’上并无任何形容词,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们可以说橘子没有栗子的内容,可是我们可以说橘子没有内容,而栗子有内容吗……我以为材料可以不拘,忠君爱国,民间疾苦,农村破产,阶级斗争,固然可以入诗,风花雪月又何尝不可以写呢?”诗人最后说:“总之,随便人家骂我的作品无用,不合时宜,颓废,我都不为自己申辩,唯有一个罪状我断然唾弃,就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内容’。”(《关于<;鱼目集>;——致刘西渭先生》,见1936年5月10日《文艺》)
评者在答复中说:“一个读者,所有经验限于对象(一部书,一首诗)的提示,本身和作者已然不同,想象能否帮他打进读书的经验,即使打进去,能否契合无间,正如一句伤心的俗话,‘天晓得!’”(《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见1936年6月7日《文艺》)。
这里追述这一争论,因为我认为这是当时文艺界一种健康的现象:作者与评者坦诚相见。作为读者,则获益良多。倘若双方都客客气气,隐瞒观点,对各方面均无好处。
四、脱了马褂,换上戎装
香港《大公报》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复刊的,《文艺》在同一天又与读者见面了。我一直编到转年九月一日登轮赴英的前夕。那以后,就交给杨刚编了。
自从我接手编《文艺》以来,它经历了一番巨变。原先它穿的仿佛是士大夫的长袍马褂,联系较多的是“五四”早期的老作家。我经管后,新一代作家群成为中坚力量,可以说穿的是学生服。在香港复刊后不久,学生服也穿不住了。随着大时代形势的演变,刊物换上了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