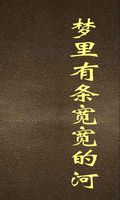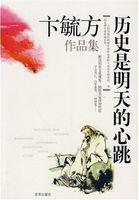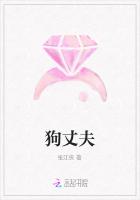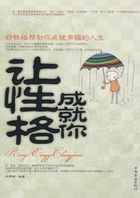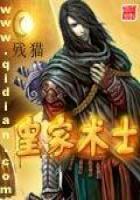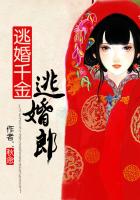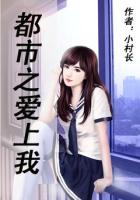第一次去国际笔会所作的演讲,讲稿立刻被该会秘书长赫尔门·奥德(Hermon Ould)索去,编入他主编的《笔会丛书》了。那其实只不过是本小册子,书名《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全书共分七章:(一)告别了老古玩店;(二)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三)诗歌在十字路口,(四)戏剧:宣传喇叭;(五)散文随笔;(六)精雕细镂与大刀阔斧;(七)翻译:广泛的流行。
书由老资格的阿兰与恩温出版公司出版,那是第一次较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五四”及三十年代中国文学。那原是我从香港动身前所准备的一份讲学稿,没在东方学院用上,却为笔会讲了,并成为我在英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当时,我确曾有意把它发展成为一部更完备而有系统的中国新文学史,后来去剑桥读书,接着又去采访二战,所以就搁置下来了。有位名叫“君干”的先生曾节译过其中一部分,刊载在一九四〇年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一九四六年,瑞士还出了该书的德文译本。
我的第二本书是一九四二年出版,一九四四年再版的。书名《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是由向导出版社出版的。书仅一百四十页,却附了近百幅精美照片,其中除了滇缅公路那几幅是我自拍的外,其余都是出版者找的。有些——如关于早期的工业合作社的,还很珍贵。
此书共分十五章,除了《滇缅公路》和《刘粹刚之死》是我根据旧稿自译的以外,其余大都是我在英国各地所作有关抗战中的中国的讲稿,第一章是“当古老国家的危险”,我向西方人提出,不要把中国当作古玩店,要他们正视从几千年沉睡中觉醒过来的中国。
一九四四年是我在英国出书的丰收年。阿兰与恩温公司这一年又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都是我在剑桥那两年研读之余自译的,内收有《蚕》、《矮檐》、《篱下》、《栗子》、《俘虏》、《雨夕》、《在破车上》、《邮票》、《花子与老黄》、《印子车的命运》。此书曾印了几版,一九四五年,瑞士出了德文译本。书后还附了《旁观者》、《论坛》、《收听者》等刊物对此书的评论。一九八四年,外文局在伦敦原出版社的同意下,曾把它编入《熊猫丛书》在北京再版了。
一九四四年,向导出版社又印了我编的一部文选《手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全书分六部分:(一)历代英国文人笔下的中国,内分诗歌、散文随笔、传记和书简;(二)六个世纪以来欧洲旅游者笔下的中国。(三)人物画廊,分男女两部分:女的从《孔雀东南飞》到宋氏姊妹,男的从孙中山到张天翼;(四)中西文化交流,内分地理、文学、科学及政治;(五)有关中国文史哲、绘画、音乐、园艺的论述;(六)民间文学:内分格言、谚语、儿歌、幽默及讽刺等。后边附有几首英译的中国民歌,如《孟姜女哭长城》、《探亲家》、《梅花三弄》等,并附有五线谱。
这些内容大都出自我抵英后在旧书摊上搜集的一些书中,编写十分顺手。但为了取得原著译者的同意,我足足写了上百封信。大多数回信都表示:“同意,请按照时价付酬。”可是有一位当时在英国赫赫有名的诗人(出身贵族,二十世纪初到过北京)回信说:“时价每千字三镑,但我要五镑。”我把这封令我吃惊的信拿给一位英国朋友看。他竟毫不感到奇怪地说:“这是表示他的身价。”
这本书很对英国读者大众的胃口,虽然部头大(五百多页),却颇畅销。
旅英七年,我最后一本书题为《龙须与蓝图》,这是我在伦敦中国学会的一次演讲。在英国作演讲,组织者常请与讲者熟悉的名流任主席。曾经主持过我的讲演的有《世界史纲》的作者H.G.威尔斯和评论家戴思芒·麦克锡。作《龙须与蓝图》演讲那回,他们请的是小说家E.M.福斯特。我讲完后,他还做了一段十分俏皮的结束语,提到了曾经在本世纪初到过中国的他的好友娄斯·狄金斯。正是受后者的影响,他早年就仰慕东方。他颇为遗憾地说,可惜他走到埃及和印度就再没东进了。他的最闻名于世的小说是《印度之旅》。
在上述同一书中,还有我的另一篇讲稿,题为《关于机器的反思——兼论英国小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那实际上是出自我当时正为剑桥皇家学院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来为了当战地记者,学位半途而废了。文中我谈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劳伦斯等人小说的读后感。此外,还有两篇文章:《易卜生在中国》及《文学与大众》。
一九八四年,香港三联书店又印了我一本英文书:《<;珍珠米>;及其他》(Semolina and Others),除了《龙须与蓝图》(此文有傅光明的节译,刊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号的《香港文学》上,并作为附录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之外,书中还收了我自译的小说《珍珠米》、《皈依》、《雁荡行》等,以及三十年代初在辅仁读书时所译的《王昭君》(郭沫若)、《湖上的悲剧》(田汉)及《艺术家》(熊佛西)这三个早期的剧本。
八十年代我精力差了,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Traveller Without A Map)只好请美国青年汉学家金介甫译成英文,先由英国赫金森公司出版,后来美国斯坦佛大学出了美国版。此书还有日本汉学家丸山升、江上幸子及平石淑子的日译本(两卷),由花传社出版。另外,原书还先后出了香港及台湾版。
同国内出版社比较,国外的出版社合同订得细,执行得也严格;然而光是一买一卖,谈不上什么人情味。中国出版社订合同之前,社长或总编辑往往会登门拜访,有时还会带上几本该社出的书,希望建立关系。西方出版社来打交道的,一般就是那本书的责编。合同上一般比中国出版社多一条:保证售完及时再版。(这一点台湾出版社做得也很好。有位朋友送过我一本书,打开一看,竟是第二十一版。他们每版印的册数不多,但再版次数本身往往就带广告意味,容易吊人胃口)
另外,外国出版社还有个特点:每出书必由出版社分寄给报刊书评家。同时,他们十分认真抓出书目录,定期印成小册子,有的按名单发给个人或团体,大批的则交由发行部门放在书店台子上任读者自取。换言之,出版社的责任不仅是把书印好,还要协助推销。我们这里,即便很大的出版公司,也未必拿得出一部本版书目来。
巴金在三十年代主编的《文学丛刊》,每辑有十六册。他在每册的版权页上都附以全辑的书名及作者。这样,就便于有心的读者把丛刊买齐。另外“文生”还利用封底内页刊登同类书的广告,以书推广书,这是极好的办法。不少书的广告还是总编巴金亲自执笔的。不知《巴金全集》的编者及研究者可有兴趣搜集一下?
我总觉得我们出版界存在一个出版与发行的接轨问题。以前,或者国境以外,书一脱销,卖书者(书店)就立即通知出版者。这种联系应是经常的。当然现在遇上特别畅销的书,如《廊桥遗梦》,也有这种联系。但我认为书一旦脱销,就应考虑再版。这样就不会有今天的情况:某书出了如不马上去买,以后就休想再买到了。
一九四九年后,除了柏各庄农场那三年及“文革”,我基本上又回到柜台里面。先是在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转到作协,四年后,就当了“右派”。一九六一年结束了农场的劳动,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阵子,我忽而副主编,忽而是戴罪立功的“工作人员”。七十年代末,又当起顾问。反正没离开过出版口。
我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参加由乔冠华和龚澎主持的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九四九年跟随地下党来到北平,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前身:国际新闻局。开头在南河沿一座小四合院里工作,统共才七个半人,因为领导乔冠华的主要岗位在外交部。如今的外文出版社已是多层大楼、干部员工超过五千人的大单位了。
这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出版社。首先,它用的是外文,因为读者对象是洋人;更重要的是它不但不需盈利,甚至也无须自负盈亏,因为它搞的纯粹是对外宣传。当时,我们编了开国初期唯一的外文刊物《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最初只有英文版,后来扩大了),运到印度时售价还不够邮费。这个单位的主要业务是出版《人民中国》。另外还有以书的形式介绍新中国事物的编撰处,下设英、法、日、德、印尼等语种的小组。
那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年月,整个国家的体制都以老大哥为榜样,我们那时自然也在向苏联模式看齐——而且像不少单位一样,也聘有苏联顾问。有些热爱苏联的干部甚至起了苏联名字。所以楼梯上常有人喊“尤里”或“萨沙”。那时颇有几位教授丢下学了一辈子的英语,改学俄语。上突击俄语班时,甚至不见客,不接电话。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亚非拉,确实很想了解我们的一切。例如,我于一九五〇年去湖南参加土改后所写的长篇报道《土地回老家》(How the Tillers Win Back Their Land)出版后,竟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那是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又是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威望最高的五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频频出访西方及东南亚国家。每逛书店,必先看看他们有些什么中国书。我常常很失望:那些书店里,中国的书籍几乎清一色是港台出的。我们这里出的很少见到,外文局出的更是一本也没有。一问(无论在伦敦还是旧金山),都说只能去专卖“共产党国家出的书”的左派书店买。那往往是一间门面的小书店。在伦敦,就是柯累兹书屋。我问过一位汉学家,我们的外文出版社不也出了不少现、当代文学名著,如《青春之歌》的英译本,为什么不能陈列在一般书店里?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只因为书脊上印着北京外文出版社的名字。”在他们心目中,那就是“宣传”,而坚持个人独立思考的西方读者对“宣传”一向没有好感。后来改用“新世纪出版社”,那套书也改名《熊猫丛书》,情形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