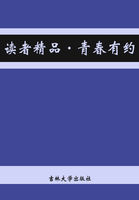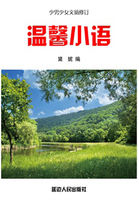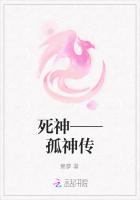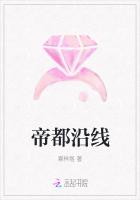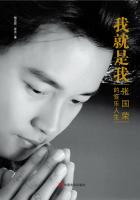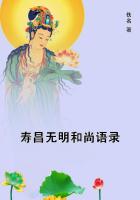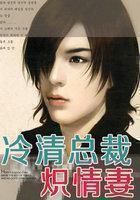我认为搞对外宣传,就得首先摸准心口中的对象,不应只限于对中国友好者。我甚至认为,主要对象应是对我们毫无所知的,甚至是不友好的。应当通过阅读我们的出版物,把他们争取过来。
从外文出版社,我一步又迈入了当时唯一出文艺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今天很难想象偌大个中国,只有那么一家印古今中外文艺书的出版社。然而那是大一统的五十年代,那时,出版社外国文学方面的出书计划,基本上是以苏联外文出版局的书目为依据,创作选题则控制在隶属中宣部的作家协会创委会手里,可不像现在,一部书稿东家不要可以给西家。那年头,像挨过骂的沈从文、朱光潜和我的书,连文学史都不提一个字,出书就更没门儿了。就是许多循规蹈矩没惹过事的作家,如果仅仅属于控制使用而不在团结之列,也休想挤入名单。一九五六年,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确实松动过一阵。通俗出版社还印过我的一本描写大连集体农庄的小册子《凤凰坡上》,事后也不晓得向我约稿的那位受没受处分。
当王任叔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他曾搞过一个十年也出不完的“五年规划”。六十年代初,我可能就是在那一计划下,译起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文革”后期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我以及我们那伙“牛鬼蛇神”于七十年代中叶被编入北京出版口的翻译组。当时,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中南海和外交部,集体翻译一些国际人物(如麦克米伦和肯尼迪)的自传和回忆录以及主席想看的什么书——如一次三天之内,我们突击译出一本《拿破仑论》。
一九七九年,随着国家的复兴,一些五十年代文学史上打入另册的作家的书又问世了。那时,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水楼台,那里最早出了我的《散文特写选》和《短篇小说选》。接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又要我编起文集。萧军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我不知道够不够“文物”的格,反正冻僵了三十年,又缓过气儿来了。我那些用旧报纸包起束之高阁的旧作,忽然又从“毒草”变为香花了。
然而我并没大意。五十年代的魑魅始终在我眼前徘徊。我并没让我的旧作原封不动地与读者见面。花城出版社要重印《梦之谷》时,我首先就把原书里夹杂的一些外文全抹掉。三十年代我力求把语言的感情内涵加深,追求形象化,并强调独创,因而句子往往挺长,有些洋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里对语言大众化、民族化、科学化的指示,我就对旧作大砍大伐,尽量符合那“三化”,只希望在下一场运动中,辫子可以少一些,甚至没有。到后来,我才从一位研究者那里知道,包括当时的文坛泰斗郭沫若在内,来自白区的作家解放后出版旧作时,很少人没动手砍伐的。不同的只不过是有人为了证明自己一贯革命,有的则是怕以后再挨批。这种改动肯定为日后文学史的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
我那些重印的书,也流传到了海外。以香港为例,那里的赵令扬及黎活仁两位教授就曾写文通过对比对我发过难,怪我不该这么糟践自己的东西。成都有位青年研究学者龚明德也曾来信责备过我。他多年来似乎都在研究一九四九年前后的版本问题。这是个极有意义的课题。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本应保存原来面貌,这么改实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倒是应追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幸好那以后出版社都印我新写的书了,再无须提心吊胆,改头换面。不过一九九二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我的六卷集时,又根据那里的政治规格改了几百处。例如,所有“新中国成立后”或“解放后”一律改为“一九四九年后”。凡是“地下党”字样一概删掉。凡批判国民党处(例如“党部靠山”或对“青天白日”不敬处),都删得一干二净,甚至“解放区”也不得用。那六卷书可以说几乎已面目全非。
幸而不怕麻烦的傅光明君目前正在用解放前的版本重编我的小说和散文,还原作以本来面貌。我那些经过两遍筛子的旧作有望重见天日了。这也表示我对前进中的社会的一点信任:像五六十年代那种大批判,估计再不会复返了吧。
不久前,我出了一本书,书名为《我这两辈子》。那是以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那次自杀被救活为界的。洁若常说:那回要是死了可真冤啦。然而多少比我高明的前人,创作如陈梦家,翻译如傅雷,不就那么被摧残掉了吗?
这十几年,他们的冤魂时刻在催逼着我:既然活了下来,就不能让这杆笔闲住,丝总有吐尽的一天,但只要还能吐,我就绝不闲下来。洁若还说:“你年轻时贪玩,老来倒分秒必争了。”这是因为我把八宝山,把死,当作我的动力。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曾为出版多元化戴过帽子,栽过跟头。现在事实证明,高唱“双百方针”的同时,却在出版界搞“只此一家”是讲不通的,那也是对文化事业极为不利的。八十年代初,出版界就如童话里的宝石花那样,先只是一家省立出版社,一转眼原来的编辑室或组都分了出去,各自成立了古典、现代、翻译、儿童等出版社了。另外,还有更多的综合出版社。出版事业确如雨后春笋。原来出版社里许多被捆得死死的干部、编辑,分出来后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精美的画册和各类多卷本的丛书也纷纷问世。各种文学奖纷纷设立,有的出版社盖起大楼。人才不再被埋没,智慧不再闲置了。今天,出版事业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太阳里也总有黑点。
八十年代,一个刊物只因登载了一篇《向前看与向钱看》的文章,立刻就被封门大吉。可九十年代“向钱看”变得赤裸裸了,有人甚至拍着胸膛自称起“亿万富婆”。
在向钱看的大潮中,表现在出版业的,一是重复出书。其实,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丑陋的中国人》印了二十来版。九十年代重复出书问题更为严重了:《高等数学》出了一百七十八种;《中国革命史》二百零三种;《马克思原理》二百五十种……据说,这现象是实行了出版社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事:为了达到指标,大家就争相出版畅销书。于是,就产生了这种重复的现象。
我不明白的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出版有专门机关管理,怎么还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九十年代初,我在政协提案中就曾提出个别出版社规定每个编辑每年必须卖三个书号的严重问题。曾几何时,现在私营书商的发行网已堂哉皇哉形成几乎与国营出版社分庭抗礼的第二渠道。我以前总把这一渠道同黄色书刊或盗版书画等号。事物都在前进。有些档次、品位十分高的书,如《世界小说流派文库》(十三卷)或波波留夫的象征派小说,竟然都是通过这第二渠道出版的。有位青年诗人气愤地说,倘若没有书商,连一部诗集也休想印出。虽不完全是这样,可是出版社把选题拿出去一征订,反响却往往是零。按常规办事的出版社只好不出,而书商就敢冒那个险,甚至可以让诗集再版!
《北京青年报》(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二日)刊有作者老猜一篇谈书商的文章,其中提到二渠道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图书交易会,说近年来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进入书商领域,书商的视野开始有了变化。他们既媚俗,也媚雅。有些书印得远比出版社的漂亮,纸张好,书脊压得板直,清一色的勒口减精装。他们熟悉社会心理,深知“情”与“殇”结合所能产生的巨大震撼力和穿透力。一个书商抓住京味文化的潜在魅力,推出《老舍文集》,说明他们具有文化眼光和良好的市场洞察力。相反,许多国家出版社则靠吃“剩饭”(出再版书)来维持。
文章最后说:“书商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应运而生的产物。”并建议“管理它,研究它,引导它,借鉴它”。
我很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它承认客观事实,不教条。以前光禁,越禁它越兴旺,何如让这第二渠道成为国营出版社一种刺激,一种鞭策。这就要看出版社能不能更有点胆识和魄力,更适应九十年代的节奏了。
这里,我还要替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买书者呼吁:书价涨得太快,太狠了,大大超出一般读者的承受能力。一本用途最广、案头必备的《辞海》,一九七九年出版时,定价为二十二元二角。到一九九五年竟然涨到一百六十八元。据说,这中间有个窍门:把书价定高了,批发时折扣才能多打一些。于是,出书者和卖书者都沾了光,可苦了广大读者,苦了买书人!
这样,把“为文化服务”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是白搭。要对读者“献爱心”(九十年代中国商界发明的时髦语!),就得看手里的算盘怎么打了。
我把心坎上顶关心的问题放在最后,这就是应该有独立于发行之外的书评。
把书的评论与广告之间画等号始终是我们对书评有意或无意的莫大误解。广告是为出版者服务的。它只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书评则是为读者服务的,它没有文学批评那么全面、高深,但它比文学批评要及时而且扼要。九十年代书出得那么多,可书评却零零落落。
几年前,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书评会议,主持人把我接去,要我讲几句话。坐在台上,我望到会场上黑压压足来了五六百人。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位献身于文化界这一咨询行业!出于好奇,我问主持人: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全是首都及各地出版社里搞发行的同志。原来书评作者还是推销员的化身。目前也有一些有关书评的刊物,但重点往往放在中外文坛掌故及消息或外国书的介绍上,对新作的评论所占比重很少。
三十年代我就曾站在买书者立场为书评大声疾呼过。六十年后的今天,书评依然没形成一股力量。这里,除了出版者既然把书印成,就不能积压,得尽快推销之外,还涉及我们的传统及社会风气。尤其一九四九年后,一个人只要政治上未倒,就只许夸,不许贬;正如谁要是政治上有了辫子,就只许贬而不许夸。
没有点容忍和雅量,书评是很难扎根的。没有明真伪、辨是非的书评,好书得不到褒奖,坏书乏人指摘,那就像是足球场上没有了裁判。球还是在踢着,甚至十分勇猛热烈,可就难免乱成一团。食品需要经过鉴定,精神食粮也应允许品评。书评可以使好书更畅销,坏书受到淘汰。它应是读者的顾问,出版者的御史;是好书的宣传员,坏书的闸门。对于出版工作,它应起到筛子、镜子和轮子的作用。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收入《玉渊潭漫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