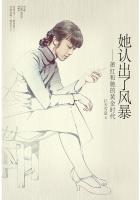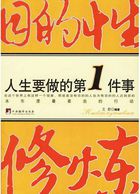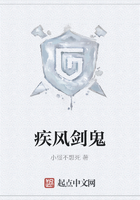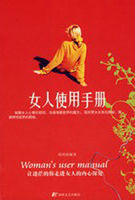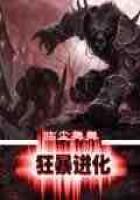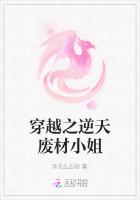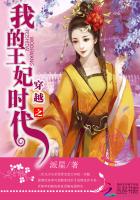我的学校坐落在海河的旁边,原址是清末建筑的李公祠,这是专门为纪念李鸿章而修建的。再往南走就是原北洋总理衙门的所在地。顺着金刚桥向南行,从海河旁边向右拐进去,再向左就进入了我们学校的范围。红色的大门中式的屋顶,学校是一个三进的大庭院,第一进是一圈儿平房,我入学的时候已经被用作学校的办公区,二进门就高一些,是一个大操场,径直是一座大殿,有汉白玉的一圈回廊围绕,估计这里即是祠堂的正堂,但那时回廊里有了单双杠,大殿里已经成了放置体育器材的地方,最后面是一座新建的教学大楼。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天津市三十三中学。我是一九六五年考入这里学习的。
那时候中学的教学单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学校是按照学科分办公室的,而现在是按照年级分办公室的,我私下以为还是那个时候要好得多,因为学生压力小,教师共同语言也多,绝不像现在完全是为了考试这么势利和现实。老师们都是一些和蔼可亲的人,也是最令学生难忘的。
算起来其中最有名的人就是温刚老师,他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父亲。不过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是一点儿也没想到。温老师正如他的姓,温文尔雅、温厚待人、温良恭俭;好像每天总是提着一个蓝布的书包,笑眯眯地走路来学校。然后就是走进教学楼三楼,坐在史地组一个靠里面的办公桌边。也许是他性格内向,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他除了上课之外的走动。我的班主任是史地组的组长侯晋武老师,我是地理课的课代表,所以有时间经常进出史地教研组,不是给老师送作业就是找侯老师问事情。所以就经常看到温老师,我见了他也从没有感到过紧张,因为他总是很谦和的样子友善地微笑。温刚老师没有亲自教过我们班,但他是那个教学组最老的一位教师。
那时的侯晋武老师可能是刚刚来到学校不久,身体魁梧脸庞宽大,一副很结实的身体;由于他是络腮胡子我始终也没有觉得他年轻过,这样的老师大概能够压得住茬,所以他能够管得住学生。侯老师讲课声音很洪亮,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句实在的,我虽然是天津人,但那时在学校里从来也没有听哪位老师说过天津话,就是在课下也从来没听到过,估计那时也许是国家有要求也说不定。侯老师的地理课讲得有声有色,很多时候不是有挂图就是带着地球仪和标本,我们在图表和高昂的声音中,想象着跟侯老师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
数学组负责教我们班的是李铎老师,他是个很清癯的人,既严肃又精神,数学课讲得极好,言简意赅是他的特点。从来不苟言笑,却是幽默有余。记得有一次有位姓梁的同学上课不注意听讲,李老师停下课来慢慢地说:“梁君,你干什么了?要抓紧时间学啊!”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那位同学的脸马上就红了。此后我们都喊这位同学叫“梁君”,现在也许记不清他的全名了,但是说起“梁君”我想全班同学都会是记忆犹新的。据说李铎老师那时是什么“摘帽右派”,但是他不管这些,只是认认真真教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落实了政策到另外的中学当校长去了。
教英语的老师叫殷虎,是上海人,他的鼻子稍大一点儿,教英语正合适。他一走进课堂就用英语说:“你们好吗,我的孩子!”于是我们就大声整齐地说:“老师好!”他一口好听的上海英语,经常用板擦敲着黑板上的单词领我们大声朗读。一次学校里不知怎么来了一个外国旅游者,于是殷老师派上了用场,他和那个老外叽里咕噜地说了很多;原来那人是个旅游者,他误把我们学校当成了附近的大悲院,殷老师经过解释终于把老外打发了。于是,从来也没有见过外国人的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语文教研组是一个比较大的办公室,是不是最大的教学组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学起就喜欢语文,因此这里是我很神往的地方。那时的老师有叶理行、张淑敏、钱克文等,他们都满腹经纶,书生意气、文质彬彬,我总是有事没事往这边跑。给我们班上课的是钱克文先生,他是一个年轻的老夫子,平时说话引经据典、才华横溢,他的最大特点是课文讲完还有时间就给我们讲故事,因此听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想下课。他的古文课讲得很是生动,对要求我们背诵的课文,第二天检查时总是一丝不苟,谁要是背诵不下来只有站着听课的份儿了。记得那时我总是想好好表现,以引起他的重视,无奈我天生愚钝,自己感觉总是有所欠缺,远不及班上的刘聚臣、孙炳如两位同学。不过我现在还能完整背诵《孟子·告子上》中的《学弈》篇及一些古文,这都是那时晚睡早起强记恶补打下的基础。据我所知,语文组的老师们都是能作古诗词的,他们常常相互切磋,彼此唱和。这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那时以为古诗是只有古人才做得出来的,今人也只有毛泽东才行,因此就对他们充满了神秘感和敬佩。
那时的学生和现在的中学生差不多,就是总想到老师家里去。侯老师、钱老师的家我都曾去过,记得还在他们那里吃过饭,但是自己从来没有给他们买过任何东西,这是那个年代的风气和经济条件使然。现在想来觉得那时的自己真是不懂事,因此就很想报答他们。
侯老师的妻子当时也是老师,是个非常干练的人,对我们很爱护很关切。钱老师的夫人据说是他同学的妹妹,这里也许有一段天赐良缘的浪漫故事,可惜当时的我根本就不敢去问。在钱老师的家里比较随便,他还是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是古代的有时是外国的,记忆最深的是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听了还想再听,但是晚上回家的时候路上很害怕,现在想来觉得那时的学生真的很幸福,成长的经历是全方位的,精神是很充实的。
老师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平平凡凡、求真求实、兢兢业业、默默奉献。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最早是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这儿来煽风点火,他们身穿绿色军服,腰扎烟色塑料皮带,满口的京腔普通话还是很吸引人的。记不得是怎样开始批斗老师的了,不知怎的,叶理行、李铎、钱克文等一批老师就被关进了一排平房,即所谓“牛棚”。我们都是很同情的,真是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实际上却是什么也做不了。
再后来我们就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从一九六八年的年底到一九六九年的年初,我们班的同学先后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哈尔滨郊区,后来学校派侯晋武老师到插队的地方回访我们,见面的那种激动真是难以言表的,他要离开的时候许多人都哭了,那时才感觉到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走后我们也慢慢长大了,从此就完全独立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也都迈入了老年的行列,值得欣慰的是侯老师、钱老师都很健康,每到春节前后我们几个同学都要邀老师出来聚聚。有说不完的话,从他们那里吸取力量,就像游子回家见到久别的家长那样。
附记:
这篇文章写好(二○○九年)之后,计划分别寄给远在哈尔滨的聚臣和天津的侯、钱二师。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就传来了侯老师去世的噩耗。震惊之余是无尽的怀念,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同学王勇、许文胜、王大强、李天仁、张磊、孙炳如和我七人一起到侯老师家里去吊唁,我们在侯老师的遗像前流下了眼泪,默默地盼望他在去天国的途上一路走好,还在花圈的缎带上恭请钱老师率我们献上了集体的悼念和哀思。
张铁荣,天津市人,一九五一年十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师承李何林先生专修鲁迅研究,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四年赴日本讲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二十世纪文学教研室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中华史料学会理事,天津市现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