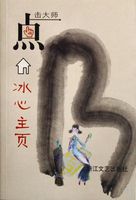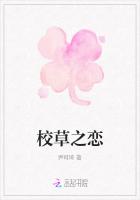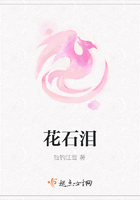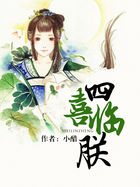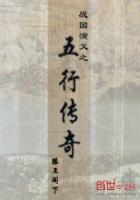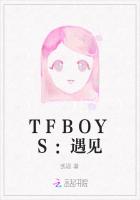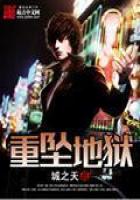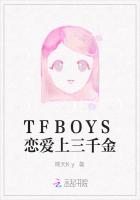一九七○年,我十三岁。入保山一中念初中,编入三连四排,随即任排长。班主任是体育老师,文化不高,整人的本事却很大。一年以后,我受其诬陷,血战经年,身心饱受摧残。导致第一次对人性的幻灭。
十月,奉命往保山军分区教导队参加“三防”(防核弹、防化学武器、防细菌战)训练班,为期半月。某日,训练归来,被紧急召往饭厅,全体人员受到时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接见。这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的官,不禁热血沸腾,一双巴掌拍得通红。
一九七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风行“学工、学农、学军”,每年有半数时间用在“三学”上。农忙,必到农村“支农”。学工是在校办工厂完成的,有时也到工厂去。初中时,到过保山总站。印象中,我学的是钳工。高中时,甚至学过打铁。这一点学工经历,如非写作年谱,早已“事如春梦了无痕”了。
学军时每年一次拉练,每次半个月,均发生在初中阶段。第一次拉练,路线是保山—辛街—昌宁卡斯凹—湾甸—姚关—施甸—蒲缥—保山。行前,我受命组建三连文艺宣传队,任队长。出发时,竟无辅导员(老师)配属。我只好带领这支从六个排抽出来的,由三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踏上征途。白天,沿途做鼓动,一副竹板,打得娴熟,还编了不少顺口溜。晚上,为驻地群众演出,自己也粉墨登场,扮几个无关大局跑龙套的角色。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由卡斯凹到湾甸的经历:清晨出卡斯凹,行行重行行,前面是爬不完的山,涉不尽的河。走到下午,队伍已呈鸟兽散,哩哩啦啦,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停下来做饭已经不可能,肚子饿得咕咕叫,生米、生蚕豆,也一把一把塞进嘴里。极度困乏,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走到日落月出,天边的晚霞与傣族群众烧甘蔗地的野火相映成趣。我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晒场上有一堆将灭未灭的篝火,四围不见人影。我打开铺盖卷,一头躺下,沉沉睡去。睡意浓时,有人在摇我。艰难地睁开双眼,是连指导员(老师)。
指导员帮着我,搬进了近在咫尺的小学教室。第二天清早,我才想起去寻找我的“部下”。“部下”就在同一个晒场,紧靠南墙的芭蕉林里,男男女女,仍在枕着露水酣睡。他们是在我到后不久,陆续抵达的,也和我一样,困不择地,当即躺倒了。
普及中草药运动在此时兴起。腾冲当时有“红医县”的称谓。星期天,我便带领采药小组上山采药。从易乐池左侧,沿一条峡谷进山。采到过重楼、茯苓、党参等,回来都交给了学校医务室。采药小组的成员,有张丽丽、樊勇等。樊勇,出身军人家庭,学习极差,初中时生活仍不能自理。然而他懂药,差不多所有草药他都认识。所以,每次进山我都带上他。这样的行动,有过多次。
这年晚些时候,我带领一支十余人的小分队,在一位管后勤的老师率领下,到离城区数十里的高山——碗水梁子去烧石灰。山,砍光了几架;石灰,却未见烧出。住地是保山地委为战备建的避难所,万山丛中,危崖耸立。有一支空军部队驻在山上,不时来和小分队联欢。
归来不及一月,风云突变。班主任为推卸责任,对我横加诬陷,痛加打击,全校批判,从此陷入黑暗的深渊。虽经血战,突出重围,但身心已遭重创——幸未扭曲。这年我十四岁。
事情的起因,是头年到太保山学农基地劳动时,奉校方之命,挖坟造楼。
保山,古称永昌、不韦,历史悠久。秦相吕不韦犯罪,后代流放到保山,县以不韦名。三国时,吕凯独立南滇,力抗地方豪族,深为诸葛亮所赞许。因而,古墓甚多。
“文革”“左”风猖獗,保山一中欲建新校舍,砖瓦不从砖瓦厂购,却派出千余学生,上山挖墓取砖。挖人祖坟,是中华民族的大忌。后来我说过:我的倒霉,是罪有应得,因为大悖人性。而在当年,却以“革命”的名义,以“排长”的身份,干得太欢。
话说某日下午,天高云淡,烈日炎炎,在挖过一座大型砖墓之后,发现了一个小洞。循小洞掘进,有一块小小的石碑,碑上大书“当方土地”四个字。翻捡泥污的土地,捡到一圈形如手镯、铜迹斑驳的什物——这就是惹祸的根苗了!我当时刚读过童恩正的考古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为显示知识渊博,一边挖,一边大谈考古。其实是哗众取宠,啥也不懂。
东西挖出来,用一张白纸包好,交给小组长保存,我便忘却了。随后几天,为些琐事,大闹情绪,甩手不干。又在班主任宿舍里见到了这个白纸包(这是解谜的关键。一年之后,班主任收拾我时,又出示了这个白纸包,但是说里面包的是麦冬,而非手镯。然而,白纸包的存在总是事实,而且到了班主任手中),以为小组长已上交。事后更懵懵然,不知祸之将至也。
事情的诱因,则是四连某排也挖到了一只手镯,而被班主任出售后喝了老酒。学校出面追究。体育老师大窘之余,精心策划之后,突然向我发难。这是一场极不平等的决斗:班主任对班里的学生;五十多岁老谋深算的成年人对一个初涉人世十四岁的少年。居高临下,结局可想而知。
这之后是日日批判,天天斗争。每天早上的“天天读”时间,体育老师必来攻我。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撕下×××画皮”等字样的檄文。排里的批斗会,每周必有。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况味。我在最初的愕然之后,以稚嫩之躯,力抗强权,也写了“致军宣队长的公开信”“给清六办的控诉信”等一系列辩诬文章。
一九七二年,一年血杀,迎来了初中毕业。学校给我“记过”处分,处分却找不到我任何“贪污”的证据,仅以“态度恶劣”定罪。为抗议故,我拒考高中。后为父亲干预,转往腾冲一中念高中。离开保山时,学校尚未举行毕业典礼。我径往班主任宅,要求提前发放毕业证书,且坐守不去。这位四肢发达的江浙汉子,无奈之际,只好把毕业证书给了我。
八月,孤身一人重返腾冲。此时,在排里,我保有几个“死党”,如刘峰吉、郑留发等。走时,是排里两个女同学送我上车的。
到达腾冲后,插班进入腾冲一中高34班,班主任刘云鹏。铩羽归来,却有了意外的收获:比小学同学高了一级。这意外后来证明并非好事,多下了一年乡。
从急风暴雨中走来,回归故里,心情是黯淡的。故乡美丽的山水给我以慰藉,故乡浓郁的文化氛围给我以鼓励。我在故乡复苏,我在故乡重新崛起。
我的住处在腾冲一中三大楼,地处来凤山麓,前有密林,后有荒坟。夜晚,常有异音来扰。
我对语文的爱好,得到了长足发展,遇到了几位对我一生影响巨大的好语文老师:杨学湘、赵槐生、董云林、冉子玉……杨老师是我的科任老师,由于偏爱,他指定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不久,学校成立文学小组,他又指定我担任小组长。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作家,除我以外,还有岳丁(武和兴)、杨必传等人。杨老师对我的关怀,不仅在学习上,也在生活上。那时,他有两片肉吃,也一定要分给我一片。师生间的亲密情感,与专门置学生于死地的初中班主任,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对鲁迅的阅读,也始于此时。先是《鲁迅杂文书信选》,后来买到了全套的鲁迅著作单行本。初读,不懂。渐读渐懂,体会甚深。对我人格的确立,起了关健性作用。至今,我已拥有三套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仍在学习和阅读中。
一九七三年,发表处女作、独幕话剧《又迟到了》。署名是“腾冲一中高34班文学创作小组”。
学校组织会演,要求各班自创节目。我尝试写了小话剧《又迟到了》,先被搬上舞台,又被《腾冲文艺》(油印刊)刊出。修改后,更名《批判会之前》,参加了保山地区调演。这个小剧的主题是“学雷锋”,塑造了几个性格还算鲜明的人物。三十年后,我加“附记”,将其收入《飞海寨》一书,以资纪念。
由剧本创作,认识了县文化馆张天翔老师。随后几年,创作上我得到过他的大力支持,虽然成就不大。十一月,省里在腾冲办文学改稿班,我追随张学文叔叔(名曲《美丽富饶的潞江坝》的作者)之后,出入于会场。等候父亲的老朋友杨苏伯伯不至,却在腾冲一中小花厅见到了来访的李钧龙、辛勤诸同志。这是我结识的第一批作家。三十年后,钧龙同志给我来信,对这次见面,仍记忆犹新。人们对我说:“坚持十年,必有成就。”我坚持了,直到现在。
也是因为剧本创作,我被抽到学校宣传队。先做演员,不成。后来专司创作,兼管服装和拉幕布。在学校宣传队,我把自己写的剧本演回了保山一中。那位专制的剧中人,影射的是蛮横的体育老师。心中大感快意。
岁末,县里安排我到边境一线“体验生活”。同行者是县革委一位常委和学校一位李姓老师。杨常委带了一支手枪。这次边境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古永起程,进入傈僳族聚居的胆扎,在前哨排宿一晚。翌日,转道往猴桥。其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政治边防”还在肆虐,小村并大村。莽莽山林,走一天路,不见一处人烟。松涛轰响,林荫蔽日,羊肠小道,曲曲弯弯,竟不知在境内,还是境外。走至下午,逮住一条傈僳汉子,杨常委认识他,说是专门贩私货的。所谓“认识”,是关过、审过他。逼他带路,他一脸媚笑,点头连连。但我不放心,杨常委也不放心,只好枪上膛,用武力胁迫。一路忐忐忑忑,走到日落时分,终于抵达傈僳大寨。又走了一天,到达了战火未熄的猴桥。藤桥悠悠,江水澹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颗久悬的心,才算落到了实处。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原本就不正常的教学,重新陷入困境。三四月间,某高中学生在班主任鼓动下,集体向县革委写信,要求提前下乡,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于此时,退出学校宣传队,“纠集”四人:我、邵曰培、赵玉书、赵胜国,与某班展开大论战。这些文章,多数由我起草,邵及二赵誊抄成大字报贴出,坚决反对提前下乡。其中一份,题为“致县革委的公开信”,一直贴到县革委大门口。说是清醒,是超前,未必。口号叫得山响:多学知识,建设新农村。反对提前下乡,朦胧中,革命是假,想多读几天书是真。
四年中学(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终于在动乱中结束了。这年,我十八岁。我谢绝了父辈的安排,自作主张,前往德宏傣族地区插队落户,一去就是四年。
离开腾冲,是交通管理站黄伯伯为我找的军车。坐在高耸的车厢上,车开得飞快。过南天门时,“悠”地一腾,下瞰万丈深渊,这颗心,便很久、很久没有着落。
马旷源,回族,一九五六年二月生于云南腾冲县。高中毕业后在德宏州傣族聚居地遮放坝飞海寨插队落户四年,一九七八年考入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楚雄卫校、楚雄州委党校、楚雄师范学院。一九九七年任楚雄州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