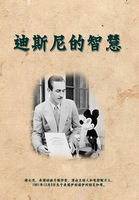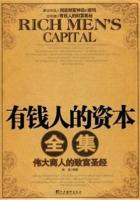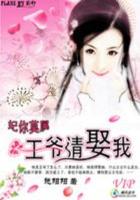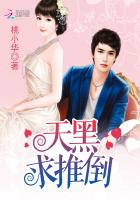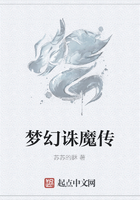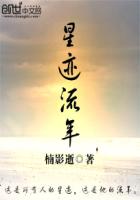快过春节了,家里包饺子,其乐融融。我和孩子们说起在部队包饺子的故事,他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于是,我有了写这篇文章的愿望。
一九六九年二月到一九七五年三月,我在山东当了六年兵。虽然艰苦,还是吃了不少次的饺子。现在想起来,包饺子也像是在包一个个的故事,储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我当兵进了济南军区防化团五连,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就是连队的伙食费亏空七百多元。对于伙食费一天四毛四分八的我们,七百多元简直是天文数字。
记得我父亲那时对我说:咱家存上五百块钱就行了,能应付突发事情了。而那时候他在原子弹生产基地工作,工资很高,每月有一百八十多元。
我们连队当时驻在长清县五峰山,每天饭前都要在食堂门口唱歌才能进门,当嘹亮的歌声在山间回荡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没有多少吃饭的兴奋,因为我们知道,早饭就是大米饭,西葫芦虾皮汤或是冬瓜虾皮汤,午饭就是馒头和有一点肉星的炒菜,晚上就是窝头稀饭和咸菜。
要用我们的嘴省出七百多元来,任务挺艰巨的。
说到吃,最高兴的莫过于吃饺子。
饺子不是经常吃的,逢年过节才有可能。而过节吃饺子还是吃饺子就是过节,其实已经分不大清了。
连队吃饺子是以班为单位,全连连同连部一共十个班,哪个班包得快就可以抢到第一锅下。因为都是非专业人士,又要抢速度,包的饺子质量大都不高,如果别的班抢到前面,后面的班也许就是在片儿汤锅里下饺子了。
包饺子是按照每人九两面发给面粉,配给适量的馅。这天,连队都是吃两顿饭,第一顿是煮饺子,第二顿大都是吃剩饺子。如果下的都是片儿汤,那第二顿就没了念想。
这像一个重大战役。
吃饺子前一天晚上,各班就都行动起来了,先要开一个战斗部署会,谁第一个去炊事班领面领馅,谁准备擀面杖和面板以及放饺子的容器,谁排队等着抢下第一锅饺子。第二天都要抢着到炊事班门口排队,领了面和馅,要一路小跑回到班里,用最快的速度包起来。
包饺子也有分工,主要是有饺子长,负责协调指挥的,饺子皮,负责擀皮的,还有饺子腿,负责跑前跑后,踅摸少了的物件,侦察敌情,就是周围各班的进展情况。
如果一个班能够协调好,再加上有技术能手,就有可能拔得头筹,得意洋洋地去煮第一锅饺子。这时,哪怕是有人在锅边排第一名,看到举着饺子托盘来的人,也要乖乖让开,眼巴巴地看着一锅滚开的清水,下上别人的饺子。
包饺子得到第一名,那个兴奋劲,不亚于在全连大会上受到了连首长的表扬。
说来惭愧,饺子皮是技术活,我干不了,只能当饺子长,动动嘴。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班似乎没得过几次第一名,吃了不少别人的片儿汤。
有时候,部队在野营拉练中过节,包饺子的条件更加艰苦,尤其是没有擀面棍,没有放饺子的容器,有时候甚至没有下饺子的锅。记得一次拉练在莱芜的一个村里,正好赶上除夕,各班领了面和馅包饺子,擀面棍倒是事先藏了一根,包好的饺子放在哪儿?防化兵是机械化部队,有车,车上有训练用的金属托盘,就包好一盘放在外面冻上一盘。那时候似乎比现在冷,饺子很快就冻成了冰坨,把托盘拿回来再放上一盘饺子冻在外面。
第二天煮饺子,没有锅,就用洗脸盆,几块砖垫起来,放点柴火烧水煮饺子。不过,说洗脸盆有点客气,其实当兵的就一个盆,洗脸洗脚都是它。
那天,排长巡视到了我们班,看到热气腾腾的饺子,高兴地抓起一个就丢进嘴里,一边问,用什么煮的?我指了指熏黑的脸盆:就是它。排长是个爱干净的人,哇的一下把已经嚼烂的饺子吐了出来。
我告诉他,其实,已经高温消毒过了啊!
现在,吃顿饺子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那句话,叫: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早已被当作一句名不副实的话了。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是,现在的饺子,没有了军营里饺子的味道。
军营的饺子,里面包着故事。
码字生涯
我的四位老师
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故事
那时洛阳纸贵
纪录片《邓小平》前前后后
照片中的深情
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出版画册
走近王震将军
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在这个机关十六年,我等于上了十六年的学,算是把我以前落下的学业补回来了。很多人问我,在这个机构里你学到了什么?我都是这样回答:严谨、积极、内敛和宽容,当然还有文化程度的提高,都是在这里得到的。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我曾经平淡过,曾经得意过,曾经失落过,也曾经痛苦过,但是,相比我得到的东西,那些失落和痛苦根本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