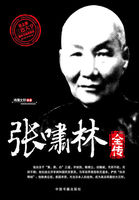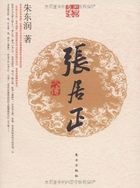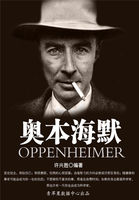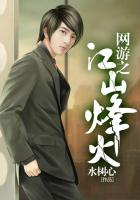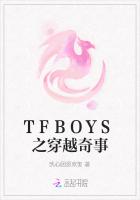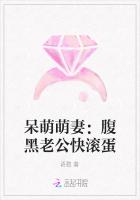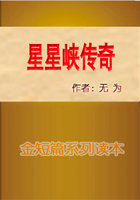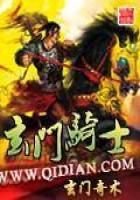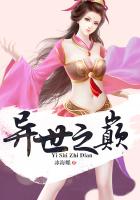明天,就是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了。
有机构约我写写邓小平,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说史实,中央文献研究室,我的老东家,有许多专业人士,在这块地里深耕细作,不会留下什么空间。说观点,众多的专家学者也没有留下任何角落。但是,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伟人,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上,我似乎也应当做些什么。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的十年里,我参与了不少与小平有关的文字和影视工作,例如,参与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出版,做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做十二集电视片《邓小平》的制片人,做邓林的《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摄影画册的编辑及展览策划等等。其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当然,也许有些还不能说,都写出来也太长,所以,我先写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故事。
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我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刘少奇研究组一呆就是七年,开始是编辑《刘少奇选集》,之后是撰写《刘少奇年谱》。作为一个初入门者,这七年等于是在上学。
一九八七年四月,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文献出版社。记得批复的日期是四月十五日,签字批准的是邓力群,他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也分管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室抽调了秘书处的一位老处长李庚奇来筹办出版社,他是中央办公厅的老人,在周总理办公室长期工作,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他不知搭上了哪根神经,从文献研究室的近两百号人里,挑了我来帮他。
我那年三十五岁,现在看,三十五岁已经是老朽了,但是当时我还是懵懂青年,处在混沌状态,不知道自己能够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李庚奇找到我,没有做什么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就上了他的船了。不少熟人劝我不要去,认为是件前途未卜的事情,但是我却决心已定。
回头想也不意外,因为自己在刘少奇研究组做得有些倦了,希望换一个环境。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还是会老老实实在刘组呆着的。因为我曾经动过心去农村政策研究室,我认为那里更是改革的一线,不像文献研究室,是个故纸堆。我的组长姚力文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和农研室的杜润生、吴象等都熟,我希望他能够推荐我去,但是,被他轻描淡写地拒绝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条船,当时还很不像样。
国家给了二十万元的开办费,在文献研究室院里的角落里找了几间房子,这条船起锚了。我和李庚奇招了几个人,第一年好像是八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做过出版。就是像那句话说的,只看过猪跑,没吃过猪肉。
不过,蹒跚上路也是上路。
出的第一本书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小册子,总共只有两个印张,但是开机就印了一百多万册,这本书赚了二十多万块钱,算是初战告捷吧。
而第一本有影响的奠定了出版社经济基础的是大型画册《邓小平》。
其实,这本画册在出版社没有成立时就开始编辑了,主要功臣是杨绍明。绍明是杨尚昆的公子,一九四二年出生的他当时只有四十五岁,他刚刚从新华社摄影部调到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研究组工作。那时的杨绍明,还有着青春活力,组里有同事搬家,我看他卖力地往五楼上扛家具,真的感动了好一会。当时邓组的组长汪作玲以及邓组的周立平、冷溶、龙平平等,都为这本画册出了不少力。
杨绍明因为和邓家关系密切,出入邓家如履平地,所以拍了许多邓小平的照片,编邓小平画册时,他提供的照片大都是非常生动的居家照片。后来跟他熟了,我开玩笑说,你的照片好不说明技术好,第一是你的相机好,第二是你有机会,第三是你洗照片不要钱。
一次他说,到小平家去,老爷子正在看报,脚丫光着放在凳子上。绍明取出相机,说老爷子照一张,小平说,那我得穿上袜子去,绍明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就这样好。于是留下了一个生动瞬间。
还有一次,他拍下了一张小平正在读书的照片,地点好像是北戴河。很多人知道这张照片,都说小平同志在认真学习。我问过绍明,老爷子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古龙的武打小说。
很多照片很珍贵,有些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有些则展示了邓小平的家居生活。为了确保印刷质量,这本画册是在香港的凸版印刷制作的。邓小平在晚年时,曾经深情表示,希望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在十年前,他的许多照片就到了香港。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制作等手段,只能是用原图扫描,修版后再制版,随时要和原图比对,所以,这些照片的原版都运到了香港。很多是极珍贵的照片,工厂为了保证安全,特地在车间里焊了一个硕大的铁笼子,每天收工时,把照片都锁在这个铁笼子里。当然,工人们也都非常重视这本画册的制作。
一九八八年,杨绍明特意带我到香港看画册的印刷。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也算是第一次到境外,还领到了五百元置装费,到北京的红都做了一套西服。记得穿上这套西服到香港,杨绍明带我去光大,王光英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别看你穿了一套西服,一看你就是共产党的干部。
这本画册,是邓小平生前看过的唯一一本《邓小平画册》,这是毛毛拿着给他看的,我也见到他在这本画册上的签名,字体还是遒劲有力的。那时,他八十三岁。
画册非常精致,照片也非常精彩。但是,怎么把画册卖出去还能收回钱来呢?
一本大八开铜版纸画册,三百多个页码,要卖多少钱呢?当时,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亲自兼任出版社社长,一个正部级兼任一个正局级,也算是奇观。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怪。李琦可不是挂名的,为了定价,他和我们或者在机关开会,或者到人民出版社取经,用了整整九个半天。最后的定价是,平装本四十五元,精装本五十八元。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定价了,可是,和成本相比,又很便宜,因为这本画册的成本也很高。
当然,主要原因是这本画册是由一个港商赞助印制的,我们不太考虑成本,所以拍脑瓜印了七万册。但是新华书店系统征订情况很不理想,我现在记得的数字是沈阳市新华书店第一批报数是六本。
当时犯愁啊,又是不断地开会想办法。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杨尚昆,他老人家当时不但管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而且主持军队工作。他说,不要急,我可以让军队腾仓库给你们。
可是,光有地方放也不行,还是要有人买才行。
我们分析,不是没人买,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图书发行的体制是只允许新华书店系统一家垄断发行,而由于种种因素,人找不到书和书找不到人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就出了一个怪招,就是找各省的省委办公厅系统帮助征订。现在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似乎有摊派和权力寻租的嫌疑。那时看,也是不对的,是没有遵守国家有关图书发行的规定。所以,新闻出版署的刘杲副署长后来曾经专门召见我,严肃批评中央文献出版社。不过,这时候我们的画册全卖完了,甚至还加印了两批。
这就是那个怪招的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没有腿的单位,不像中组部、中宣部甚至党史研究室,一直到县都有相应的单位,而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于是我们只能找各个省委的办公厅系统。当时我算是出版社领导层里最年轻的,正好是冬天,我自告奋勇,说,我去最冷的地方吧,就去了东三省。我那时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副主任也是刚刚提拔不久,因为我一直算是研究人员,没有行政职务。不过,临出发前,李琦同志找到我,说,你这次出去,为了方便工作,就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回来再办正式手续。我有点发愣,从一般干部,到副处、正处,好像只用了一年时间,是不是太快了?
不过,还是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做好了挨冻的准备,穿了一件海军的蓝色人字呢大衣,里面满是羊毛的那种,省委的同志又不认识我,所以从辽宁到吉林,从吉林到黑龙江传递的信息都是,接一个穿皮大衣的人,似乎成了接头暗号。
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我去的东三省一共卖出了七万册邓小平画册,也就是说,第一批印刷的画册都卖光了,就在这三个省。
当然,我喝了太多的酒!
从此后,我有了一大批的东北朋友,友谊延续到了现在。几年前,我和太太去参加亚布力论坛,回来时到哈尔滨绕了一下,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前后六任处长都出来请我吃饭,郑兴汉、王普庆、王润增、张伟、于佩常、刘善琦等等,我太熟悉的名字此刻都到了我的脑子里。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是很大的领导了,见面还是亲的不行,似乎从来没分开过。太太悄悄问我,他们怎么都对你这么好?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不能一下子答上来。
广东也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画册在香港印制,广州成了画册发运的集散地。在广州军区支持下,我带了几个人,在三寓宾馆住了二十多天,往各地发运画册,省委办公厅的李万国、朱固志、曾小仕等忙前忙后地帮助我们。闲下来就骑个自行车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转,那一段时间,把广州的路算是认熟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听说深圳在建设特区,热闹得很,我们应当抽空去看看。怎么去呢?也是想了一个怪招,给深圳市委打电话,说我们印了一本邓小平画册,想给李灏同志送去看看。李灏是那时的市委书记,其实他也是我中学同学李绗的父亲。结果深圳方面回话很欢迎。于是我们乘火车到了深圳,市接待办副主任张国英和接待员李广建亲自到车站接我们。那时的深圳火车站,似乎还是一个工地,整个深圳,也是一个工地。现在我常常到深圳,看到今天的高楼林立,繁荣发达,总是想起一九八八年底的深圳。
时间流走了,城市变样了,我和张国英的友谊,却延续到了现在。
几次加印,《邓小平画册》一共印刷了十二万册,也给中央文献出版社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杨绍明力主把港商资助的经费还了回去,还在香港买了一辆三十座的考斯特,一辆丰田面包车,草创阶段的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下子鸟枪换炮了。
遗憾的是,我手头现在一本邓小平画册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