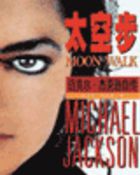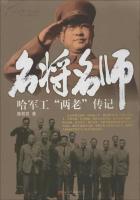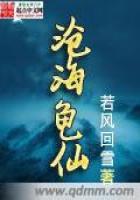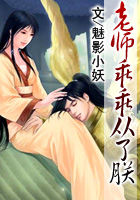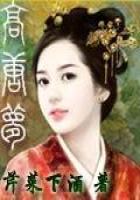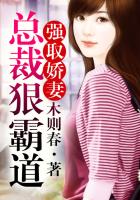一九九六年,我离开了工作了十六年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加盟凤凰卫视。
在凤凰卫视,我做的第一个活儿,是组织飞跃黄河。这是台湾艺人柯受良当年在香港回归前的一次壮举。从这时开始,我全部精力都投在初期的凤凰卫视。
说实在的,我再也没想过,今生还会和出版有关邓小平的图书搭上关系,因为,毕竟离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成了一个电视人。
可是,邓小平逝世后,他的长女邓林要出版一本摄影画册,找到了凤凰卫视,希望得到凤凰卫视的帮助。这个活儿,似乎很自然地归了我。道理很简单,我搞过出版,我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了解邓小平。
邓林是邓家的“政协主席”,这是开玩笑,邓家几个孩子里,如果说邓榕是“外交部长”,因为她擅于对外交往,那邓林的特点就是低调,不太过问政治,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有点像民主党派。
邓林出生在战争年代,小时候在幼儿园没有得到很好照料而得了重病,留下了后遗症,上学时不能集中精力,所以,她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时,常常趴在桌子上睡觉,于是就改行学了绘画。会画画的邓林自然也爱摄影,于是,给父亲拍了很多照片。
邓林爱摄影,我也跟着沾过光。记得我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就是邓林在香港买了送给我的,那时还是稀罕物件,只有区区二百万像素,而且很少有配套的软件,哪像现在,胶卷照相机早就被打败了。
这算是分了一个岔。
邓林为了编这本画册,特别找了她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的同学陈莲来帮她。陈莲大姐已经退休了,几乎是全部精力来做这件事情。她是个非常热心也是非常细心的人,细心到了有时候我觉得是多此一举的地步。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灯市口的皇冠假日,这儿的老板也是邓林的朋友,借了房子给我们用,一大堆照片摆在两张单人床上,我们就在这照片的宝库里逡巡。
这本画册编辑不是那么复杂,无非就是挑照片。而且,因为是从女儿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家居生活的照片为主,当然这也是一般老百姓最喜欢看的。我们的工作,是协助邓林选照片,再就是写图说,帮助邓林完成一篇怀念文章。这本画册的装帧设计我请了吕敬人先生,他是非常著名的书籍装帧专家,也是我很多年的合作者。
画册的编辑进展很顺利,很快,一本厚厚的由白色牛油纸作外封的一本精美画册就问世了。影响当然不能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相比,但是,因为是女儿的视角,多了许多亲情。这本画册很受欢迎,成了许多人的珍藏。
从这些照片,到那篇让人动容的文章,都凝聚着邓林大姐的心血和深情。
真正费了些功夫的是画册出版以后的图片展览。
展览的名字与画册相同,第一场展览选在了北京,在邓公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地点在军事博物馆。因为是第一次办这个展览,没有什么经验,还是费了一些周折。
首先是资金问题,时间很紧,不知道能不能拉到赞助,但是,一周年这个时间点又不能错过,当时,凤凰卫视决定以神州电视有限公司的名义来主办这次展览,也做好了没有赞助就自己全部承担的准备。作为我这个直接负责人来说,这当然不算光彩,因为毕竟凤凰卫视也是刚刚创办不久,资金也很紧张。不过,吉人天相,展览开幕前两天,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联通决定赞助三十万元,让我松了一口气。主要的推动者是中国联通市场部的李戈美,她是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孙女,这样一种身份,当然她懂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赞助,而是表达对邓公的崇敬。
开幕这天,来了很多人。记得当时邓公生前的保健护士也来了,站在有她的一张照片前很久。居然还被认出来了,许多人围着她,希望听她讲故事,久久不肯离去。
邓家三个姐妹都来了,毛毛的婆婆也来了。我早就听说过老太太,知道是口碑极佳的人。在贵宾室里,毛毛特意向老太太介绍我,说,这是周志兴,咱家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帮着做的。
有了这句话,我所有的辛苦和难处,都一风吹走了。
这个展览,后来去过很多地方。除了北京以外,上海、深圳、成都、南京、银川、福州、海口、香港、澳门等城市都去了。
印象深的有这样几个地方。
香港是印象深刻的地方,但展览期间其实我没有去。我到香港做的准备工作。陈莲大姐介绍了一个香港的公关公司,现在我还记得负责的小姐叫刘懿伦,我和他们开了好几轮会,把时间敲定在“七一”,香港回归纪念日,地点定在香港会展中心。我也去看了场地,并且订好了六月三十日陪邓林到香港的机票。
结果出事了。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公司同事一起到首都体育馆的篮球馆打球,正好碰上了北京电视台的一批年轻人,就说打个比赛吧!结果没有多久,我就觉得有人在后面踢了我的脚跟一下,结果是跟腱断了。于是马上到医院,动了手术,打了石膏,躺倒在病床上。但是,香港展览在即,我是实际的操作者,我不在怎么办?邓林和陈莲两位大姐都十分体谅我,他们说,不着急,你就电话遥控吧!其实也说不上遥控,正好香港有对接的公关公司,前期准备都做好了,而陈莲大姐也是十分能干的人,所以,没出什么纰漏。只是我,退了机票,在医院躺了很多天。出院的时候,邓林大姐还专门给我送来了一个轮椅。
光是躺着也不行啊,还有很多事情。展览接下来要去上海,这是重要一站。
上海是个办事认真的地方。记得还在这个展览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时候,上海市委外宣办的主任焦杨和处长王建军专程到北京,商量这个展览到上海的事情。很多地方的承办者是大而化之地拍胸脯,真做起来往往不尽人意,而上海这两位干练女性,和我沟通的时间很长,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还签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合同。弄得我有点心里起急,觉得怎么这么啰嗦!
展览是定在了七月份,具体日子不记得了,记得我的腿上还打着绷带,是拄着拐到的上海。在上海,安排我们参观上海大剧院,正门口的台阶很高很高,我拄着拐望而生畏。这时,听到接待的上海方面有人冒出这么一句:看,邓朴方那儿还派了一个人来!快领他到后面坐电梯上去。
原来我不知不觉加入了残疾人协会。
在上海的展览非常成功,或者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当时上海的领导人黄菊、徐匡迪等都参加了开幕式的展览,参观的人也非常多,气氛热烈。这时候我想到了当初和焦杨、王建军两位领导的谈判,又一次印证了这个说法:和上海人谈判很费时间,但是,上海人执行合同最认真。
展览到了深圳的时候,安排在关山月美术馆。当时深圳文化局的副局长董小明是邓林的大学同学,也是学美术的,有了内线,事情就简单很多。印象深刻的是开幕那天闭馆后,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来看展览,没有几个人随从,他很认真地一张一张照片看过去,还不时问邓林某一张照片的内容。看过展览后,张书记请邓林和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后来他主政山东,又到了天津,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每当看到他的名字,我总是想到关山月美术馆的一幕。
在我的经历中,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做了一些事情,回过头来想想,也许遇到过一些困难,也努力过,但是我得到的远远多于付出的。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邓公的历史,通过了解一位伟人,懂得一段中国现代历史,同时,也懂得中国过去道路的曲折和将来的坎坷。当然,也知道了自己的脚步将如何迈出。
我将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