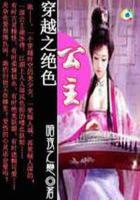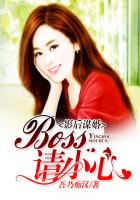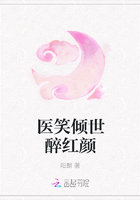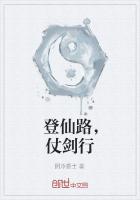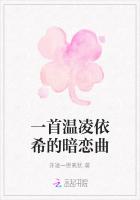一九九二年,李琦同志找我,说,王震亲自打电话来,说希望出一本自己的画册,而且说了这样的话:我知道不够格在中央文献出版画册,但是,我还是希望在你们这里出。
当时,王震此说是有缘由的,因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任务是研究中央常委以上的重要领导的生平和思想。但李琦告诉我,他马上一口答应了。王胡子,不是一般人,尤其在粉碎“四人帮”和之后的改革开放中,他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他的事情,不能怠慢。
于是,我亲自接了这个活儿。
王震家住在西单的翠花湾胡同,这个地方,后来成了我到的比较多的地方。
关于王震,有很多传说和故事。有些是正面的,例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带领三五九旅在延安南泥湾搞大生产,执行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指示,一曲《南泥湾》,郭兰英唱起“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把王震的故事唱遍了中国,也唱到了现在。后来,抗战胜利前的“南下北返”,新中国成立后的治理新疆,再后来,他指挥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带领部队屯垦戍边,创建了新疆、黑龙江和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当然也有一些是负面的,例如说他“左”,说他生活奢侈。
走近王震,发现奢侈的说法是子虚乌有,第一次到他家是夏天,老远就听见空调在叫,我后来常常对王震最疼爱的孙女京川说,你家的空调就是一个拖拉机在叫。我还到了王震的次子王军的卧室,这是中信集团的老板,卧室非常小,大概只有不到十平方米。
话题似乎扯得有点远。
这本画册编辑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尽管编辑部并不像其他画册一样都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组成,而是有王震将军的一些老部下参加,但是大家齐心合力,很快完成了编辑。
遗憾的是,王震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他的画册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王震逝世了。
王震逝世之后,中央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等等,因为这个评价,在编辑画册时还发生了争执。
王震的老秘书是李慎明,后来他做了社科院的副院长,他提出,要把中央给王震的评价加在画册的后记里。我也理解他,因为对首长的感情不一般。我在看电视王震骨灰回京时,李慎明哭得悲痛欲绝,印象极深。但是,王震夫人不同意,她的意见是,这是我们家人为纪念亲人做的画册,不是中央的文件,不要那些评价。按照王震夫人的话,她说,这些都不是老百姓的话。
但是李慎明还是坚持,他认为这是中央的盖棺定论,应当加上去。这时候,老太太还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她在里屋没有出来,由京川传递意见。京川再次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是老太太的亲笔,大意是:这本画册上不上中央的这些评价,是我的意思,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负责。
王震夫人王季青,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在我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
其实,老太太说到老百姓语言,我还是很能理解个中含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时,老人家因为某些话不中听,差点被打成右倾分子,是彭真保了她,那时,王季青还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她的终身愿望就是办一所好的学校。所以,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就担任了三五九旅家属学校的校长。王震知道王季青差点被打成右倾分子后怎么说?很爷们儿的一句话:不怕,大不了我们一起到北大荒种地去!
而王季青到那所中学区上班,从来不坐王震的车,就是像一个老百姓一样走着去,或者坐公交,直到有一次在路上出了点问题,才派车送她。
她从心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
画册的印刷过程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找了香港的中华商务来印制这本画册,因为我出版了不少大型画册了,有点掉以轻心,没有仔细和厂方交流,打样出来以后,发现很多问题,而且不是简单修改就可以解决的,最后只得推倒重来,换了一家印刷厂,就是当年印邓小平画册的香港凸版印刷,虽然多花了一点钱,但是保证了质量。
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在画册首发式上。当时的惯例,基本上每位开国领袖的画册出版后,都要开一个首发式,地点大都在钓鱼台国宾馆或者是人民大会堂,都是我来张罗。每次的规模大约一百五十人左右,都是按照规矩来,什么规格,主要体现在谁出席,谁发言,这么多的画册,都是照此办理。想不到王震的画册出版首发式出了意外。首先是到场人多了,那次是在钓鱼台开,会场里挤进了二百多人,大大超过了我们邀请的人数,再就是会场上有不少人举手要求发言,我印象深的有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他发言主要是感谢王震,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感受到了王震将军的关怀,当然,也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历史一定会记载这样的事例。在反右时,艾青、丁玲等著名文化人被打成右派,王胡子站出来说,这些人,别人不要我要,到兵团来。艾青和丁玲等人在兵团得到了在那时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照顾。姜昆自然知道这些。能够有这么多人自发地参加画册的首发式,主动要求讲话,就说明他们从心底佩服王震。
时间到了二〇〇六年,我早已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甚至已经离开了凤凰卫视,王京川突然找我,说,二〇〇八年是王震一百周年诞辰,家里希望拍一个六集的纪录片,希望我来帮助她。这个事情,我当然责无旁贷。于是,我推荐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制作单位,也推荐了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康健宁为总编导。我算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
摄制组搭建起来,撰稿、摄像、编导、剧务都到位了,王震的家人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三个儿子王兵、王军、王之,加上王震的老秘书、老部下,都积极参加座谈会,接受采访,请来的撰稿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拿出了初稿。没想到的是总编导康健宁非常不满意,认为这个稿子基本不能用。康健宁是中国纪录片最具声望的导演之一,他曾经任宁夏电视台副台长,但是他似乎对官衔根本没有兴趣,一心做好纪录片,他拍摄的《沙与海》和《阴阳》,都是中国纪录片的扛鼎之作。我认识康健宁还在十年前,那时我太太策划了一个纪录片叫《中国佛教寺院一日》,选了留个佛教寺庙,拍摄同一天从晨钟到暮鼓的生活,康健宁是总编导。
这样一个大腕的话,是不能不听的。怎么办呢?临时再找人也来不及了。康导胆子大,他对我说,你来写!我说,我没有干过这活儿啊!说来惭愧,我从进入媒体行当,就一直没有专长,只能当领导,动动嘴。康导说,我看过你写的《财经文摘》杂志的卷首语,我喜欢那个风格。
我想了两天,答应了。一是因为王震家里的事情,我愿意帮忙,我在编辑出版王震画册的时候,王震夫人、王震的几个儿子都对我非常好;在就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当一个电视撰稿。
一不小心,我从制片人转行成了撰稿。
结果还不错,我写得很快,一集大约一万字,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完成了六集的撰稿,期间还专门到新疆实地考察了一次,加深了对王震的了解。
尽管王震一生转战南北,戎马倥偬,新中国成立后也屡建功勋,但这六集纪录片每一集的开头都是新疆,为什么呢,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王震作为新疆的最高领导,管理这占中国领土六分之一的土地,在这里,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和才华,这之后的每一项工作,似乎都可以看到新疆的影子,似乎都有一条线连着新疆。
很多人在评论王震治理新疆时,都会说,王震那时候用了强硬的一手,镇压土匪和反革命分子,把新疆镇住了。我总是要反对一下,我说,王震是有硬的一手,但是,他也有柔的一手。他到新疆以后,为新疆修了第一条铁路,创办了八一钢厂,修引水渠把天山雪水引入农田,水渠修成那天,王震像孩子一样跳入水中欢呼。而做这些事情,很多经费都是从军队省下来的,那时,王震指示,把军装的兜布,把帽子的帽檐都省下来了。为了解决官兵包括国民党的起义军队官兵的婚姻问题,王震亲自给黄克诚写信,要求他支持,结果才有了八千湘女下天山的故事。这些,其实就是柔的一手。刚柔兼济,才是王震。
为了写好这个稿子,我到深圳又和老太太有了接触。这时,她已经重病缠身,说话也没有了力气。脑筋也大不如前了。在饭桌上突然出现了我这个外人,她有点不习惯,用微弱的声音问家里人:他是谁呀?家里人贴着她的耳朵告诉她,是为爷爷写传记的,她轻轻点头,对我说,多吃点,多吃点。
第二天在饭桌上,她又看见了我,又问:他是谁呀?工作人员还是告诉她:她是为爷爷写传记的。她还是轻轻点头,对我说:多吃点,多吃点。
老人家饭量很小,吃几口东西就被工作人员推走了,她瘦小的身躯像埋在轮椅上一样,脸色也苍白得没有了血色。说实话,我是很震动的,因为这些日子看了有关王震的一些资料,知道这位老太太和王震在一起,走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我总想,这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老人家有时是清醒的。我们的摄制人员采访她时,她也说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编导问她,“王老爱你吗?”她怎么回答?谁也想不到。
“不爱,他只爱他妈。”
这话在我看来有玩笑的成分。说爱他妈,是真的,王震是个孝子。说不爱王季青,是假的,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近六十年,怎么能说不爱呢?
当然,他们不是自由恋爱,是贺龙把两人硬牵在一起的。刚刚到八路军工作不久的王季青还想讲讲条件,说我还要考察一下他。贺龙一句话把她顶回去:考察什么,组织上考察了这么多年了,还用你考察?听起来这话不讲理,但是战争年代就不是讲理的时候。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初期,残酷的岁月里。
七十年过去了,老人家做了多少事情!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做了多么好的一个人!
二〇〇八年四月,在王震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六集纪录片《王震》,说实话,我不敢看,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写的太差了,另一方面,删掉的精华太多了。
对于王震这样一个人来说,差了许多的血肉,当然就不够饱满。
不过,在我的心里,王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这就够了。
砥砺人生
飞越黄河
飞翔在草原上空的凤凰
创办《凤凰周刊》的日子
如果说,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在上学,有点像在翰林院的行走,到了凤凰卫视,像另外一种学校,更像在市场上的摸爬滚打。这里是更纯粹的市场,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战场,要赚钱,要扩大知名度,还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也许是你的同盟者,也许是你的对手,更也许,有些人看起来是你的同盟者实际上是你的对手甚至敌人。
在这里,我经受了更多的锻炼,都说好钢要淬火,人生要砥砺,在凤凰卫视的七年,也是淬火,也是砥砺。
如果说,我创办共识网,要有学识的积累,要有人脉的增加,要有人生的阅历,要有坚韧不拔,那么,正是这样一个个的链条,把我和这些有用的词语连在了一起,我感谢其中每一节链条,哪怕它划伤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