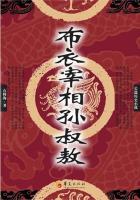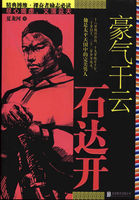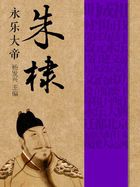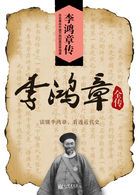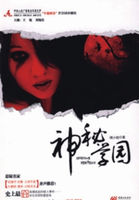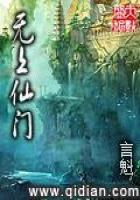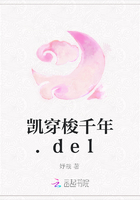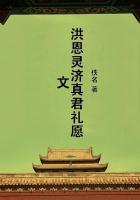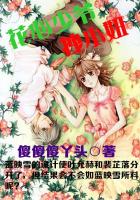十八大落下帷幕,中国开启新的时代。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达成共识。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固然是共识基础,各方能坐下来平等对话才是先决条件。朝野、执政党内部、知识分子群体都需要通过思想交锋、观点碰撞,以达改革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改革分歧不可怕
翁一:改革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但是,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未能同步进行。自八十年代末以降,政治体制改革被多方设限,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更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十年,经济改革也在“国进民退”中步步倒退。这些年来,曾经一度达成共识的改革议题何以逐渐失去?
周志兴: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够达成改革共识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九七六年爆发“四五”运动,大家都极力反对极左,体制内外呼声一致,高干子弟还起了引领作用。斯时,全国意见最为一致,也有着全面的共识。文革结束后,政治上从极左路线中走出来,而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贫穷不堪。很多旧东西要改掉,新东西要建立起来,百废待兴,整个社会明显处于转型期。因此,当时取得改革共识是较为容易的。
但是,回头看来,改革最初就有分歧。一九七八年,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要求变革,可已经表现出意见的不一致,争论焦点在于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一九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为以后的改革埋下了分歧的种子。
今天,中国再次面临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并抱团成为拥有动员强大政经资源能力的利益集团。对这部分人而言,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他们当然不愿意。所以,改革三十年后,各方要达成改革共识会比较艰难。
当然,分歧并不可怕,且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前提是这个社会要出现利益分化,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发育成熟,这样才可能形成制衡。所谓民主,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为自己的利益博弈。而一九七九年,利益还没有分化,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城市化还没起步,中产阶级、商人群体都还没有产生,整个社会简单而脆弱,受大半个世纪激进的革命思潮影响,人们的新诉求仍然非常理想化。而只有成熟社会,才有文明博弈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取得改革共识比较艰难,但却也正当其时。
重建改革共识,首在朝野共识
翁一:改革的步伐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不能让人民满意。更为根本的是对于如何变革不公的制度,各方亦未能达成共识,以致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力,体制内没有改革的动力。对于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在哪一个层面达成共识?
周志兴:对于今天的中国改革,最为重要、最具有决定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来自中央的决心和规划。回望经济改革,是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股力量在互动中共同推动的。改革是上下合力的结果。
当下,国人对于改革共识的讨论更多寄希望于达成左右共识。但从现状分析,要重建改革共识,纵向的朝野共识恐怕比横向的左右共识更为重要。只有建立起朝野对改革的共识,改革才有可能推动,而当下真正的左右分歧,远远没有国人以为的那么严重。改革的朝野共识可以逐步达成。且政改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民间期待改革,党内有远见的力量也正试图推进改革,这就是达成朝野共识的基础。中国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党内依然存在强大的理性力量。
朝野要达成共识,前提条件是朝野之间的良性沟通。政府官员是在朝的,他们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把握国家的大船前行,老百姓既是船上的乘客,也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毋庸赘述。因此,在朝者要多听在野者的意见,船才能开得稳。说起来容易,做到却殊为不易,如何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与建立可操作的沟通机制,着实考验执政党的智慧。
翁一:朝野要达成改革共识,妥协必不可少。
周志兴:是的。十八大之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更高,很多人都盼望推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实际上,这种改革也包含了妥协的成分。为什么要改革?因为有些生产关系影响了生产力,有些上层建筑影响了经济基础,有些做法或者有些政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了不满。为了解除这些不满,就要调整相关政策和做法,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妥协。
可以把这种妥协看作是良性的妥协。而良性的妥协一定是双方的合力的结果。因此,要达成改革共识,就要懂得妥协、学会妥协,多听对方的意见,多理解对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对方一步。
妥协,不仅是弱势一方和理屈一方要做到,强势一方和占理一方也同样要做到,千万不能把对方逼到墙角。就说现在的官民这一对矛盾,各地群体性事件中,常常是官民矛盾深藏其中,相当多的时候是政府官员处置失误。政府当然要妥协,但是,老百姓也要学会妥协,不要觉得逼得官员威风扫地就是好事。谁都不妥协,弦就会越绷越紧,总有一天会拉断。弦断容易,接起来可就困难了。
改革进入深水区,收拾人心当先行
翁一:那么,执政党内部对于改革有何不同意见?十八大已落下帷幕,顶层对于重启改革是否已有了初步意向?
周志兴:党内也好,政府内部也好,永远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正是改革的空间所在。干部队伍本身也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制度原因,囿于自身的乌纱帽,在一定意义上亦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又有良知的召唤,一部分开明官员认为现行体制有问题,也认同并且接受循序渐进的改革。因此,在一些场合,可以发现体制内人士与体制外人士的想法往往是一致的。正是这部分开明官员,他们有作深层次改革的诉求。
而另一部分官员,因为涉及自己的利益,希望维持现状,不作大的改革,只做表面文章。作为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他们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班子带头,地方跟进,初步在作风上有了改变,例如轻车简从,简化接待礼仪;在文宣上反对假大空的言论;在会议上,尽量做到切合实际,不奢侈铺张。但不应止于此。镰刀割草,不能去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的生命力极强劲,不断地一茬一茬地割,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在去根上下功夫。如果蜜月期一过,迟迟未见改革的实质性动作,依旧延续之前的老方法,那是不行的。所以,要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就要有电钻一样的利器深入下去。
新一代领导人表达了改革的愿望,行动上在一些大家看得见的层面,部署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千丝万缕,例如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党政分开,司法公正等等,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甚至不可能一下子铺开,渐进主义地推进改革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表,一个路线图,要让人民看到更加光明的前途。
当然,党内会有不同意见,包括他们现在表面做的东西,都会遇到相左的意见。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如果能顶住压力做下去,就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比较灿烂的一笔。
目前,执政党需要改进作风,以制度反腐为契机,重新把人心收起来。如果继续腐败、继续官僚化下去,就不能提改革了,一提改革反而会引起大的乱子。今年两会即将来临,政府换届在即,要推进改革,首先要收拾人心,让人民群众看到执政党在往好的方面改进,让人心更多地凝聚在党的周围,才能一呼百应地推进改革。
翁一:重建改革共识的当务之急在于收拾人心,历史上因收拾人心不当而造成国家分崩离析的教训何在?
周志兴:在上世纪后半叶,中国曾有过两次人心齐的时期。一次是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很多人心中一扫阴霾,认为中国这艘大船换了船长,光明的彼岸就在眼前。但是,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使得人心丢失,尽管口号喊得很响,实际的前进速度却慢了下来。
再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结束十年文革,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开始,无论是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心又一次聚拢。但是,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聚拢的人心再次慢慢散去。
同样,今天也到了收拾人心的历史时刻。
今年七月,《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赶快收拾人心》,其中写道:“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合法性资源不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本文从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看到了人心逐步丧失。作为一家党报,字里行间关注着人民、国家和党的生命。
如果把时间回溯六十四年,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也是《赶快收拾人心》,文中说道:“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少数人来挽救最大多数人。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是看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我们走少数人的路线,那么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的。如果我们走多数派的路线,甚至口里不标榜革命,老百姓还是知道我们是革命的。”这篇社论最后说:“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行将丢掉政权、退守台湾,却浑然不觉。二〇一二年,中国共产党还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领导者。两篇社论,虽同名,但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不难发现,是《中央日报》的社论为时已晚,国民党已没有时间来收拾人心了。
今天提出这样的问题,算不上未雨绸缪,言亡羊补牢却不为过。执政党需要警醒:不能再沉湎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应当看到,贪腐、改革步伐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民主建设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骄纵蛮横,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人心。
超越左右之争
翁一: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内部急剧分化,笼统言之,这一群体分化为了左派与右派,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他们有哪些分歧?
周志兴:社会转型期是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为了简便,人们常常把不同的思想观点归纳为“左”与“右”。这种归纳其实不尽合适,但是,却成了约定俗成的标签,也许会贴错,但是总能找到对象来贴。无论准确与否,左与右的争论是随处可见,尤其在微博这样一个公共平台上。现在的这种争论,似乎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可以跳出网络,在现实生活中“约架”了。可见,左右之争朝着白热化在发展。
在左右之争中,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左右,都觉得自己正确,而且都觉得自己的支持者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哪怕是十分弱智的观点、十分“脑残”的人,都会毫不掩饰和毫不心虚地宣称,自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认为左派知识分子与右派知识分子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分歧,他们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有一致性的,也具备就宏观政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左右互相之间不交流,没有耐心倾听对方的意见,没有认真思考对方意见中与己一致的东西,这是造成知识分子分裂的主要原因。任何讨论,都要有理性的态度,所谓理性态度是指不同观点的人,要能够坐在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互相排斥,甚至不论是非只论立场;要能够理性表达,而且能够认真听取别人的观点,从中寻找自己可以接受的部分,哪怕是完全不能接受,也要讲出道理来。就是那句老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北宋诗人苏轼有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观感,所以,囿于一群,就难以得到全面的和正确的看法。左右之争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因为左右之争而把自己捆绑起来因而难以左右,就往往会陷入泥潭。
左右之争涉及的还是沟通问题,刚才讲到了朝野沟通,其实还包括左中右、官产学、国内外的国通。左中右的沟通中,左右两部分中的极端分子,几乎坐不到一起,遑论交流?所以,这三者的交流要从易到难地开展,先是中左中右,逐渐向两端延伸。起码要先坐在一张桌子前,先互相混个脸熟,先了解对方在想些什么,表达的观点究竟有什么内涵,有没有合理性蕴藏其中。
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是当今社会其实也是任何时候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也是社会气候的晴雨表。所以,他们代表的声音,基本上是社会主流的声音。
另外,就算是顶尖的国外汉学家,对中国也有很多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有的从正面误读中国,有的从负面误读中国。原因在于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常常是根据媒体和部分人的意见得出结论。国内外的沟通,官方学术机构组织些论坛固然需要,但更多的还应当是民间渗透式的交流。
翁一:知识分子对于改革有何推动作用?
周志兴: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改革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比如知识精英和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对改革的期待肯定不一样。一九七九年政治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要求,一九八九年有这个要求的圈子扩大了一些,到了今天,这个圈子更大了。社会在改变,人们的意识也在改变。尽管如此,今天中国大多数人对改革的诉求与一部分知识精英提出的改革诉求是不太一样的。一部分知识精英从来认为自己的诉求应该是首位的社会诉求,这并不客观,也未必能代表大多数人。
当代知识分子,力量本来就不强大,在政府这个利维坦面前,完全处在附庸地位,谈不上独立性。提出的大多数主张没有太大价值,很多东西都流于纸上谈兵。有一些知识分子会去跟政府唱反调,但是过于激进、毫无策略,很多时候生存都是问题。另一些知识分子尽管表达了正确的意见,但是他们自身的责任感、对自己的约束力,包括团结大多数的本领,都很差。一些深受民众喜欢和崇拜的知识分子,就那样慢慢地把自己给毁掉了。经历这些年的大浪淘沙,知识分子的力量已是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比左右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朝野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