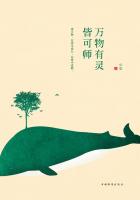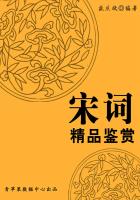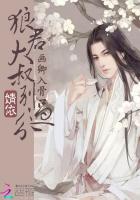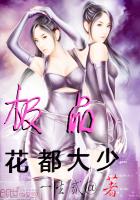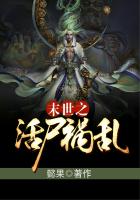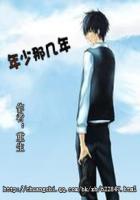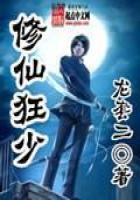荒诞派戏剧就是属于丑的艺术。“荒诞”意为“违反理性、不合逻辑、不适当”。[53]尤内斯库则认为:“荒诞是指切断了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基,人失去自我,一切行动毫无意义、荒唐而无用。”[54]荒诞戏剧正是这一定义的体现。喜剧是荒诞的直观,荒诞的、放大的丑带来了喜剧的效应。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模仿。”[55]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坏”不是“恶”,而是“丑”。[56]“品特戏剧中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就像《皇帝的新衣》,喜剧效果一览无遗”。[57]品特戏剧中病态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外表,正是“丑”的表现。他们或是双眼空洞,绑着绷带,或是身材矮小,走路一跛一拐,这种病的外表的夸张产生了“丑”。而通过人物病态的动作反应,更增加了喜剧性的成分,例如,由于失聪,人物往往答非所问;由于失语,人物说话结结巴巴;由于精神失常,人物竭斯底里,动作失常。这些动作反应呈现出一种与正常行为大相径庭的形象,使诙谐得以产生。而病态人物常常遭到他人捉弄,更呈现出一种丑态。例如,在《生日晚会》中,斯坦利眼镜被拿走踩碎,被蒙上了双眼,漫无目标地四处摸索,被麦肯恩故意放置的小鼓绊倒,摔倒在地。又如在《微痛》中,妒忌妻子、心胸狭窄的爱德华的一系列行为导致妻子真正地喜欢上了卖火柴的小贩后,双眼昏花、四肢麻木,口不能言,妻子顺势将卖火柴的器具塞到了他的手中,将他变成了卖火柴的小贩。“荒诞戏剧经常使用的手段就是突然使观众面对一个疯狂世界的怪诞放大和变形的图画……观众面对着动机和行为几乎都不可理解的人物,他们几乎不能与之认同,他们的行动和本性越神秘,越不具备常情,就越不容易令观众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观众不能认同的人物不可避免都是喜剧性的”,[58]疾病的突变作为一种夸张也展现出了喜剧的效果。在多部戏剧中,品特的戏剧人物受到精神打击,立即瘫软倒地。例如在《茶会》中,本是想以眼疾为名洞察别人心思的迪森发现妻子与情人都背叛了自己时,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又如《归家》中的老山姆,在明白嫂嫂与邻居在自己的出租车后做爱时,心脏病马上发作,两脚一蹬,告别了尘世。这些疾病的描述均有夸张的成分,通过夸张放大的荒诞的“丑”,形成了品特戏剧的喜剧性。
然而,荒诞戏剧又被称为“悲喜剧”,从“丑”到“喜”绝非剧作家最终的创作目的。荒诞戏剧以推倒戏剧的形式的逻辑性为前提进而推倒了理性的内容。通常认为,荒诞戏剧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生活,人的生活因而也毫无意义。存在主义的先驱萨特、加谬等人根据这一原则创立的存在主义戏剧,在主题内容上都体现了这一哲学思维。然而,存在主义戏剧只是在戏剧的内容上体现荒诞,他们的荒诞是不彻底的。而在荒诞派戏剧中,戏剧的形式首先遭到了颠覆。艾斯林认为,荒诞派的创作方法就是要“用非理性的形式表达非理性的内容”。[59]非逻辑的情节发展,梦呓般的语言艺术、怪诞的舞台形象,扭曲抽象的人物形象是荒诞戏剧的常见特征。在荒诞戏剧中,人物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并不重要,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重要的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及行为方式所表达出来的情绪及人物的生存状态。“荒诞戏剧中的人物从来就没有活得有尊严,面对他的人物,荒诞剧作家展现的是冷漠的嘲笑的宽容,但是几乎毫无爱意……就如众多的医生诊断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罪行及焦虑的世界一样,荒诞剧作家展现的是疾病,而不是治疗。”[60]荒诞戏剧着力展现的是世界的不和谐,是人类处境的终极真实,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完全契合这一哲学思维,他的威胁喜剧又被命名为“黑色喜剧”,是让人笑中有泪的戏剧,是“以喜剧的形式表达悲剧的内容的戏剧”[61]。从词源学上来说,病人( sufferer)就是受难者。与早期的疾病意味着邪恶、不道德相异,品特戏剧中的受难者几乎都是普通人,是社会中的弱者,这些病态人物身上的疾病是他人伤害的结果,他们本是社会的弱者,却又遭到了他人的捉弄与伤害,在他们可笑的外表与行为下,是社会的不公,是弱肉强食,是无奈与辛酸,是现代生活中的惶惶不可终日。对疾病的讽喻功能颇有研究的学者兰姆贝克指出:“讽喻言说人类处境,根植于人类处境。疾病作为人类的一种处境,为讽喻提供了可能。”[62]患病,是尴尬的,是痛苦无奈的,是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的。当观众看到品特式人物拖着残病的躯体,以蝼蚁式的方式生活着不禁嘲弄发笑的同时,他们也会从这些病人当中看到自己的,以及正在生活着的世界的影像,品特借助种类繁多的疾病的丑的形象喻指扭曲的病态世界,以“丑”讽喻令人难以满意的社会现实。
第四节 疾病的戏剧性与宣泄效应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著《诗学》中,针对悲剧提出了著名的“净化”学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观众在看戏之时会自动融入剧情,被剧中的情景所打动,为剧中人物的凄惨人生遭遇而感叹,为剧中人的高贵人格所折服,于是情感从心中喷涌而出,得到宣泄,心灵受到净化。疾病作为品特戏剧中的重要元素,在激发情感宣泄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戏剧的写作本身就是作家的一种情感宣泄,那么疾病意象又宣泄了品特怎样的情感呢?德国剧作家古斯塔夫·弗莱塔克( Gustav Freytag)在讨论戏剧性时指
出:“所谓戏剧性,就是那些强烈的、凝结成意志和行动的内心活动,那些由一种行动所激起的内心活动……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种激情本身,而是表现一种导致行动的激情;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个事件本身,而是表现事件对人们心灵的影响。”[63]戏剧中各种要素的运用的最终目的在于戏剧性的生成,以达成剧作家的目的———对观众心灵的影响。疾病作为品特精心选择的元素,在戏剧性的实现过程中功不可没。首先,由于疾病的普遍性,容易让观众与剧中人物形成认识的同一性。自有人类以来,疾病便伴随人类,人的一生也难免要与疾病打交道,人类对疾病有深刻的认识。说到疾病的普遍性,迈克丹尼尔如此进行了陈述:
在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家庭叙事中,疾病总是一个明显的主角。即使我们自己逃脱了重病的侵袭,我们也无法阻止它深入我们的家庭或是朋友当中。通过照顾,疾病使我们团结,然而通过残疾或死亡,疾病又将我们分离。它使我们理解生活,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创造了混乱和疑虑。它激起了勇气和恐惧、希望和绝望。从孩提时候开始,疾病就像我们所吃的食物和我们体验到的强烈情感,如情爱和拒绝一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个人和家庭生活。[64]
如同吃饭穿衣,如同恩爱情仇,疾病已经深入了生活的肌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据学者研究,戏剧的最早形式———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除了人所皆知的感恩狄奥尼索斯带来丰收的内容以外,还跟疾病治疗相关。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是梦境中的艺术,在沉醉中,人们载歌载舞,让生命的本能尽情发挥,其本质上是一种“宣泄”,而“‘Katharsis’用作美学,指陶冶;用于宗教,指净化;用作美学,指宣泄;用作医学,指治疗”。[65]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包含了“病—药—酒—醉”的过程,“它既呈现了人类对于疾病的生物、生理性特征,也有因此带给人类害怕、恐惧的心理征兆,还有通过某种方式排解和宣泄来自人类生理、心理方面负担和折磨的行动和行为”。[66]这样看来,早在古希腊时代,疾病便已深入了人们的艺术生活,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已有了深刻的理解。疾病是观众与剧中人物共有的现实体验,因而这样的事物最适合应用于荒诞戏剧的心灵直接沟通机理,实现了观众与剧情的零距离接触。其次,疾病与荒诞本身具有的同一性,为疾病直喻荒诞打下了基础。疾病是身体的不正常,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不相和谐,与正常二元对立,而荒诞是“违反常规、违反理性、违反逻辑”,是人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也与正常是二元对立。因而,身体的疾病与社会的荒诞生长于同一根基,具有最坚实的基础。在疾病与荒诞的同一性上,学者詹姆斯·艾豪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身体生病就是人们定义中的正常或健康产生了变异,疾病除了会破坏正常的生理及心理功能以外,还会打乱日常生活,毁灭期待,造成混乱。”[67]而荒诞又是什么呢?荒诞就是绝望,就是混乱,可见,疾病与荒诞之间没有障碍,从疾病跨跃到荒诞仅仅是一步之遥。最后,由于疾病的巨大危害性,疾病容易形成巨大的戏剧张力。疾病给人带来的最厉害结果往往是结束生命后的死亡,较轻微的可能造成肢体伤残,或者某种功能缺陷,即使很快能痊愈的轻微的疾病,也会给人们带来刻骨铭心的痛苦,可以说,疾病既是最常见、最普遍的事物,又是最为恐怖的事物。更为恐怖的是,品特戏剧中疾病虽有与生俱来的,但大都是由别人后天造成的。“荒诞戏剧不再强调情节的连贯统一,往往采用碎片式或是平面式的舞台表意形式。荒诞派戏剧不再争辩人类状态的荒诞性,它仅仅呈现它的存在———以具体的舞台形象加以呈现。”[68]品特的剧作也是如此,他的许多部剧作从始到终所要达成的效果其实就是人物致病的一刹那,而前面所有的剧情几乎都成了铺垫,只是为了表现致病的一瞬间。艾斯林对此的看法是:“品特式戏剧所呈现的只是一幅打开了的画卷,表现的是一种形势,而不是整个事件。”[69]在《房间》中,以粗暴偏执的胡德高举椅子、罗斯手捂致盲的双眼、赖利蜷曲的尸体作为剧情的结束。而在《生日晚会》中,斯坦利被两个入侵的人员麦肯恩和戈德伯格逼迫得精神分裂,被带上了黑色的汽车,剧情戛然而止。在《归家》中,房间中的所有男人都或坐或跪地瘫倒在地,幕布随即被拉上。剧情结束,观众脑海中只留下人物被致病时的这一画面,然而这也已经足够,观众已被戏剧所散射出来的力量层层包裹,他们的神经已被恐怖紧紧抓住。正是疾病的普遍性导致观众与剧情认识的同一性,以及疾病的恐怖性所形成的巨大戏剧张力,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引发了观众心灵的震动。
从宣泄的角度而言,自然是悲剧性越强,效果越好。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形成依靠于戏剧人物命运的突变,他提倡以“好人受难式或者是高贵人物跌至底层”的境遇作为突变的模式,这些人物受难之前的地位与后来的地位形成了“由上到下”的巨大落差,形成了悲剧性,使观众产生了怜悯同情之心,然而他们具有高贵的品格,并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却做勇于承担责任的英雄,观众为他们所折服,泪流满面,情感得到宣泄,心灵获得了净化。品特戏剧中的人物虽非大人物,也不一定是好人,但他们是社会的弱者,本来就已命运多舛,还要遭受别人强加的疾病,这是一种“由下到更下”的过程,若说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人物是从天堂落到了人间,而品特式戏剧人物则是从人间落到了地狱,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落差,是一种命运的突变,展现出一种悲剧性。“疾病在戏剧中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它们大幅度地提升了戏剧性,在推进剧情、强化矛盾、调整节奏、设置悬念、创造紧张氛围、制造出乎意料的突转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70]正是依托疾病,品特将这种悲剧性展现了出来。在古典时期,戏剧是一种精英艺术,观众多为有身份、有地位的王公贵族,而现代的观众本来也已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这更容易让他们体验主人公的痛苦、思想和命运,由此及彼,产生心灵的共鸣,对人物的命运唏嘘感叹,然而品特戏剧的功能不仅止于此,他在写给作家鲁赛尔的一封信中说道:“观众在观看我的戏剧时会有一个从笑到不笑的过程,他们不笑了,那是因为他们在目睹剧中人物的命运之后,心生警惕,害怕与剧中人物有着相同的命运。”[71]由于“移情”的作用,观众从担心人物的命运过渡到对自己命运的担心是自然的过程。但是,他们终会发现,这样的主人公目前还不是自己,自己也许可以采取点什么行动来避免类似的悲剧,快乐的感觉又油然而生。对于疾病的恐怖、对于剧中人物的怜悯同情、对于自己也许可以避免同样命运的快乐的情感在观众心中相互交织,形成了良好的宣泄净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