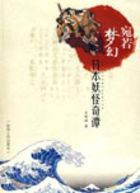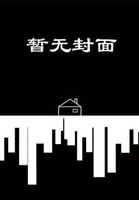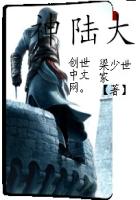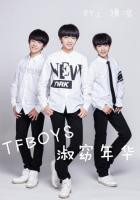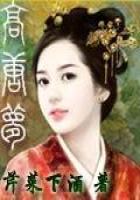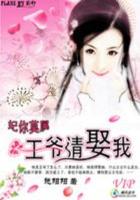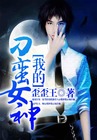怪老孙
孔明
陕西文坛,出怪人怪事,蓝田孙兴盛,更是怪中之怪。开放、搞活时,文人忙着爬格子,制造轰动,他却默默无闻做生意,邓小平南巡后,文人忙着下海,梦想发财,他却撂了生意,重操文笔,杀上岸来。先有《应聘者》出版,却不解馋,自1992年连发重磅炮弹,命中率百分之百,推出的长篇小说计有《尘世》、《沉浮》、《清河川》、《孽情》等,一版再版,印数俱在万册之上。文坛有无人羡慕,我不知道,我是他乡党,常害红眼病:同室操笔,他却捷中先登,太不够意思。故乡人不操笔,也害“红眼病”:只听说“要发家,种棉花”,没听说“要发家,搞文学。”怪在孙兴盛“倒行逆驶”,却有声有色,到西安三四年,就尽得古城风光,莫说故乡人,连古城人也要“侧目而视”了。
查祖宗三代,都是劳苦大众,没有遗传怪的因子。怪老孙生于解放前,共和国成立时,正是花朵之年,就读于故乡峒峪庙小学。他父亲做小本生意,不识字,却天生一个好记性,逼着儿子学加减乘除,所以刚上学的他,算起账来令老师瞠目结舌。一年级念了10天,老师说:“你上二年级吧。”第二天,老师让他上讲台,在黑板上写3加5等于几,他没写对,老师说:“回你一年级去。”他不服,勤学苦练10天,课文能倒背如流,老师说:“看来上一年级太屈了你!”他就又上二年级了,还成班上的尖子生。考上三年级,他转学到许庙,宿在学校,吃在街上,吃喝记账,父亲月清一次。下雨天,清浴河水涨,他立河这边,他爸立河那边,背的大锅盔送不过来,就从河面上往过撇。1956年,他初中毕业,想上中专,却被保送上高中,一年到头,勤工俭学,踏泥,烧砖,理发,糊信封,收入归班,时常干个通通夜,加班费是两个馒头。雨天干不成活,就开生活检讨会,有人检举孙兴盛手上干活,脑子里想课文,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人给累病了,学校批准休学,只一月病愈,要求复学,校方不允,他只得半年自修。高考前,他叫了一位伙伴,来到西安大雁塔,以社会青年名义报名,却被卡,原因是他持的休学证,非退学证。他两人来到田野,看一眼好风光,却泪汪了双眼。死不甘心,却无法可想,只好偷梁换柱,碰运气了。他们把高中改为初中,居然蒙混过头,报了西安交通大学热处理系,想不到歪打正着,居然榜上有名,录取通知书发到县上,教育局知了内情,对他说:“你这情况,违反了规定,一政审肯定除名。不如这样,咱县缺教员,你去教书怎么样?”当时吃饭是头等大事,恭敬不如从命,孙兴盛不说二话,就直奔白鹿原,到孟村小学报了到。过了春节,他奉命调灞源小学,兼给初中带体育课。他“贼”心不死,偷着复习功课,伺机报考大学。学校升了他两级工资,推荐他当全县红旗手,介绍他入党,提拔他干教导主任,千方百计挽留他。滴水之恩,当泉涌以报,他死心塌地了。
低标准时,吃不饱,就吃杏叶、桃叶,那个苦呀,他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害怕。他一月工资38元,他爸的小本生意虽然不景气,两三天却也可挣80元。他想不通,就要求离职回乡,申请了三次,才获准下农村第一线,还发给他退职金、还乡证。
文学的梦自小就做,回乡后就更迫切了。他写小说,写儿童文学,发表了不少,得意洋洋。有一篇小说名曰《麻婆娘》,《人民文学》杂志通知发表,但却突然因周扬的“中间人物论”被批判,而受牵连,重新通知,不予发表。他从此搁笔,发誓不再操文学,心爱的书也全卖掉。农村三自一包,他连小说都不看了,一心一意种庄稼。他的村子坡多平地少,出门就是山,地里的活挣死人,却产量不高,儿女一个一个出世,不靠山吃山,如何能养家糊口?他就跑生意,把山里货贩到城里,把城里货贩到山里。
文革开始,村里也闹派性,因为他有文化,两派人都拉他入伙。“八八”派还客气,对他温言相劝:“你参加‘八八’派,‘八八’派是革命派!”天未明,“五一六”的头儿叫他,他一见人家背着盒子枪,就怯了。人家劈头盖脸问:“两派对立,你赞成谁?”他说他中立,“五一六”的头儿火了,喝斥他:“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那人把枪甩到桌子上,抬高了声调:“‘五一六’是革命的。你到司令部来,我们让你当秘书!”他说他干不了,人家不由分说,限了两天时间考虑,不准他逃跑,还派了人监视。他老婆害怕,劝他参加,他天生一个犟脾气,心说:“你逼我,我就不参加,我不信你敢把我杀了!”总算谢天谢地,风云突变,两派树倒猢狲散,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民以食为天。他已有四儿一女,一个个面黄肌瘦的,他心里难受。把心一横,担柴,砍笼鋬,做酱油,只要力所能及,可以挣钱,他都拼了命干。每次进山,拉着架子车,他在前,妻在后,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发酸。他携妻走过兴平、高陵、乾县,拉去的笼鋬,带回的粮食。娃们饱了肚子,他却成了投机倒把分子,被打入地富反坏右行列批斗。
“我跟他把罪受扎咧。”他妻子如是说。
1979年,他从半导体收音机上听到了贾平凹《满月儿》获奖的消息,怎么也睡不着觉。第二天炕上一爬起来,操笔就写《送礼》,毕,又改写《麻婆娘》,前者8000字,后者1万字,自我感觉良好。腊月天,他直奔《陕西日报》,不料见到了叶浓先生。叶浓先生下放陕南,一去十年,归去来兮不及一月,主持文艺副刊,不期被他撞个正着,命乎?运乎?反正他时来运转,两篇都发表了。因为长,又不忍心删,叶浓先生把《送礼》推荐给《陕西日报》,把《麻婆娘》介绍给《长安》文学月刊。每提及此,他对叶浓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受了叶浓先生鼓舞,他写作的劲头更大了。1980年,他的小说《开会之前》在《陕西日报》副刊上发表,次年被评为渭南地区优秀小说一等奖。往后,他的名字常出现在报刊上。
怪老孙在创作上春风得意,人皆羡慕,谁知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弃笔从商。他在渭南开饭馆,红火时期,发展了五个摊点。又回故乡,在许庙开了蓝川酒家。人忙着赚钱,心想着小说,每年不发两三篇,心就发痒。他的《应骋者》就是在此期间写成的。
他在海里如鱼得水,拿家乡人的话说,“把钱挣美咧”。谁也想不到他洗手不干了。1992年2月来到西安,他把大小生意交给儿子,他先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又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再后来,干脆来个无职一身轻,呆在屋里,既当作家也当坐家了。
怪老孙是第九届西安市政协委员。老朋友一见到他就说:“老孙呀,你这人怪到家了。”他只管笑,怪得就像弥勒佛。
录自1994年10月27日《西安晚报》
此文收集于孔明散文集《谈情》一书
快乐在于耕耘中——近访作家孙兴盛
万世锦
在总结市政协换届后的工作时,我想起了作家孙兴盛。
孙兴盛是市政协第九届政协委员,在他任委员的年月里,我常和他一起海阔天空侃大山,转眼过半年,真想找他聊聊。
当我冒着寒冷,走进他的家门时,见他正伏案写作,我“嗨”一声,他猛回头一惊,“嘿!你怎么来了?”我诙谐地说:“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嘛,你怎么把政协唱的歌给忘了”。他放下手中的钢笔,莞尔一笑,打趣地说:“俗话说,人一走,茶就凉,看来,你是唱着歌来的。”
当我坐进沙发里边,孙先生立即递上一杯热呼呼的茶水,我说明来意,要他谈谈几个月来他的创作情况,他笑着说:“没什么好谈的,咱还是想到哪谝到哪。”我和孙兴盛先生是在五年前开政协会议时认识的,从那时起,我们两人就频频来往。据我所知,他在出版了一本20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之后,从1993年至今,已完成七部长篇小说,其中已有四部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另外三部也交出版社正在审稿,不久将与读者见面。他的小说,均以故事性很强而吸引了大量读者。最多的发行量竟达20多万册,而且很快地销售一空。
孙兴盛先生已出版的几部长篇,不同程度地被电视剧作家和影视公司看中,纷纷要求与孙先生签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目前已有两部改编就绪,其余两部亦在筹编之中。
孙先生虽然年近花甲,但他的精神充沛,毅力很大。他曾告诉我: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三两年内不死,他一定要写够10部长篇!讴歌改革开放的农村题材三部曲《玉山风情》已经全部出版,《尘世》《沉浮》《清河川》早已为读者所熟悉;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峣柳风云》系列《孽缘》《孽种》《孽情》三部也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另有城市题材《都市弄潮》四部,已完成《苦夏》《闹春》,其余两部将在1998年年底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