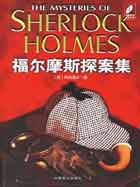津子围听到了,他想了想,说:“……可能吧。”
“你实际在谈物质的局限和精神的局限,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宋词说。
“而实际上,这两者有的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常常是这样,看似自由越小的人他的自由越大,反之,觉得自己的自由很大的人,其实他的自由很小。”
我相信,津子围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他们一定把我作为解剖对象了。津子围向我转述时,我想,有些内容他是不能转述的,一件事经过了语言的转述,跟事实一定是有差距的。不过,我听到他们的关于自由的评论,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后来,他们又讨论我的爱情生活,津子围没讲他们是怎么评价的,我这样想,津子围不讲说明他不想讲,不想讲自然有不想讲的理由,我也没有问的必要,那样,会让人觉得我很在意那些,我没什么好在意的。
宋词说他的爱情已经“过季了”,他犹如燃烧过的篝火,只剩下炭火的余温。
“你这个年龄是不应该的,除非另一种可能。”
“什么?”
“提前透支。比如人的感情是一瓶酒,你喝得太快了,没有平均分配,提前把酒喝没了。”
“是那么回事儿,你哪?”
“我没有,我是喝的少,剩的多。”
小玲在一旁大笑着,她对津子围说:“你应该把你的酒分给宋词一些。”
宋词说津子围是这样的人,“他传带技术不错,只是临门一脚欠佳。”
“怎么解释?”小玲问。
宋词说他和女人交往还好,有的认识r好多年,像足球运动员的传带似的,可关键的地方总是突破不了。
“为什么?”小玲又问津子围。
津子围笑着说:“别听他的。”
“有一次,我们和一位西北来的朋友喝酒,那个朋友自称是气功大师谁谁的传人,他说他会一种特殊的催眠术,让—个女的跟他走,就跟他走,让女的躺在床上,就躺在床上。当时津子围说,那你教我这个功法吧。大家说,你学了也没用,你可以让女的跟你走,也可以让女人躺在床上,关键是,等女人躺在床上,你说‘好好休息’,转身就走,并轻轻把门关上……”
津子围说:“夸张点了吧。”
“我说的是事实。”
“……的确,”津子围说,“我在这方面是有点笨,一到关键时候就没了办法。”
小玲问:“缺乏勇气还是别的什么?”
“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因素,观念、经验……总之很……”
“可这是一种逃避,男人的责任并非完全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几种,还包括你说的这个问题。”
宋词说:“男人真他妈的累呀。”
按着津子围的说法,后来,他们就没再谈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不过,宋词和小玲送他到飞机场之后,津子围说他从一种环境又到了另一种环境,“好像一个锣鼓喧闹的剧场,一场大戏突然停息,曲终人散。”津子围坐在候机大厅,望着窗外雨中的停机坪,静静地等待着晚点的飞机出现。就在这个时候,津子围给我挂来了电话。
“我在珠海。”津子围说:“我知道。”
“过一会儿要飞三亚。”
“是吧。”
“我在珠海的飞机场。”
“啊。”
“飞三亚的飞机正点是九点四十,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是啊,已经十点半了。”
“到三亚应该是凌晨了……”
我知道他实在是无聊了,不然,他从不这样嚷的。我问他还有别的事吗?
“没什么事津子围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在珠海。”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津子围的电话来的非常不是时候,他打电话时,我正和李司拥抱着,我们彼此注视,我几乎要找到我们火热那时的影子了,有了要吻她的愿望,这个时候,津子围给我挂来了电话,把我的情绪全破坏了。
从果园回来之后,李司的情绪很好,她像这个房子里的女主人,她开始安排我换衣服,她自己则到厨房做晚饭。我想象不出李司为什么会喜欢下厨房,也许,在这方面女人有一种潜意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事业上找到信心和具有强烈的支配愿望的李司,平时是不会下厨房的,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她眼下面临着人生难题。她现在不是大公司的“李总”,而是一个被通缉的“流亡人士”。也许,她想在被抓以前体会一下做一个传统女人的感觉,也就是她曾经要摆脱的、事实上已经摆脱了的传统女人,而在她看来,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也许,她还会这样认为,这样的生活比她当“李总”还值得过。——关于这一点,这几天我已经有了察觉和感受,只是,她越这样我越觉得心里凄凉。
晚饭后,我和李司在壁炉前静坐着。
李司说我小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梦想,晚上,我的情人在炉火旁为我朗诵诗歌,或者在我人睡前为我读爱情小说。
我明白李司的意思,因为我们就坐在壁炉旁,壁炉里燃烧的火焰呈现出多种颜色,尽管那些火焰并不是真的火焰,真的火焰应该噼啪作响,应该不那么均匀的,可那火焰一样很逼真,坐在旁边,就有了被火烘烤的感觉。这是一个真假难辨的时期,一个可以复制的时代。我相信,李司可能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不排除她的想法是在壁炉旁才产生的,她不过是使用了一个惯用的话语方式:我小的时候……
我对李司说,我的书橱里还真有诗歌集子,有几本是津子围给我的,津子围不写诗,可他还是比较喜欢诗的。
我从书橱里找来了阎月君的诗集,那是津子围去年送我的。我还记得那是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和李红真在一个咖啡馆聊天,李红真说她想要一本津子围的书,我就给津子围挂了电话。那时,津子围正和邓刚、孙惠芬等人聚会,他们大概在一起谈小说。我说你能不能过来,他说现在不行。我说一个漂亮小姐想要你的书(李红真不满地白了我一眼)。他说改日吧。我问他什么时候结束,他说怎么也得九点多。
“那没关系,你是知道的,九点半我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那天,津子围带来了阎月君的诗集《造句与忧伤》,却没带来他自己的书。
“阎月君是我认为最好的诗人之一,我的看法并不一定等同于别人的看法,这也没办法,我就这样看!”津子围说。
他还朗诵了几句:
——生下我的那女人
其实是放了一把火
孕育了一种波涛
点燃了一场战争的导火索
听听,这样的句子出自一位女诗人的笔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李司见我从书房回来,她问我:“你拿着什么?”
“一本诗集。”
“你真的要给我读诗?”
“是啊。”
李司激动得脸色涨红,嘴上却说:“瞧你,样子做得还蛮不错的。”
我努力用读诗的那种声音朗诵了起来:
——没有一个词是靠得住的
实词呆头呆脑
虚词几乎无赖
介词小心翼翼
形容词奇奇怪怪
什么能充当这座大厦的依赖
支撑到天老地荒
有没有确信无疑
值得一锤子钉下去的东西
名词开始怀疑
动词开始怀疑
形容词是更加神经质的怀疑
赝品们的问題仍是去年的问題
去年的你曾说要向哪里去
……
我的诗只剩下疑问
李司静静地看着我。我问她,你感动了吗?李司说:有没有比这更煽情的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