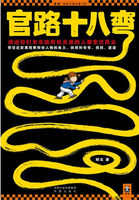我又觉得无聊了。有时我想和勇勇堂哥玩,可他在上学,白天在学校里,晚上回来就到他自己的屋子里写作业。有时我悄悄进屋去,他一看见我,就会不耐烦地冲我说:“你烦不烦?一边去!”把我赶出来了。牛栏土墙的屋角上有一个蜘蛛网,一个拖着大肚子的灰蜘蛛静静地吊在网中央,我有时就和它说话。我说:“蜘蛛蜘蛛你好,你想妈妈吗?”可蜘蛛听不懂我的话,只用纯洁的黑眼睛看着我。我又去沙坑里掏“地拱牛”,掏出来后,我也不抓它们,赶着它们在沙土上爬,然后说:“‘地拱牛’,找妈妈去吧!”看着它们用头拱开沙粒,重新钻回土里面。我想,它们可能找到妈妈了。这时,我就又开始想爸爸妈妈了。自从爸爸妈妈一走,不管爷爷奶奶对我有多么好,我都始终觉得自己走在一条孤寂的路上,没有爸爸妈妈在家时那么快乐。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帮我解脱孤独和空虚。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妈妈那时在北京的日子非常艰难。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他们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和家里保持联系。爷爷把所有的信都装在他一只极为珍贵的木匣子里。木匣子箱盖的背面,爷爷用他只有初小文化的水平,歪歪斜斜地写着全家人的生辰时刻,从大爸一直到最小的堂妹。大爸他们名字的墨迹都有些看不清楚了,而堂妹刘芳的名字,却像是昨天才写上的一样。爷爷把大爸、二爸二妈、爸爸妈妈的信放在匣子里,在爷爷心里,这些信无疑也是他的珍宝。
爷爷怕我们去翻他的匣子,就把匣子放在大立柜的顶上,让我们搭上凳子也够不着。奶奶死时,爷爷让我爬上梯子,到柜顶上取东西,我顺便就把匣子里的信翻了出来。
爷爷把大爸、二爸二妈、爸爸妈妈写给他的信,分别收藏保管,每沓都用橡皮筋扎着。爸爸妈妈写的信最多,有二十多封,最少是大爸,只有四封。我想,大概是因为有大妈在家里,大爸把信都写给大妈了。我自然是先读爸爸妈妈的信。
妈妈在一封信里写道:
我们住的地方叫六里桥,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远。我早上三点钟就要出门,骑一小时自行车赶到队里报到。然后有点什么杂事比如班长队长讲讲话,再坐上队里的三轮车到工地那儿。大概四点多钟,就开始扫马路、装垃圾,不停地干到早上八点才下班。我们班一共有五个人,我一个人要扫两里多路面。工具都放在那里环卫处的一间小屋子里,去了就拿东西干活。一般先扫一遍,然后就是拿着垃圾箱和扫把,看到什么脏的东西就捡起来,保持路面的清洁卫生。像我们这样的打工仔都得仔细干,从不敢偷空站下来歇歇,因为有班长在一旁监督着,班长是正式工。班长要是发现谁偷懒不认真干活,那就惨了,有被辞退的危险。八点以后到下午四点,是正式工来接替我们。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元,正式工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五百多元,而且工作时间还那么好。不过有什么法呢?谁叫人家是北京人,我们是外来人呢?就是这八百元钱,也比在家里种地强好多倍了……
我那时上小学三年级,读信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了妈妈扫路的一幅活动的画面来。妈妈戴着大口罩,北京初夏清晨的空气虽然十分清新,但妈妈无法顺利地呼吸到。路灯把妈妈的影子投到路面上,妈妈的影子会比实际身子长得多。亮着明亮车灯的大小汽车从妈妈身边飞驰而过以后,四周寂静下来,只有妈妈扫帚擦在路面上的“沙沙”声。妈妈会偶尔停下来,捶一捶累酸了的腰。在捶腰的同时,她的眼睛要警惕地、不停地四面逡巡,像胆怯的小兔子一般,因为她怕监督她们的班长发现。天慢慢亮起来,妈妈的头发被北方的露水濡湿了,上面沾了一些被扫帚扬起的浮尘。面对冉冉升起的太阳,妈妈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不知是驱赶疲劳和睡意的侵袭,还是庆幸终于迎来了早晨。
妈妈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房东是个哑巴,一辈子也没结过婚,今年都五十多岁了。我们挺同情他的,尽量照顾他,洗衣服的时候,我就把他的衣服收起一起洗。他对我们也很好,尽管他说不出话,我们却看得出来。他住在底楼,屋子很潮湿,前几天,我们屋子的墙壁上,突然爬了一只蜈蚣虫,我就对他说:‘大哥,我们屋子里连蜈蚣都爬进来了!’第二天,他就叫人来把墙壁重新刷了一遍。在屋子的角角落落,还喷了一遍药,就再也没见到蜈蚣了。我们算是遇到好人了……
可是,这个“好人”不久却露出了自己的不良用心。他开始用那种火辣辣的、不怀好意的目光看妈妈了。妈妈早上下班回来,困乏极了,好想上床睡一觉。可这个老光棍却会找各种机会,过来骚扰妈妈。他一边用那种下流的目光看着妈妈,一边打着手语,“叽叽哇哇”和妈妈说着什么。妈妈听不懂他的话,却能看懂他目光里的意思。妈妈就尽量防着他。可是有一天,老光棍还是把妈妈抱住了,他一边打着手语,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两百元钱,往妈妈手里塞。妈妈还读懂了他的手语:他告诉妈妈,只要妈妈答应了,他可以免除他们的房租,还替他们交水电费。妈妈用力挣脱了哑巴的手,对哑巴说感谢你的好意,可你别把我们外来人想得那么贱!说着把两百元钱甩给了哑巴,跑了出去。
没隔几天,爸爸妈妈就搬家了。
在每封信里,妈妈都要问一问家里的情况,问一问我和妹妹的情况。有一封信里,妈妈跟爷爷这样说道:
中央现在说要减轻农民负担,村里减轻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年纪大了,一定要看开点,穷就穷过,富就富过。庄稼能种多少就种多少,一定要把扬扬他们带好,等我们挣到了钱,我们就也在北京买套房子,把你们和扬扬、玲玲都接到北京来,让我们也做北京人!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笑话我是蚊子打哈欠——口气大,那天我们单位来了几个当官的,说是来视察的,其中一个当官的表扬了我们几个扫地的农民工,他鼓励我们好好干,以后就留在北京城。他还说,中国现在有八亿多农民,只需要三亿左右的人种庄稼就够了,以后有差不多五到六亿的农民要成为城里人,因为中国要城市化。我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我们身边确实有许多打工仔在北京买了房子,做起了城里人。到了那一天,我想就好了!
读到这里,我的心里一下高兴起来。我想,如果我们都去了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去看天安门吗?一想到天安门,我马上又想起了爸爸妈妈临走时说过的话,于是就在信里去搜寻爸爸妈妈是不是去看过天安门了,可看遍了他们所有的信,都没有找出这样的话。
“扬扬,你在哪里?快回来!”奶奶的声音在院子的上空飘扬,透着她的着急和恼怒。
我就藏在屋后一堆柴火里。晌午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叫罗爷爷的老剃头佬来到了我们院子里,就悄悄躲了起来。过去都是这样,只要罗爷爷一来,妈妈就会把我拉到他面前,像牛不喝水硬要把它的头按到河里一样把我的头摁进水盆里,指甲重重地在我头皮上抓着。我会很不舒服又很不老实地扭着身子,妈妈就会用她湿漉漉的手在我的屁股上打上一气,说:“老实点,看你的头发都能脏一河水了,不洗干净今后哪个女人会嫁给你?”我最怕肥皂水流到眼睛里辣得我“哇哇”叫唤,还怕水呛进我的鼻孔里,那滋味也很不好受。情愿没有女孩子嫁给我,我也不愿理发。所以,每次看见罗爷爷来,我就要躲得远远的。
可是,每次我都会被爸爸妈妈捉回来,推到罗爷爷的“行刑台”上。说也奇怪,每次到了罗爷爷这个老剃头佬这里,他总能让我安静下来,使我乖乖就范。
我怕罗爷爷,可我又很喜欢他,要是他超过时间不来,我还会在心里想念他。这不但是因为他有一肚子故事,还因为他的小把戏让我着迷。他只比爷爷小几岁。“罗爷爷不但给你剃过胎头,还给你大爸、二爸、你爸爸他们几弟兄剃过胎头!”爷爷有一次对我说。我知道他是爷爷的好朋友,每次来村里剃头,都在我们家里吃饭,天晚了还住在我们家里。他总爱摸我的脸蛋,摸着摸着,就在我的腮帮子上轻轻拧一下,一边拧还一边说:“狗日的,硬是像你爹脱的壳,一点也不走样!”这让我很不舒服。可他的耳朵能动,鼻子也能歪到一边去。还有最绝的,他的身子不动,头也不动,脖子却能来回运动。每次移动脖子,妹妹就欢喜得哈哈大笑,还往他身上爬。我努力去学,可怎么也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剃头佬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能学会吗?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这是新疆舞里的动作!新疆舞知道吗?”说着,他的眼睛看着我,双手抬起来,一只手向前,一只手在后,手指弯曲,右腿稍稍抬起,然后左脚蹭地,疾步向前,嘴里发出“嘚嘚”的响声,最后右手在头顶旋出一个漂亮的弧形,喊出一声“嘚儿——驾”,停了下来。
“这叫骑马,知道吗,小崽儿?”他看着我,脸上露出十分得意的表情。
我看得入迷,后来他这个骑马的动作终于被我学会了。那一段时间,村子里只要有我的身影,就一定会有我“嘚儿——驾”的声音和半像不像、如青蛙单腿跳跃前行的怪动作。
后来我才知道,老剃头佬在部队当过兵,他理发的手艺就是在部队学的。后来因为嗓子好,又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所以,他能跳新疆舞。
“扬扬,出来呀,你个小祖宗怎么这样不听话呀!”奶奶叫着走过了我藏身的柴火堆。从柴火堆的缝隙里,我看见了奶奶被汗水打湿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了背上,她一边走一边说:“这个小祖宗,真是怄死人了!理了发好上学发蒙读书呢,你躲什么!”
我才不管读不读书,反正我不想理发。见奶奶走出有两丈多远后,我从柴火堆里爬了出来,正想走,奶奶忽然转过身,看见了我,急忙叫了起来:“小祖宗,原来你藏在这里呀?”说着就朝我追了过来。
我终于被奶奶抓住了。我知道,只要被奶奶捉住,就逃不过被她按在水里的“厄运”,罗爷爷自然会有办法让我像小绵羊一样听话的。
果然,罗爷爷一看见我,就向我伸出一只手掌,手掌上摊着一枚亮晶晶的一角钱的硬币,对我说:“你从我手里把这枚硬币拿到了,它就归你,怎么样?”
我看着他那宽大的手掌和粗硬的指节,有些犹豫,但又禁不住那枚闪闪发光的硬币的诱惑。犹豫了一阵,终于下定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猛地向他手掌扑了过去。可还没等我靠近他,他以更快的速度,五根看似粗硬的指头往掌心一攥,就把硬币握住了。看见我泄气的样子,他又把拳头伸向我:“你把我手指掰开了,它就归你!”
我迟疑着不肯上前。他又突然伸开手指,把那枚硬币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待我正准备去抢时,他又把手指并拢了。我于是就去掰他的手指,一只手不行,就用两只手。我的脸憋成了一只红苹果。可不管我怎么用力,那手指像是互相焊住了一般,怎么也不动。我失望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时,他的手指忽然张开了,把那枚硬币递到我面前,另一只手摸着我头说:“小崽儿,你还早,还要吃几年糙米干饭呢!来来来,你把发理了,我就把这钱给你!你马上就要上学了,把发理了才像洋学生嘛!”
为了得到那枚一毛钱的硬币,那天中午,我又一次做了老剃头佬的俘虏,乖乖地坐在了那条他剃头的凳子上。他给我理了一个平头,理完后,罗爷爷又左右端详了一遍他的作品,然后自豪地说:“看看,扬扬现在多精神,这才像进学堂的样子嘛!”说完后,果真掏出了那枚硬币,交给了我。我高兴极了,接过那枚硬币,一溜烟跑了。
第二天,爷爷就把一只书包挂在我肩头,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正式读书了,在学校里可要听小梅姐的话!”
小梅姐高中毕业了,差五分考上大学。小梅姐坚持要复习一年,说再复读一年一定能考上。可大妈坚决不干,说:“已经供你读十多年书了,也差不多了!是你自己不争气,怪得我们吗?”小梅姐又给大爸写信,大爸在信里和大妈观点一致,还说:“年纪这么大了,还读什么书?要是换了别人家,早就让你出来打工挣钱了!”小梅姐流着眼泪来找爷爷,爷爷说:“孙女,你父母都不让你读书,找爷爷又有什么办法?爷爷要是有能力变出钱来,就让你去读了!”说完,停了一会,爷爷又说:“也不要怪你爹妈心狠,你家修房子的老账还没还清,你爹又是满五十的人了,还在外面下得到多少年苦力?就是复读把你供起了,你读大学又哪来的钱?人争命不争,梅梅,听爷爷的话,认命吧!”小梅姐回去痛哭了两个晚上,就认命了。正好村小学一个女老师要生小孩,学校领导就让小梅姐去代一个学期的课,就教我们。有小梅姐做我的老师,我当然高兴了。
爷爷对我叮嘱完后,又对堂哥说:“勇勇你是哥哥,都读三年级了,你可要照顾好弟弟,听见没有?”
堂哥看了我一眼,没吭声,挎起书包一个人就走了。爷爷在后面说:“看看,叫你照顾弟弟,你就一个人走了,回来!”
可堂哥没有回来。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堂哥年龄越大,性格越怪。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也不爱和大伙儿一块玩,有时还爱一个人在一旁发呆,像装着什么心事。爷爷问他想什么,他也不答,问急了,就一个人跑到自己那间小屋里,关上门,连堂妹喊他都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