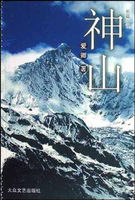这时,谢芹心里突然蹦出个想法,就拿过酒瓶,要敬那女人。那女人经不住几个人一再怂恿,就跟谢芹对掐起来。谢芹就一连和她干了三杯,早把那女人醉得颠三倒四了,谢芹自己也醉得糊里糊涂。就听那女人大声说,我要上厕所!老娘要屙尿!干呕了两下,却又嚷了这么一句,后果很严重!
那眼镜儿就要去扶她,她却一把甩开,嘴上说,哪个要你扶,老娘自己会屙!就扶了墙壁,一路歪歪倒倒去了厕所。不一时,听得她在厕所里喊,给老娘拿个纸来!那眼镜儿便拿了一叠餐巾纸,歪歪斜斜去了厕所。却又听女人喊道,哪个要你拿?叫唐明富拿!曾宪就朝唐局长笑道,人家要你拿的纸才肯擦呢,你还不去?唐明富也早是个醉鬼了,就说,拿就拿,我怕个!就拿了纸往厕所去。
谢芹已醉得迷糊了,像是不断往一个黑窟窿里坠,竟有些看不懂眼前的事,歪在椅子上,觉得自己像是一滩泥。不一时,觉得有人把这滩泥捧了起来,一路出来,到了一个光亮的地方,睁眼一看,搂着自己的竟是那眼镜儿,心里一紧,要把他推开,却没有一点力气。那眼镜儿似乎更有些大胆了,竟把一只手牢牢把在她腰臀上。这时,听得曾宪骂了一句,把那眼镜儿一把拽开,扶着谢芹一路搅缠着往外走。谢芹觉得,自己是斜挂在他身上的一个大包袱,忍不住想笑。到了大堂,一下歪在沙发上。又听有人对服务安排了一阵,就有人过来,要把他们弄到一栋别墅去休息。曾宪却死死抓住谢芹不放,嘴里说,你们要干啥,这是老子的女人!
折腾了好一阵,才到了那栋别墅。
不知睡了多久,谢芹被一阵隐忍不住的叫声惊醒。曾宪早已醒了,正紧紧搂住自己,这才发现,自己是被脱光了的。就伸手去推曾宪,曾宪却一脸的绿,像是要杀人一样。谢芹故意气道,你去找那婆娘嘛,我看你骨头都酥了呢。
曾宪哼了一声说,她是个啥东西,她要来,老子一脚把尻子给她踢成八瓣!又听得那叫声更为确切,谢芹还有些犯迷糊,就问,是哪个咋的了?曾宪笑了笑说,是唐明富在弄那婆娘呢!谢芹一愣,旋即骂道,你们都是些畜牲!曾宪却不管,一翻身爬上来。谢芹就用手在他背上乱抓,嘴里不停地骂曾宪。骂着骂着,眼前慢慢浮出另一个人的影子,就是那个曾经的房客,那个不知去向的李南。似乎就听见了雪花飞舞的声音,听见了梅花落地的声音。这声音像水一样渐渐淹没了自己,淹没了整个世界。
离开梅园时,天已黑透,雪还在下。两束雪亮的灯光里,有一缕缕热气隐隐约约升腾着。一路上,谢芹一言不发,觉得心里很乱,像淤了一滩烂泥。曾宪就说,你猜他们给你送了啥?谢芹说,我又不是他们的领导,送啥我都不要。曾宪大声笑道,你今天是处长夫人呢,人家是见你来了,专门去买的呢!都搁在后尾厢里,是一件貂皮短袄、一块伯爵女表,加起来近十万呢!谢芹吓得都面如土色了,就觉得那两样几乎从未听说过的东西是镣铐、是枷锁,更是个阴谋!莫名其妙竟跟自己扯到一起,早乱了方寸。
又听曾宪说,还有五万块拜年钱,等会儿你都带回去。谢芹还是一言不发。曾宪又说,我怕是给你五十万了吧?我心爱的女人都是个小富婆了,你还要给那个姓尹的瓜娃子当服务员,我搞不懂你。谢芹依旧不理他,去看窗外,车子正在城郊结合部行驶,外面是一大片被人圈了,却一直闲着的空地,黑黢黢的,像一个陷阱,便觉得背心里一阵清寒,不觉打了一个冷颤。
到了玉石街口,谢芹要先下车,曾宪就去打开后尾厢,要她把东西都拿回去。谢芹却像躲瘟疫一样匆匆走了。气得曾宪忍不住在后边骂,你妈的,钱跟你有仇呀?!看见街灯里,女人的身影被纷纷而下的雪花一层层围了,突然觉得有一种隔离感,那女人仿佛行走在另一个世界里,跟自己从没有过任何关系。曾宪把手里的东西重又放回到后尾箱,地一声关上盖子,嘴里不禁抱怨道,老子咋就搞不懂你呢?每次给你钱,就跟他妈要你的奶奶吃样!是不是有意给老子装清高?这世上真有不爱钱的人?老子不信!这样骂了,心里却无端觉得很虚,似乎是裹了一身秽物,偏要往清水池里去,不觉得自己脏都不行。那你是不是那池里的清水?你能把我洗干净吗?
倏忽间,已是旧岁将残。
那雪却下得更为密集,一场连一场,好像永远不会晴了。第一场雪带给成都人的惊喜和愉悦早已消磨殆尽。成都似乎在这一场接一场的雪里,已经彻底迷失。不觉间,已丢了那份自古皆然的从容和淡定。那迷茫无尽的风雪里,藏着成都人从未有过的焦虑和惊诧,都说从来没见过这阵势。直到不断有南方雪灾的种种消息传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囊括了整个南方的罕见的雪灾,成都人似乎才勉强愿意接受了这个被雪层层覆盖的严冬。
尹老三的茶铺一连好些天都打了白板儿[76],没有一个人上门来喝茶,却又不能关了张等过年,凭白无故关门歇业是个忌讳,只好天天来这里耗。好在不是第一遭过冬,心里并不十分焦躁。何况眼看就要过年了,大庙会就要开张,等那场热闹过后,也该开春了。成都的春天来得绝早,一过完年,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就会冒出一片一片的花色来,觉得像是坐跷脚席一样,只等冬天一跷脚离席,春天就会一屁股霸拦了那位置,并且长期不走。
这段日子,尹老三、谢芹、毕慧和那看游船的小伙子,几乎天天都在茶铺里打麻将,早打得腻了,却又找不到别的啥来消磨。
尹老三今天来得最晚,一路堵车。成都人没见过这一路的冰溜子,开车的都找不到感觉,到处都有追尾的或碰头的。等他进了茶铺,谢芹、毕慧和那小伙子早候在麻将桌边了,单等他一人来。毕慧说,我当你不来了呢,我们都打算散伙了。尹老三拍了拍身上的雪花,嘴里骂道,他妈的,这一路上都有人撞车,老子刚出门就差点儿遭一个婆娘弄了我尻子,要不是老子手脚利索,早叫她龟婆娘把我屁股搞烂了!
几个人笑闹了一阵。毕慧大声道,光说你那屁事干啥,还不来打牌,这都耽误老半天了!尹老三看了眼桌上早已摆好的麻将说,老子不想打了,你们日妈一个个饿里饿虾的,都按到老子合牌,伙到一起来,把老子当毛子烫!走到墙边去翻了翻挂历,又说,噫,又是星期五了,要放到平时,今天该柳豁子来说相书,也不晓得那老东西过不过得了这个冬天?
毕慧就说,你个两面三刀的东西,当面喊人家柳老师,喊得巴心巴肠,背后却叫人家柳豁子,人家比你爹都大一辈,你喊人家一声柳爷爷也是该的嘛!尹老三笑道,我要真喊他一声柳爷爷,他还要跟我急呢!那老家伙是个人老心不老的怪物,你没见他每回来这里,一双眼睛老在你们两个身上转,恨不得把你们都搂到他那布笼子里搞好事呢!
毕慧伸手在尹老三肩头打了一下,嘴里笑骂道,你妹子才跟他搞好事呢!要说,那双老色眼也是照准谢姐身上瞅的嘛,哪里看过我?
谢芹忙说,你两个烧香磕头要找准庙门,莫把赃水往我身上泼,我惹不起你们。说笑了一阵,谢芹不禁感叹说,人家柳映楼那相书说得真算是一绝,学啥像啥,只可惜没带出一个徒弟来。毕慧一拍手说,尹老三,你何不把那姓柳的请来给我们说一场相书?往回他来,我们要给那些茶客添茶倒水,忙这忙那,就没有听过一回完整的。你要够意思,你把他请来,说一回给我们听。尹老三竟有些心动,脑子里一转,说,那干脆这样,我去请他,你们去买点儿吃的回来,先弄好,就算是一起团年了,如何?毕慧却不干,说,你狗日也算得太精了,就想这么简简单单把我们打发了?
尹老三说,你们不干算了,反正牌我是不打,我们就在这里干坐。
几个人只好答应下来。尹老三就叫毕慧去买一只鸡回来,再买几样外卖。毕慧大声道,你不是说团年吗,你打发讨口子呀?何不到外面去订一桌菜,叫他送过来也就是了,好不简单的事,哪里用得着在这么个旮旯里弄得尻子抵尻子?尹老三无奈,只好答应下来。一边叫谢芹去订菜,一边要毕慧跟他一起去请柳映楼。
尹老三带上毕慧,到了一处小巷,是清一色的旧门楼,两行枯柳依依排开,跟那些旧门旧院相映成趣。这景象虽跟眼下的成都有些隔,却暗含了几分倔犟。尹老三在一处似被火烧过的黑黢黢的大门口停下来,给柳映楼家里打电话。毕慧忍不住说,成都居然还有这号地方啊!
大约过了一刻钟,那门总算开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探出头来。尹老三赶忙从车上下来,喊了一声柳老师。便上去说了一阵话,柳映楼却又进去了。尹老三回到车上来,笑着说,老东西还没洗脸呢。说着,竟把一双手伸到毕慧两腿间,要她暖一暖,又只顾在里面不停地乱摸。毕慧骂道,你这么怕冷,早晓得你就赖在你妈肚子里莫出来嘛。尹老三笑道,那我干脆钻到你肚子里去。
就把头埋下去要钻。毕慧骂道,你个狗日的下流东西!
正说笑着,柳映楼出来了,手里拿了一只装行头的大帆布箱。尹老三赶紧下去把那箱子接过来,放进后尾箱里。
坐在车里的柳映楼像个不会说话的老木偶,一声不吭。等车子开出了小巷,柳映楼却说,干脆去把裴瞎子两口子也喊上。尹老三只好依了他,又顺着柳映楼的指点,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乱糟糟的大院里。柳映楼叫尹老三和毕慧在下面等,自己上楼去喊。两个人在楼下,等足了一顿饭工夫,柳映楼才和裴瞎子两口子出来。走在后面的是裴瞎子的老伴,叫李幺妹。一上车,柳映楼像是一截逢春的枯木,突然活过来了,满嘴的笑话,大都是围绕李幺妹儿说。
一路到了文化公园,早过了晌午时分,就挤在一张麻将桌上吃饭。不觉,外面又下起一天雪来。柳映楼笑道,今天我说个新段子,名叫李幺娘雪夜思情郎。说完,两眼瞅着李幺妹儿只顾笑。裴瞎子骂道,你那豁嘴就不能积点儿德,留到下一世免得说话漏风?柳映楼笑道,你怕啥,你还不晓得呀,我一辈子都只是个过嘴瘾的主儿。两人就好一阵笑骂。
几个人就忙手忙脚把桌子撤了,帮着柳映楼把摊子扯开。那柳映楼看了一眼李幺妹儿,满面春风地钻进布笼子里去。
只过了片刻,听得从布笼子里传出一阵呜呜的风声,果然是寒意如水,铺天盖地一派雪花乱舞的阵势。等到风声渐歇,又响起一片淅沥之声,若远若近,似有似无,真是雪花落地的那种轻响。却又传出一串鹊鸣,叽叽喳喳,乱作一团,明明是几只喜鹊正乱纷纷争一树梅花。这时,一个嫩闪闪的女人腔念出一首诗来:
听得喜鹊闹梅花
春风吹破旧年华
满天白雪纷纷下
叫人心里乱如麻
一声娇滴滴的嗟叹过了,又听那女声念道:奴家本姓李,是城南李布客家的幺女,都叫我李幺妹儿。嫁在本城小户人家。无奈那冤家视钱如命,一年在外贩牛贩马,抛下我年纪轻轻一个红颜小娘,守住这孤灯瞎火,好不凄凉!弄得我满腹情丝无处可吐,只可怜夜夜抱住个空枕头!幸喜东边街上有个张姓郎君,生得面如满月,松柏一般高挺的身子,心里对我有意。那本是我可心可意的人儿,可恨那死短命的媒婆子走错了家门,才嫁给了这个薄情寡义的东西。没想到有天下午,那姓张的小哥打从我门前经过,把一个胀鼓鼓的钱包失手掉在了门口。我连忙跑到门外朝他喊,张哥,你钱包落到这里了!
这时,听得一个男人回道,放到你那里就是了,我改天有空来拿!
又换作那个女声,你说这是啥意思嘛,自己钱包掉了都不急着回来拿,要放在我这里,这明明是有意的嘛。待我看看这钱包里装了些啥。听得吱地一声拉链响,那李幺娘又说,还夹了一张纸条呢,我看看写的啥?李幺娘,你要是拣到这钱包就帮我收好,三天后的晚上我再来取。要是老天有意就下一场雪下来,要是老天不允就亮出一片月光来。哎呀,你看他是不是有意的嘛,要不,他咋提前晓得要把钱包掉在我家门口?哎哟,好羞人哟!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整整一天都是亮晃晃的太阳,哪有个要下雪的影子?这是老天不允呢!看来我和他是有缘无分了,我是空等了这几天了。哎,好不容易碰上个两下都有意的人,偏偏老天又不可怜!你说那姓张的也太跟自己过不去了,那老天咋会为你两个的私情专门下一场雪来?嗨,哪知道还不到傍晚,那明亮亮的天眼瞅着说变就变,一眨眼的工夫,真就乱纷纷下起雪了!我两个的缘分果真是天定的呢!那我要先化一化妆,再换一身好衣裳,要他看见一个光鲜鲜、亮闪闪的李幺娘。
就听见一阵开箱取物的响声。李幺娘又自顾说:
画两道细眉如烟柳
画一张粉面似桃红
画一点朱唇如樱桃
画出个妙人儿
犹如那牡丹笑春风
外边,尹老三不禁看了眼已是残荷一般的李幺妹儿,却看见那一脸的皱纹里竟似填满了春色,像是被水打湿了一般,显得格外滋润。裴瞎子似乎满脸的危机,正伸手去抓她的手,却被她轻轻一扭挣开了。裴瞎子轻声骂了句,狗日豁子,今天我非把他灌躺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