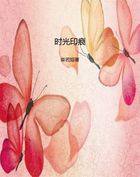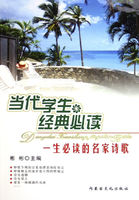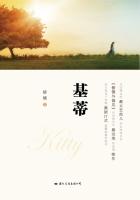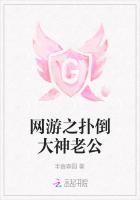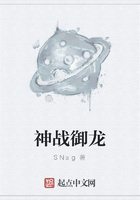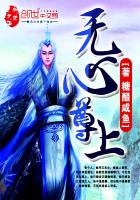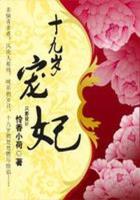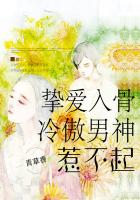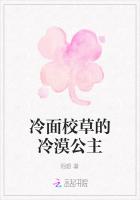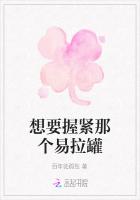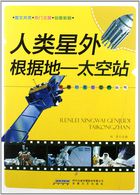十年前,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展览:一群美丽窈窕的女模特,被关在一间华丽的、流金溢彩的大厅里,她们集体赤裸着,一丝不挂,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超高的、时尚的高跟鞋。摄像机的镜头,暗中监视着她们,就像一双偷窥者的眼睛。起初,高跟鞋使这成百上千名裸女保持了习惯性的优雅姿态,T型台上的那种姿态,挺拔、傲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站累了的双脚开始觉醒反抗,开始试图挣脱高跟鞋的桎梏,开始放纵自己的身体,开始用各种不雅的、近乎隐私的姿势让身体尽可能自由自在地松弛、懈怠,于是,高跟鞋这件寻常的东西变得诡异,而它存在的意义则被解构了。
或许,是更加凸显了出来。
我忘不了这景象带给我的震撼。我问自己,高跟鞋是什么?我不能确定创作者的真正意图,但,它确实让我看到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里所隐藏的秘密,以及,令人警醒的暗示,那就是,任何一样貌似美丽的东西都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它们使“自由”陷落。至少,在这里,我以为,高跟鞋隐喻了枷锁——物质和欲望的枷锁。它在某种意义上锁住了我们的肉身以及精神。
绿色生活这个词,首先,使我想到的是“田园”。在中国文学中,或者,在中国文化中,田园,是中国文人最后的归宿或者人生的理想。“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戴月荷锄归”或者“采菊东篱下”的诗意生活,更是一种对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种对心灵的解放,让心灵从物欲的压迫下自由挣脱,我以为,是任何时代、任何空间,所谓“绿色生活”的真正内涵和灵魂。
所有人都知道那句话,所有人都喜欢引用那句话:“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其实,这句海德格尔的名言出自何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句话如今早已被“小资”们庸俗化成为某种情调、腔调的代言。而海子用他年轻天才的生命,在令他绝望的大地上书写的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成为了房地产商高端楼盘的广告。不错,在属于我们的时代,在今天,拥有一个真实的田园,拥有竹林、菊花,拥有夕阳下的虫鸣鸟唱,早已是生活在钢筋与混凝土森林之中、为一小套“蜗居”而终生沦为“房奴”的人群的一种奢侈的梦想。被高大的建筑物、泛滥的物质和千人一面的“标准化”挤压着、塑造着的现代人,拥有一个精神的田园就显得尤为珍贵。
几年前,我丈夫去日本访问归来,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黄昏时分,他和一个朋友在大阪的街头闲逛,无意中闯进了一条叫做“法善寺横丁”的小巷。不用说,那小巷,因“法善寺”而得名,但此刻,时间已是傍晚,来寺庙旅游的观光客散去了,幽深的小巷终于回到了日常生活的宁静之中。苍茫暮色里,只见路边一尊石佛前,安静地排着一队小长龙。一望而知,他们应该都是本土的居民:老人、孩子、妇女,还有拎着皮包刚刚下班的白领职员。他们安静从容地排在那里,等待着完成一个仪式:每一个人,走上前,从一只大木桶里,舀一瓢清水,虔敬地浇在石佛的头上,然后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无数的人,无数瓢清水,无数个这样的夕阳西下的黄昏,那石头的佛像,竟不可思议地长出了碧绿的青草,变成了一尊被茂密的青草覆盖的草佛!石头开花的奇迹就这样出现在我丈夫眼前,这个外乡人的心里慢慢升起了一种感动,为这种对生活的珍惜和古老的尊敬。他说他在那一刻看见了日本的隐私,看见了近乎永恒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执著与祈盼。这份执著的力量足以让冰冷的石头盛开鲜花。
我也很感动,为这尊开花的有生命的草佛。
我想,写作,对于我,就是一种在精神上努力甩掉“高跟鞋”、努力挣脱桎梏和枷锁的自觉,飞翔的自觉,我认为这是“绿色生活”的前提,无论这桎梏和枷锁叫做“贪婪的欲望”、“物质暴力”,还是别的什么。我希望用自由的写作来完成这样一个仪式,一个过程,就像用一瓢一瓢的清水,浇洒石头,一瓢一瓢,一下一下,年深日久,看它慢慢慢慢被青草覆盖,慢慢慢慢变成一尊夕阳下生机无限的草佛。这是我藏在心里的田园,也是我绿色生活的归宿。
曾经,受某个“行为艺术”的启发,我忽发奇想,想在此生完成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走遍中国大地,随便在任意一个城市或者乡村,任意一个街头或者村寨,任意一个小巷、港口、码头,随便拦住任何一个陌生的行人,一个老人、孩子、少女或者青年,请他或她读一段我手中的《红楼梦》。用各自不同的声音,苍老的或者青葱鲜嫩的,颤抖的或者蓝天般明快的,用各自不同的方言,南方的或者北方的,海边的或者高原之上的,从第一回第一行开始,接龙阅读,可以是一句,可以是一段,一直读完百二十回。我用录音设备将这些声音珍藏起来,这些朴素的、天然的、绿色的声音,然后,我这样为它命名——中国好声音!这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一个漫长的仪式,就像用一瓢一瓢清水,浇灌石头,但,我有耐心,因为,我相信奇迹。
是,人应该诗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