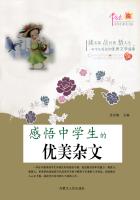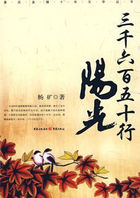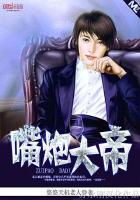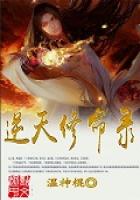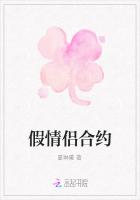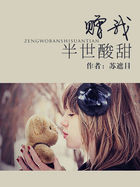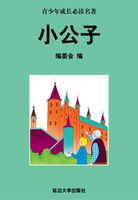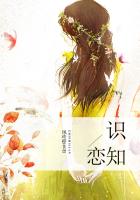非常荣幸,能够来苏大“小说家讲坛”和大家交流,因为我知道,在我之前,来这个讲坛的都是一些著名的文学人物,可能只有我是个例外。我曾经和王尧先生,还有林建法先生开玩笑,说,你们怎么只请李锐不请我啊?结果我来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受邀是不是因为这个呼吁“平等”的激将法的缘故,当然,但愿不是。
我这么说,并不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说,在今天还有实力远逊于名声、名气的作家、艺术家的话,那么,我肯定应该算一个。有人说,在今天,在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凡·高那样的悲剧不会重演了。河南有一个画家,叫李伯安,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他的画展震动中国甚至世界,被人称为天才。当然,我不是天才,更不愿意马上就死,所以,只好安于现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言归正传,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们正在失去什么》,这个话题是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不过至今没有答案。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其实是我的困惑,或者,说得严重一点,是我的痛苦。我不知道在座的年轻人、新新人类对这种古典的话题是否有兴趣,我女儿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妈妈,你知道吗,你不爱这个时代。当时我很震惊,我震惊她的一针见血。我想这可能也是我和在座各位的最大区别:我确实不怎么爱这个属于你们的时代,至少,我对它充满矛盾之情。
一、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
我想先从古根海姆谈起。
古根海姆美术馆和美国现代艺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名字。且不说它的藏品,就那座建筑本身,一诞生、一落成就曾经让世界震惊和震撼。惊世骇俗的事物,从来就是有人激烈抨击,有人热情赞美。我们知道卡尔维诺就是极力称赞和赞美的一个。卡尔维诺对古根海姆的赞美几乎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们对现代艺术的那份崇敬也几乎可以用顶礼膜拜这个词来形容。只不过,对我来说,和古根海姆的相遇,晚了将近二十年。2002年冬天,当我终于来到了古根海姆时,我想我的震惊大概也不亚于当年的卡尔维诺,只不过,我震惊的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人类对于自己的表达会如此苍白贫乏。在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建筑空间里,“想象”这种奇妙的能力正在退出人类世界。这种感觉,是我看完了正在那里举办的一个大型艺术展之后引发出来的,那个展览,似乎是关于人对于自己的重新发现这样一个主题,也就是身份识别和认同。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具有巨大挑战性的主题,是一个无限丰富的领域,可是,我看到的却是,毫无新意、似曾相识、众口一词的表达:无非是把“人”解构成肢体和器官,以后现代的名义,建构起一个肢体和器官的霸权,欲望的霸权。或者说,在人的身体上作尽文章,可最终却是让人感觉到,“人”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去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人”的灵魂和情感、精神和思想,甚至,人的身体。人正在用不容分说前所未有的暴力将人自身驱逐出这个世界。
那天我非常悲哀。我没有想到古根海姆会让我如此困惑和失望。那天,纽约下着小雨,我特别想哭。雨中我们走进了“惠特尼”,我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我以前从不知道的画家,爱德华·霍普,我看到了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许,更早一些的几幅画作,我被触动了:他笔下的夕阳、小镇、铁路、南加州明亮的早晨、慵懒丰满的女人,是正在“失去”的东西,他把“流逝”的瞬间和过程给呈现了出来,他画出了冷峻的失去,有一种怪诞感,却非常动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误读了他,反正,他深深感动了我,就算是误读,也是我需要的。
“失去”其实一直是我小说的主题和意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小说中已经出现了那种被放逐到了时代之外的人物,出现了那种生活中的“外乡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前苏联的影片,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叫做《苦恼的女人》,这个影片中的女主角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她就是一个和急功近利的时代格格不入,固执地生活在时代之外,固执地想走回精神家乡的悲剧式人物。这个女人的精神气质后来成为我小说的底色,也决定了我小说的命运——八十年代是一个大时代,而接踵而来的九十年代是一个彻底的物质和欲望的年代,抛弃一切理想、道义和浪漫的年代,我的小说无论是对大时代而言,还是对一个欲望的年代而言,都是格格不入和异己的。我想这也是我不在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之中的重要的原因吧!
二、属于我们的是什么?
还是要说到美国之行。从美国回来,有一些改变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比如,从前,那些无法进入我创作视野中的东西,如今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魅力,像《在传说中》《想象一个歌手》,特别是《在传说中》,假如在几年前,这种民间传说之类的东西,是绝对被我忽视的,因为我从不知道,也没想过它们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作家成一曾经把那些有模仿痕迹的文学作品称作“副本文学”,遗憾的是,新时期以来,许多引起反响被批评界所关注的,常常是这种“副本的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正本”的存在,批评家似乎就会失语。这种状况其实不仅仅存在于文学界。2002年秋冬,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人一共有六名,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这六个人中,除了李锐和我是写小说的之外,还有诗人西川、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编剧廖一梅,以及雕塑家姜杰,这次经历对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即使是在国内,也很难让这样一群从事不同行当的艺术家聚在一起,就算聚在一起,也根本没有了那种能够就一个严肃的话题深谈下去的纯净的氛围。那段时期,我好像又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艺术复兴的黄金时代。我们六个人,几乎天天晚上,聚在聂华苓老师的家里——建在山坡上的鹿园,谈话、讨论、争论,一谈就谈至深夜甚至黎明。我们这几个人,虽然从事的行当不同,可是大家发现,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困惑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怎么样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怎么样表达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的处境和情感——这种严肃和激情,是我久违了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怀念那些留在鹿园的美好的夜晚。
孟京辉把一些类型化的作品称作“摸脉”之作,这样的作品,无论是电影还是美术,真是太多太多,这样的处境,也不仅仅是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所需要面对的。记得西川第一次从纽约回来,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到了纽约之后,你会发现,纽约好像是一个大批发商店,全世界的艺术家要做的,好像就是从纽约把东西批发回去零售。面对全球语境中的英语强势,每一个非英语国家的作家、艺术家,其实都有一个怎么样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的严峻现实。
就拿“身份认同”来说,这个话题很大,是一个理论的问题。“理论”从来都是我的盲点,所以,在这里,我要说的不是“身份认同”的理论,而是我看到的现状。大概是2003年,奥斯卡把它的最佳动画片奖给了日本的宫崎骏,这是奥斯卡第一次把这个奖项给外国人。后来我看了他获奖的影片,《千与千寻》,我有点明白他为什么获奖了。《千与千寻》讲的其实也是一个身份识别、身份认同的主题,这是一个公共的语言,是一个美国人听得懂并感兴趣的语言。只要贴上“身份认同”这个标签,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行无阻的“护照”。虽然宫崎骏的动画形象很东方,可我觉得他只是使用了“东方的元素”讲了一个西方的故事。这样的例子几乎举不胜举,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叫《看阿仙》,就是讲我在纽约看到的一个展览,阿仙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后来到了澳大利亚,我们在纽约无意中撞见了他的个展。他用陶瓷烧出了一尊尊人像,大多是半身,也有全身,这些人像毫无表情,秃头、面目不清,甚至不辨男女,可是裸着的身上,却布满极其鲜艳、艳丽无比的图案,那都是最经典的中国瓷器上的图案,或是青花或是粉彩的中国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他把经典的古老的瓷器上的图案移植到了人体上,看上去又怪诞又奇异,给人感觉十分强烈。看得出,这位艺术家是有想法的,只是我觉得,这种过分符号化的表达仍然显得简单了一些,仍然有贴标签的嫌疑。
那段日子,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必然讨论或者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我们不要贴标签式的表达,那么,我们要什么?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争论会对我的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回来后,2003年春节,我很偶然地听我多年不见的姑姑讲了几个关于我家乡开封的传说,虽然只是几个小片段,但是我突然很兴奋,从前,这一类的故事,也不知听人讲过多少,但从来没有让我这么兴奋过,我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见那两个和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的可爱的小泥胎。春节过后我就写了《在传说中》。后来,我和李锐到北京,又见到了京辉、一梅他们,他们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写了一个中篇。然后,我说,假如我不去美国,我大概不会写这个中篇。孟京辉当时问我,为什么?还真把我问住了。我想了一想,告诉他,因为美国没有鬼。
当然,好莱坞也许有一些讲吸血鬼的电影,但我觉得,那不是我们文化中的鬼,它是能够从生活中剥离出去的东西。而我们的文化则不同,中国的孩子,当然,是到我们为止的孩子们,哪一个人不是听着鬼故事长大?在我们的童年经验里,“鬼”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特别的记忆。我记得莫言写过一篇文章,非常动人,他说有一天晚上赶夜路过河,一群小红孩儿从水里钻出来,说:“过不去过不去。”一直到天亮小红孩儿才消失。后来李锐告诉我,他说,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他的《美国与美国人》中,说过这个结论:美国没有鬼。他把书找出来给我看,果然,费孝通先生从理论的层次、从社会学的层次阐述了这一见解,比我说得透彻多了,他说:“我总觉得他们的认取传统,多少是出于有意的,理智的,和做出来的。这和我们不同。我所以这样感觉的理由,因为我发觉美国人是没有鬼的。传统成为具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神圣,成为可怕可爱的时候,它变成了鬼。”他还说:“生命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他把过去变成现在,不,是在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成为一串不灭的,层层推出的情景——三度一体,这就是鬼,就是我不但不怕,而且开始渴求的对象。”他甚至说:“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
同学们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写鬼、表现鬼,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独特的表达。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我要说的是一种清醒和自觉,是意识到强势话语对我们文化中有魅力的东西的遮蔽。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或者,比我们更大一些的人,已经是和传统断裂的一代了。我们对于传统点点滴滴的接受不是来自庙堂而是来自民间:比如鬼故事,比如我奶奶告诉我的关于过年的种种禁忌和习俗。现在,连这些也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我不知道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还能挽留住什么?难道我们只剩下那些作为旅游资本的伪民俗了吗?想到这些常常就感到很悲哀,觉得自己好像承受着旷世的孤独。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于西方的借鉴,是非常自觉和积极的,几乎是一种全盘的输入,但对于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资源,则是漠视的。八十年代,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一说我们自己的文学资源,以为就是章回体,就是白描。那时我们觉得无论是章回体还是白描都根本无法表达现代人复杂的情感。这就是我们当初抛弃它的合法理由。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其实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从审美的意义上看,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中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什么,或者说,它对世界最具独特性的贡献是什么?
有时候我瞎琢磨,我想,从文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学对世界最独特的贡献在哪里呢?我这样想:不是关于苦难的表达,表达人类的苦难和苦难感,俄罗斯作家达到了极致,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是关于爱情的表达,表达爱情,全世界有很多的经典,或许,法国作家将它推向了极致,比如雨果。那么,属于我们的最独特的贡献是什么呢?我想,是乡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这一点,无论在中国的诗词、戏剧,还是小说比如《红楼梦》中,表达到了极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能像我们一样,将乡愁和生命悲情,高度意象化,象征化,成为整个民族灵魂的印记,这显然是无人可以企及的文学高峰。
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学在人类的精神史和情感史上的不可取代性吧。
但是有人问我,意思是说,这种古典的悲情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关系?我想是这样,在一个科技至上的时代,对于狂妄自大百无禁忌的现代人来说,这种生命悲情的提醒,无疑有着警世恒言的意义,那就是,我们是人,不是神,还有,在这种幻灭的伤痛中,其实有着对生命无穷尽的大爱。
《双城记》中开头那段话,用在对于今天对于当下的描述应该是很精彩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眼前应有尽有,我们眼前空空荡荡;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毋庸讳言,我们在获得的同时也在无可挽回的失去。作为我,正如我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固执的凭吊者,我凭吊那些失去和正在失去的美好与珍贵的东西,或者说,我记忆“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