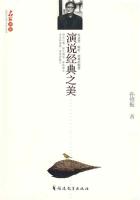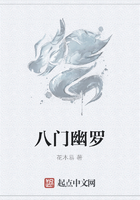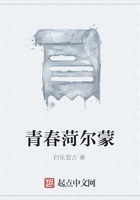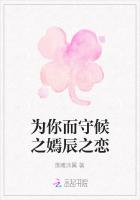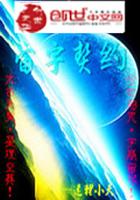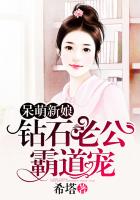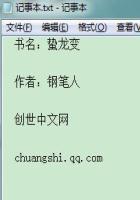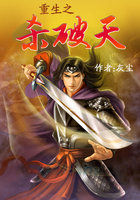读《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对我而言,像是在漫长黑夜中的绝望穿越。就像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跋涉在茫茫的大戈壁上,一望无际的石头,一望无际的黑,一望无际冷酷的死寂,天地都被这黑笼盖,只有一颗泪滴似的星星,悬挂在天边,它清醒而孤独的光明,有一种牺牲的悲壮——我想,那是作者的眼睛。
想起雨果的一句话:人心比夜黑。
读完这部四十万字的大书,雨果这句话,就像一个咏叹,在我耳边,在我心里,不断回响,不断回响。
说它是部大书,当然不是因为它的字数,关于它的意义、它的独特、它进入历史的孤独而勇敢的姿态、它罕见的犀利与雄辩、它对时代、社会、政治、文化刀刀见血的批判与反思、它对灵魂以及“精神之父”的拷问、它对女性伦理的深度审视、它的史诗性追求,等等,足以构成这书的深沉厚重。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后新时期”重要的、严肃的、有心肝的大书。
在“职业化写作”日渐成为主流的今天,陈亚珍是这个时代罕见的视文学为信仰、视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为负有某种使命感的写作者。五年前,2008年,她曾在我的博客上给我留了一封公开信,遗憾的是,这封信,我一直到今年初夏时分才看到,其中缘故,不在这里赘述,只想说,当我读到这封信时心里有着很深的触动。亚珍这样说:
“写作是具有使命感的,仅仅是帮闲与帮忙不过是匠人而已,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大智大勇是一个作家有能力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人类提供建设性的远景,有勇气坚持反叛意识,发出正直的呼声。”说到女作家这一身份,亚珍这样说:“我以为这个身份是神圣的……”她告诫人们,“灵魂腐败将是全民的危机……所以,反叛勇敢的退化,反叛人性的腐败,反叛灵魂的堕落,应是我们的主张。起码是我个人的主张。否则,男女作家有何区别呢?我们是人类的母亲,没有母亲,既没有诗人,也没有科学家,更没有军事家、政治家。女性不是社会的附庸、男权的委身者,我甚至认为,我们应有能力,有勇气成为人类的教师……”此刻,当我阅读完手中亚珍的这部大著,我想,这部心血之作,应该是她为这理想所付出的严肃的文学实践。
我是这样来理解亚珍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亡灵”的视角:作为一个游荡的痛苦的灵魂,她漂泊无根,却也拥有着一种“俯瞰”的自由(从这书名我们似乎可看出这俯瞰的立场),就像那颗我想象中如同牺牲般的孤星,泪滴一样挂在天际,为我们烛照出那黑——人心的黑暗,人性的黑暗,堕落灵魂的黑暗。没有这颗星的烛照,你可能无法深刻地感知,那无边无际的黑是多么凶险、汹涌、恐怖、狰狞……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传统伦理意义上的北国乡村还是被时代洪流席卷的红色城镇,无论是面对当兵打仗保家卫国的故乡长辈还是面对情窦初开的爱情,在生前,这个原本有着“拯救者”色彩的亡灵无一例外都做了黑暗人性最无辜的牺牲。所以,她同时也是一个决绝的、悲愤和悲壮的“审判者”。在人的罪恶在人性的罪恶面前,或者,在终级审判缺席的人世间,我想,她无疑应该是作者的代言人:那是一种不惜以飞蛾扑火玉石俱焚的惨烈姿态坚持的正义审判。
这是一部勇敢者之书。
我在想,假如,让我来写这部小说,我或许会选择这样一句话来做我的题目,那就是,炊烟升起的地方让我心动。
这句话,出自亚珍这部大书的首页,它扑面给我带来了深沉的感动。从这句话中,我读到了悲悯。
在至深的苦难和最黑的人性的深渊中诞生的悲悯,永远有着令人最震撼的感动,属于灵魂的感动。也因此,它是至善也是至美,就像我永远仰望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仰望它,不是因为它的高不可攀,而是,它让我懂得了一点,那些使人沉入黑暗使人不幸使人悲惨或者卑鄙的人性的弱点、缺憾,我都有。那是我的宿命,或者说,是人类的、众生的宿命。
所以,当我如同孤独的夜行者穿越在这部大书中时,我情不自禁地在这书中,寻找一些最寻常最平凡也是辛酸的温暖,比如,就像那童谣:
窝窝窝窝你下来哇,
再蒸窝窝不搅糠,
玉茭面窝窝抿曲汤。
……
它们对人世的抚慰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