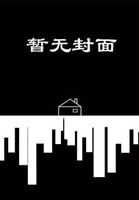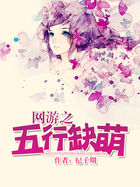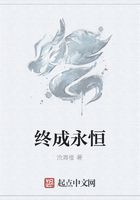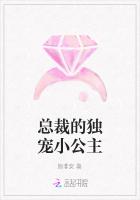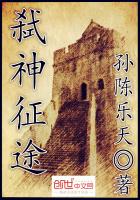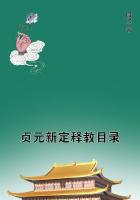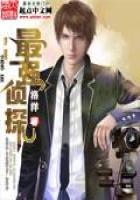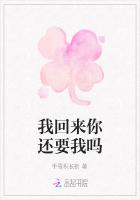黄裳
一
这是朋友F出给我的题目,已经好几年了。可是一直踌躇着不敢下笔。我感谢朋友对我的信任,可是自己知道要做好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没有把握。作为一个后辈,我对巴金的了解实在不多。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谈天,一位客人提出要我写点什么有关他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惶恐,就声明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我举出的理由是,巴金曾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可是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却非常贫乏,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不料他听了哈哈笑道,“你弄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懂”。这就使我更为尴尬。其实我只是想顺手找一个理由来推掉,并没有除此以外对他就有足够了解的意思。但他的话也给了我一种启示,即使如此,知道多少就谈多少,懂得什么就讲什么,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不过实在的困难也正在这里。有一部古书上讲过做文章的“秘诀”就在“趋”与“避”两个字。懂得了这一点天下就不再有难做的文章。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应该怎么说就跟着人家一起说,不该说或不能说的就避开不说。这正是一条写作的坦平大道。但是困难恰好在这里出现。应该说可以说的人家已经说了许多,用不着再来画蛇添足;不该说的呢旁人倒少有说及,但我真的就能很好地一一说出来么?看来一切都是可疑的。总之,没有勇气是不行的。
我确实相信,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作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读。我尝试过用这办法来从头读巴金的书,从近作开始。在阅读过程中自然会记起许多旧事、谈话。开始时是高兴的,以为到底摸到了门路,可是随即又感到了茫然。从纷繁的线索中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正如海边的居民,日日面对大海生活,对那一碧无垠的海水波浪与涛声都熟习、惯常了,但对大海本身却还是摸不透,还只是一个茫然。
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已经出版的四本《随想录》里,他在很多地方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也许是“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从第一篇《说“望乡”》开始,一直谈到第一百二十五篇,看来今后还要说下去。可以说他是从“文化大革命”还是个“禁区”时开始,一直说到彻底否定“文革”,……他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时,还常常接触到“文革”以前的许多事情。“老年人的唠叨”是讨人厌的,早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来了。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只将“文革”看作那荒谬绝伦的“十年”,总不免是过于天真的想法。正如我们站在长江大桥的中腰,俯视江水。遥望江天,无论是赏心悦目还是惊心骇目,以为“叹观止矣”,终于还是“短视”的。因为他忘记了怎样一步步走上桥头,也没有想到还得一步步走下桥去。前后的“引桥”比起桥身来好像还要长一些。对于这样的问题,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文学家、哲学家都不会作出不同的答案。
巴金最近在一篇“随想”里谈到了他与杂文家林放之间的交往,提到前两年林放因为写了一篇“江东子弟”的杂文随即接到了恐吓电话的事。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我们目前还在“引桥”上慢慢地往下走,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大写十三年”的故事也是《随想录》里曾经提到过的,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情,谁都看得出这个口号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是一个“信号”,可是不久前还有人站出来为之辩解,说口号还是正确的。在提出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三七开”的议论也重新搬了出来。与“江东子弟”的无头电话不同,这些议论都是堂皇地出现的,被看作一种“革命化”的内容出现的。这都不是梦话,是现实的生活。只有明白这一切,才能理解他“老人的唠叨”,才能明白,不是他揪住“文革”不放,实际上到今天“文革”还在揪人。
巴金是想认真弄清“文革”的来龙去脉,取得经验,使我们有可能不让这种“浩劫”再度发生。他为自己规定了几条,即使是身历其境、身受其害的人,如果不肯深挖自己的灵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十年浩劫”。他写《随想录》,就是在不断地挖掘自己的灵魂,挖得越深,越痛,也愈困难。“探索”的结果是说出了“真话”,同时也用实践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
巴金的自我解剖,并不只是个人的事业。在几册《随想录》前面都附有插图,是作者在不同时期留下的生活照片,有许多轻松地带着笑容,也有一两幅是在沉默思索。就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说明这几年的路并不是平静地走过来的,解剖自己也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科研工作。他为《序跋集》写的序文中有一节描写“风”的话,我觉得写得好。他写出了某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写法是隐喻性的,这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写出真实来的文学方法。他说,当风开始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人朝着一个方向跑,或者挤成一堆,才知道刮起风来了。”“大块噫气”是自然界的风,在社会上,伴随着风起来的则是各种样式的叽叽喳喳,也正是这叽叽喳喳造成了风的声势。这就使人们记起了才过去不久的十年以及十年以前的岁月。人们在这种刮风的季节里过得够久了,积累了经验也留下了后遗症。巴金说他过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很怕风,但终于见了世面,而且活了下来,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断言从此不怕风,“不过我也绝不是笔记小说里那种随风飘荡的游魂”。
这些话说得很沉痛也很坚决。使我联想起曾经议论过一阵子的“看破红尘”。人们在曾经沧海之后是很容易“看破红尘”的。不过看破以后却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可走,有人到深山里学道去了,有人却更勇敢地向红尘里大踏步走去。同样是“看破”,但结论却不同。
巴金多次说过,不少人劝他关起门来安度晚年,不要再写文章,再说话,享受由“相安”取得的好处。可是这办不到,即使每天只能艰难地写一两百个字。而且字越写越小,可是怎样也不肯放下笔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啊!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他在西湖边上住了一段日子。虽然行动不便,不能有太多的活动,更多的时间只是留在旅馆的房间里,可是看得出他的精神是松弛下来了,飓风已经过去,天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他还到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去过一次,他有一张百草园中的照相,拄着杖的老人脸上浮出的是欣快的笑。在游禹陵时,他还拖着病腿挣扎着爬到树有“大禹陵”的碑亭前面。这是几年来难得的一段平静舒心的日子。可就在杭州的旅馆里又吹来了风,接着就是隐隐的雷声。一场大风暴眼看着就要起来了。
在以后他住院的日子里,我有时候去看他,也只是随意说笑,并没有谁谈起那阵风暴,可是风暴时时压在心头,摆脱不掉,因此连谈笑也带上了勉强的性质。风暴来得很快,去得并不爽利,决没有自然界雨过天晴那样干脆。
有一天正在他的病房里坐着,有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问答以后,大人物说,“我看你还是好好的休息,以后不要再写了。”说完就告辞出去,仿佛特来看病,就是为了说出这两句“忠告”似的。
这是我碰巧遇上的一次,他当然还受到过别的人的“忠告”,总之不外是希望他“安度晚年”的意思。而这一点,他也早在“随想”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二
《寒夜》上演很久了。影片是在重庆拍摄的,故事主要在一所楼房里进行,这本来应该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在的那座楼房,可是原址已经没有了,导演在“水巷子”里找到了近似的场景。那可是另外一处地方。风格、情调与民国路完全不同的地方。
不过影片的效果还是好的,仿佛使我又回到了抗战中的重庆。民国路是一条热闹的马路,前街就是繁华的大道;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看见许多小吃摊子,担担面、抄手……一副担子就是一个单位,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街道两侧,使路面都显得狭窄了。在摊子的背后有冷酒馆,当时重庆,还有桂林……都宣布过一种禁令,酒店里不许卖热菜,菜馆里不许卖酒,说是为了厉行节约。不过这也难不倒酒馆的老板,冷菜就冷菜罢,照样还是拿得出那么多花样,就和用来盛不同等级酒水的多种瓷碗、玻璃杯……一样。左转上坡,有一家戏院,远远就能听到川戏乐器奏出的凄厉的高音。在喧闹的市声中我感到的却是一种难堪的萧寂,这是很奇怪的,大概和我当时的漂泊心情有关。
一九四五年的初春,我在民国路上找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第一次看见了巴金。
离开上海的时候,老师李尧林交给我一封信,说有困难时可以去找他住在重庆的弟弟。不过我并不是为了解决困难来的,我非常希望看到自己敬重的作家。几年前在天津,一次听说巴金来了,就住在尧林先生的宿舍里,可是终于没有勇气闯进去看一眼,失却了机会。孤岛时期巴金躲在霞飞坊写书,他也没有给我引见过,我也没有提出过要求。这次依旧是带着惴惴的心,壮着胆子去的。我看到的是一位朴实的人,虽已不是青年,但仍旧带着青年人的神色,和我从他的小说中认识的那些青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话很少,只是从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同样熟悉的热情。好像很想和我说些什么,可是又说不出什么。
文化生活出版社只有按下临街的一间房子,很小,杂乱地安放着几只写字台,大概编辑、发行的事都是在这里办的,里面还有一间更小的小屋,是巴金和新婚夫人的住处。那一次我没有见到萧珊。
我交出了尧林先生的信,说了些他在上海的生活情况,没有坐多久就告辞了。
这以后我大概又去过一两次文化生活出版社。我将几篇旅行记请他拿给《旅行杂志》发表;他还帮助我卖掉了一件大衣,是托他在沙坪坝的朋友开的寄售行卖出的。这样,在写作和生活上就都得到他的帮助。到了重庆以后,续学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没有得到学校的承认;生活上也是窘迫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孤愤暗晦的心情,就和重庆的天气一样。
转过年来的初夏,我到了桂林。那已是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在一个飘着细雨的下午我在桂林街头徘徊,又找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但他已经离去了。
后来在印度接到过一封信,告诉我《锦帆集》已由他编好付印的消息。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子。
一九四六年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五十九号去访问,又见到巴金和萧珊。从这时起,我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尧林先生已经过世。他们就住在他生前住的那间房子里。过去尧林先生和巴金同住的时候,他自己是住在亭子间里的。这间三楼工作室临窗放着一只书桌,过去我看见过的井井有条的书桌巴金住下以后就立即变得零乱,书籍、纸张、报刊胡乱地叠得像小山似的。书桌后面是一张床,床后面三分之二地方排成了用书架组成的方阵。书架是漆成黑色的,玻璃橱门后面糊着报纸,已经发黄变脆了。我在这书橱组成的“方阵”里走过,那是只能容一个人侧身挨过去的。我不知道书架里放着些什么书。
亭子间里也排满了同样的书架,只留下很小一块地方安放床铺。
二楼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一张圆台面以外,就是几只破旧的沙发,这就是当时我们称之为“沙龙”的地方。朋友来往是多的,大致可以分为巴金的和萧珊的朋友两个部分。不过有时界限并不那么清楚,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们这些“小字辈”混在一起的。萧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这里面有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好像过着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显得非常快乐,无所不谈,好像也并不只是谈论有关文学的事情。
巴金平常很少参加这种闲谈,他总是一个人在楼上工作。到了吃饭或来了客人时才叫他下来。到今天我还保留着一个清晰的印象,披着一件夹大衣,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咿咿哦哦地读着,踏着有韵律的步子从楼上慢慢地踱下来,从他那浮着微笑的面颜,微醺似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从阅读中获得的愉乐。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情景是有点可笑的,因此就记住了。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巴金在我们身边,可是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像一群孩子那样围着他喧闹,当他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时,他才是活泼的、生动的。这“糖果”就是在他工作的出版社里出版的新书,这包括了他自己的著译和朋友们的新作。当签了名将一本本新书交到朋友手中时,他表现出了最大的快乐。他说过,“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这确实是真话。
巴金写完了《寒夜》以后,一直在译书。工作勤苦、休息的时候很少。有时候向他提议,“去喝杯咖啡吧”,他说“好嘛”。这样就和萧珊带着小林一起到老大昌去坐一会。我记得大概还有一两次一起到“兰心”(现在的“上海艺术剧场”)去听工部局乐队的演奏。这是尧林先生多年的习惯爱好,过去我常陪他去听这个乐队的演出,每次他都是选了八九排靠边的位子来坐的。
萧珊和我们都叫巴金“李先生”、“巴先生”,到后期有时候萧珊也叫他“老巴”;他招呼我们的时候就只叫名字,他叫起萧珊来总是用“蕴珍”的原名,常常把“珍”字拖长了来念成“枝儿”,这就说明他的心情很好,接下去要说什么笑话了。
上海解放前那两年,币值暴跌,物价飞涨。巴金是靠稿费生活的,当然也受到不小的影响。可是我不记得他们有什么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时候。读了他纪念顾均正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在最紧张的时候他接受过开明书店每十天十块银元的“应变费”。我只记得有一次陪着萧珊拿着开明书店开出的期票去兑现,两人坐了三轮车从书店赶到银行,取出用小口袋装着的“法币”坐在车上毫无办法的情景。那时“大头”(银元)好像还没有出现,如不将手头的“法币”立即变为“物资”,几天以后就会变成一堆废纸,那真像手里捏着一团火。可是“抢购”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就是在这样紧张尴尬的时候,萧珊依旧是高高兴兴的,仿佛是在进行一种新鲜有趣的冒险活动。
萧珊当时虽然已经做了母亲,可实在不像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好像仍旧处在“不识愁滋味”的状态。当然她也有皱起眉头作出苦脸的时候,但并非为了自己。在她脱掉鞋子横坐在沙发上入迷地读小说的时候,当听到自己的同学好友给人欺负了的时候,就会生气,发愁。她会说一口不够水平的宁波腔普通话,喜欢在朋友面前一本正经地说,特别是当着北方朋友面前是如此。如果谁要取笑她,她就生气。
她对人没有私心,有的是同情。她愿意帮助随便哪一个陷入困难的人,天真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她受十九世纪外国文学的影响很深,说话、行事有时候就流露出这方面的影子。她喜欢写信,很美的、散文诗一样的信。听说女儿小林打算整理她和巴金的通信,真是值得高兴的事。
萧珊喜欢认识新的朋友。她听说黄宗江夫妇正借住在朋友的住宅里,有很大的花园,环境很好,就约我一起去访问。那一天她特别高兴,换上了新衣服去作客,玩得痛快。不过看到我们拿她当作尊敬的客人接待时,她却并不满意。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巴金离开上海起程去朝鲜,国庆前后回国度假。萧珊带了小林到北京去接他,九月二十三日与我们结伴一起北上。第二天来到天津,车子出了故障,我们先下车,玩了半天。在起士林吃点心,到南开中学寻访尧林先生的故居,这已经毁于日军的炮火了。又到东门里、劝业场买旧书,乘当天下午车到北京,送她们到顾均正先生家。巴金是十月十四日从朝鲜回来的。这以前萧珊和小林在北京玩了半个月。陪她们逛了故宫、北海、天坛,到门框胡同吃奶酪,“仿膳”吃饭,听了梅先生的“金山寺”,看到了许多同学、朋友,……这半个月她玩得痛快、高兴,巴金回来后他们就同住在顾家,又几次应朋友之约吃蟹、吃饭。以上这些往事都是从我的旧日记里查到的。日记发还时已经残缺不全,还经人细细读过,画了许多红杠子,夹了许多签条,指出应该注意研究追查的各种线索,但后来却逐渐失去了兴趣,不再进行“批注”。也许这些简单频繁的记事并不怎样有趣,经过归纳、拔高,最多也不过可以得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定论”,这也实在过于平淡无奇了。不过读了这些旧日记,倒真能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记起萧珊怎样迫不及待地要赶到北京去接离开了八个月的亲人和她们重逢时的欢乐。
萧珊是忍受不了寂寞的,她爱朋友、爱热闹,喜欢在生活里有更多的光明和欢笑。她译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译得很美,带有她个人的风格。翻译是困难的工作,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要能保留原作的风格才算是好的译品,我却一直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名译。做不到这一点,能在译本中表现出译者自己的独特风格也算得是一种有创造性的上等作品。鲁迅先生的译《死魂灵》就是例证。
萧珊后来请求到《上海文学》去作义务编辑,还参加过“四清”工作组,看来都是她的不肯安于“寂寞”的性格表现。不过这又有什么值得责难的呢?只是她的善良、天真与长期来生活环境中养成的作风、习惯与现实生活矛盾不少,一旦碰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她是必然无法抵御的。一九六六年后我已经完全断绝了与巴金家庭的来往,不过也时时想起,担心萧珊怎么能挨得过这样残酷的考验。我听说过在淮海路上贴出了批判巴金的大字报专栏,可是一直鼓不起去看一下的兴致;连参观全市电视广播批斗巴金大会的“光荣”也一次都没有过。等我知道萧珊病逝的消息,那已经在两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