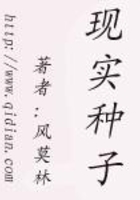正如怀特(1995)所指出的,像美国的哈金法案(USHarkinBill)这样试图抵制进口一切不能证明是“非儿童劳动力制造”的产品的运动,都将重点放在关注出口部门的儿童劳动力,但事实上这些行业的工作条件有时候要比其他行业好。相较于家庭或家庭农场的无报酬的工作,童工们更愿意选择在这些部门就业。可见,这种保护主义框架其实是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来倾听儿童的声音。例如,它将儿童的受教育权与参与工作对立起来,却无法解释为何对于大多数国家的儿童而言,是工作让学校教育成为可能。更一般地说,它忽视了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对于他们而言工作很重要的儿童的要求。
儿童工作与儿童劳动
保护主义话语中对儿童工作的普遍定位的一个结果是,研究文献常区分“儿童工作”和“儿童劳动”的区别,并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核心的分析性区别(Nichols,1992)。例如,费夫(Fyfe ,1989,第4页)认为:
我们需要对“儿童工作”和“儿童劳动”作出基本的区分。因为它已经带来混淆,且没能对这一领域中真正急需关注的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很明显,并非所有的工作对于儿童都是不利的。这一观点几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毋庸置疑,许多儿童都希望得到工作机会,认为它是通往成年的一个过程,是儿童发展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合理组织和计划的轻度的劳动,不是儿童劳动。那些没有减损儿童的其他基本活动如休闲、玩耍和教育的工作,不是儿童劳动。儿童劳动是那些损害了儿童的健康和发展的劳动。
为了辨别出对儿童有害的工作,那些致力于让儿童远离虐待和剥削的组织对儿童劳动/儿童工作的差异进行了区分。他们对那些被认为是“劳动”的活动优先进行干预,并制定了关于哪些儿童工作形式应该被废除的标准。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做法是很有用的。它辨别出了那些儿童对于特定工作形式特别脆弱特别是那些本质上很危险的工作,以及那些儿童患病率和受伤率特别高的行业(Salazar,1988;VanOosterhout,1988)。它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奴役的形式如包身工上,这种形式如今在印度是非法的,但仍然存在(Whittaker,1985;Karp,1996)。在印度,一个家庭欠下的债务必须通过在工业企业中用劳动的方式偿还,其中制砖业就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在实践中,低工资和故意欺诈使得还债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债务被转移到儿童身上,使他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能在无休止的苦工和不断增加的债务中度过。对于这样的儿童活动,用劳动(labour)来表述可能是恰当的。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法律允许的儿童工作进行控制,但在实践中,这些劳动法普遍被忽视了。其部分原因仅仅是因为儿童的工作太分散了。儿童工作的广泛存在使它成为一种常态,变得不被人所注意了。结果是,那些被国家注意到的童工可能不是通过人道主义视角来看待,而是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个问题来看待,“在街头从事销售或服务工作的儿童并不被视为工人,而是被当作流浪者、被抛弃者或反社会行为的犯罪者而被带到法官的面前”(Boyden,1990,第204页)。另一方面,大量童工又不可能受到调查:大部分童工都在乡村,远离官方的管制,通常是和家庭其他成员一起工作。另一些儿童在与外部几乎没有接触的环境中工作,如泰国的童工实际上是被监禁起来的,他们的家信都要被审查(Boyden,1991,第124页)。这些儿童通常在小型作坊里做一些从大企业转包来的工作,这些大企业无论是否知情,都可以否认他们雇佣了童工。
一部分官方控制都会被规避掉,因为这样做有广泛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官员们可能会收受贿赂从而对那些产生暴利的非法劳工雇佣现象视而不见。在一些行业中,如印度的地毯制造业(Kanbargi,1988)或埃及的皮革制造业(Abdalla,1988)中,童工的低工资是确保这些行业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中立足的重要因素。并且,父母们也可能积极反对政府对他们的孩子工作的管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当美国和欧洲逐渐建立起严格的控制时就是如此(Stadum,1995)。从当代世界的贫困家庭的角度来看,儿童劳动可能给儿童个体带来的伤害必须要与整个家庭的生存进行比较来做出衡量。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许多情况下,将儿童排斥在帮助他们家庭生存的工作之外的做法既不现实也不受欢迎,这一现实打消了基于人道主义来保护儿童的念头。这个领域更为实际的政策发展是试图将对禁止虐待儿童的政策和增进家庭经济的政策结合起来,非政府组织在这个新思路方面走在前列(正如他们的一贯表现)(BoydenandMyers,1994)。他们没有孤立地关注儿童的工作,而是采用了一种更为宽泛的方法,即关注结构又关注能动性。家庭整体收入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得到提升:为成人创造更安全的就业;将学校课程调整得更符合贫困家庭的实际需求以增加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吸引力,以及增加校园餐作为重新分配财富和提升入学率和出勤率的一种方式;让儿童在既能接受培训又能得到收入且能培养出参与感和能动性的行业内就业。正如博伊登(1994,第38页)所指出的,这种方法非常重要,因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为儿童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意味着儿童工作责任的增加而非降低:许多儿童为了支付学费而工作”。
但是,尽管儿童劳动与儿童工作的区别在决定社会政策和实践的优先领域方面有用,但它作为一个分析术语则没什么帮助。事实上,这里我们一直替换着使用它们———这是有点不寻常的做法。原因显而易见:所谓的分析性差别主要是道德层面的。它导致根据什么提升或破坏“童年”、“健康”和“发展”来评判儿童活动的价值,仿佛这些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不证自明的普遍真理一样。事实上,关于儿童应该做什么工作,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做,它对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的平衡等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所有观点都谴责对儿童生活的严重侵犯,但除此之外却几乎没有其他共识。正如怀特(1995,第13页)所说:
想要在“儿童工作”……和“儿童劳动”……之间划一条清楚明晰的界线是不可能的,大多数这样的尝试都太宽泛、模糊和陷入循环论证,又或是,当它们试图变得具体,又太过自相矛盾,不合逻辑,并且和儿童的观点不相协调。
关于儿童劳动的著作通常难以对不同形式的劳动作出区分,因为它们对工作和劳动的区分会引起关于什么能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道德评判。例如,它们没有关注儿童在市场上的有薪劳动和“不自由的”或强制劳动,如占有奴役(chattelslavery),农奴和债务奴役(debtbondage)之间的关键差异(Archer,1988)。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指出的,尽管世界市场的商品的生产和交易的整体环境是自由的,但劳动力的不自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与成人相比,儿童几乎没有任何地位,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儿童,因此,他们特别容易遭遇强制劳动。虽然这方面少有权威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形式的儿童劳动相对来说很少。儿童运动者最常引用的关于儿童劳动的例子都是那些不自由的劳动或具有这种特点的劳动(如上文提到的泰国被监禁起来的儿童劳工),这是分析混乱的表现。虽占有奴役的特点是奴隶主拥有对奴隶的所有权利;债务奴役是债务人向债权人用自己的劳动服务作为担保,但这些劳动服务并不属于债务偿还的一部分,且其时间长度和性质都没有具体规定;农奴是指向土地主租种土地,保证在这边土地上生活和劳动,向土地主提供服务,但不能离开这片土地,其身份也无法改变。
然有薪劳动毫无疑问也具有剥削的特征,但似乎儿童运动者过分重视引发道德愤怒的需要,而忽视了分析精确性或甚至是公正的精确描述的需要。
例如,索耶(Sawyer,1988)不加区分地用“儿童奴役”一词来涵盖了所有儿童工作的状况。
这种概念模糊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分析的不恰当。这种对于不自由劳动的解决方案并没有被大多数儿童研究所采用。事实上,对于儿童面临的问题,不恰当的回应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使问题恶化。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孟加拉国服装业解雇了儿童劳工,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服装工厂中的75万工人中,有大约1/10的人是年龄14岁以下的非法儿童劳工,大多数都是女孩。她们从事一些不太有体力要求的工作如剪掉服装上松垮的纱线和将服装的各个部分分发给机器操作者。
雇主们迫于国际社会抵制儿童劳工生产的产品压力而解雇了儿童劳工。结果一项跟踪研究发现,这些被解雇的儿童仍然继续选择工作———没有一个人选择重新回到学校———但就只能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和街头的更为危险的条件下(包括卖淫)工作。和那些仍留在服装业中的少数人相比,她们的收入减少了,营养状况更差,健康状况也更差。在向媒体的请愿中,这些儿童自己提出希望每天参加轻度的工厂劳动,在学校读书2—3个小时,这样是解决她们的贫困的最佳方法。最后的结果是,雇主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将重新雇用与学校教育及未来的就业前景结合在一起(BoydenandMyers,1994)。
将视线转向工业化国家时也会发现,将劳动与工作区分开也没有什么帮助。例如,费夫(1989)在记述那些导致儿童工作制度产生及儿童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位置的事件时,就无法证明这种差异。他天衣无缝地从工业革命时期的儿童工厂工作转到调查当代儿童参与家庭作业、家务劳动和照顾小孩上,却没有考虑到他认为非常关键的劳动与工作的差异。这种忽略隐藏了另一个重要的可能性:从儿童的视角而言,在结构水平上对家庭之外的有偿劳动和家庭内部的劳动进行区分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女性工作的研究文献对这种区分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它们认为这种区分是基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而这种划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这些研究文献不仅关注有偿劳工与家庭劳动的结合为女性带来的“双重转换”,而且还关注“私人”的家庭劳动对于“公共”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虽然儿童在这场争论中是隐而不见的———其假设是儿童是劳动的对象,而不是成果的贡献者———但很明显,儿童也参与到了这样的劳动中(Goodnow,1988),尽管布莱恩(Brannen,1995)和宋(Song,1996)发现,这种参与在英国有着重要的性别和种族差异。关于父母与儿童各自对于一般家庭劳动的贡献还存在争议,但儿童逐渐学会了“自我照顾”,从而减轻了母亲们的任务,从而也对公共经济作出了贡献(Mayall,1996)。更不幸的是,当父母生病或身有残疾时,儿童承担起本该由国家承担的照顾责任(AldridgeandBecker,1993)。
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费夫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种认为在工业社会的经济中不存在儿童有偿劳动的观点只是一种错觉。在英国,儿童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状况的转折点是在1900年和1920年之间。
在这期间,儿童开始将大部分白天的时间用于学校教育,法律将14岁定为工厂雇用工人的最小年龄。英国目前儿童的法律地位是由《1973年儿童就业法案》(犜犺犲1973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狅犳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犃犮狋)所确立的。这部法案以20世纪30年代遗留下来的地方立法和全国立法为基础,并澄清了地方立法和全国立法的不明确之处,它对儿童的工作时间进行了限定(他们不能在早上7点之前或晚上7点之后、放学之前工作以及星期天工作超过两小时),并且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就业。此外,就业的儿童必须进行登记。但是,1973年法案实际上未能施行。过去的10年在不同地点进行的一系列调查证明,有很高比例的儿童———1/3或以上———都参加了有偿劳(Davies,1972;MacLennan,1985;PondandSearle,1991;Lavalette,1994)。即使在考虑到定义和方法的差异后,这一比例仍然存在。来自荷兰和德国的数据也显示了相似的比例(Hobbsetal.,1992)。
的数据代表的是在某一时间点儿童工作的发生率。如果将之前有就业经历的儿童包括在内,则比例上升到66%(Clydeside)和62%(Luton和Bedford)。这些研究中儿童所做的工作也很一致:最常见的工作是送牛奶、报纸等,销售工作特别是上门推销,以及做服务生,这些工作有一些性别差异。男孩们更可能从事送货的工作,而女孩们更可能从事销售和服务生的工作。
按年度、地区和研究分类的儿童劳工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