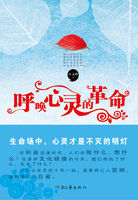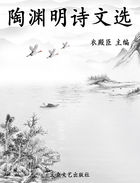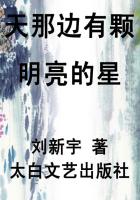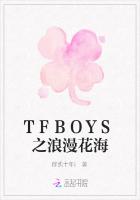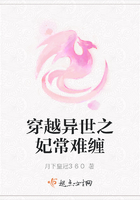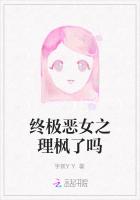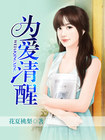童年及其具体化
希林(1993)本人对于童年的关注相对较少,他的研究与童年相关的只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他对于社会和文化塑造及改变生物身体的过程的阐述,这是埃利亚斯(Elias,1982)所称为的文明的进程。他并不想通过对这一过程的阐述来意指一个高级社会形式的出现,而是揭示出一种历史趋势,在这一趋势中,社会中的个体逐渐内化了特定形式的规则,并开始控制社会行为。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与身体功能有关的行为,如进食、性交和排便。
这些行为从理论上说是自由的,但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上,埃利亚斯所描述的进程带来了儿童和成人之间心理距离的加大:在西方社会中,“成长”是个体文明化的过程,每个年轻人自童年初期开始就自动进入了这个过程。
那些将儿童与成人区分开来的行为,即使是无意识的,也被认为是对身体及其功能的控制的成功内化。因此,这意味着那些还没有学会特定身体控制技术(随着时间发展会发生变化)的年幼的儿童从文化上来说是不文明的。
事实上,埃利亚斯指出,现在许多与儿童有关的行为———例如用手抓着东西吃或随地大小便———成人曾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也这样做(见“童年的时间性”一章)。但是,在当代社会,尽管人们会原谅那些还在学习如使用洗手间或使用刀叉就餐的儿童的行为,但他们要想成为正常的成年人,就必须逐渐学会这些技能。埃利亚斯提到的这种渐进的习得的具体化过程扎根于身体实践之中。
因此使得特定行为方式成为自发性的行为。这一过程也是布迪厄(1986)的社会阶层研究的核心。他认为,不同个体和群体所能获取、调动和转化的“资本”不同,造就了不同的阶层,这些资本包括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
经济资本包括家庭成员可以支配的金钱和商品———但不一定是同等的———也是其他资本的基本来源。文化资本由两种类型的个人特征组成:制度文化资本———主要是指正式的教育文凭———和具体化的文化资本———言谈、品位、礼仪、技能、个性以及其他特征。社会资本由关系、网络和群体成员身份所组成,它提供潜在的社交机会、社交技能以及获取这种技能的机会。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还有一项很有用的概念,即希林(1993)所说的“身体资本”:身体本身或多或少就是或会成为一种资本。在某些方面,诸如健康状况的不平等,身体本身就是阶层关系复制过程的一部分,父母们常常说的“生活的良好开端”(agoodstartinlife)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们从布迪厄的学说中吸取的关于童年和具体化的最重要观点是,阶层差异(品位、言谈、习惯等)是具体的———他通过“惯习”一词来表达这一观点。惯习的形成是无意识的,它是儿童社会化的基础。例如,它包括一系列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假设的传播,不但以语言的形式,而且以具体化的实践的形式。所以,正是在童年时期,惯习的关键方面的具体化得以产生。那么,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可以说儿童生来就通过身体来理解和体验阶层差异。
但从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就可以对其的许多方面进行批判。
简克斯指出,英语社会对于布迪厄理论的接受事实上强调“(文化)再生产是一种复制或模仿,而非再生或合成”(1993:118)。这种对布迪厄“惯习”的解释是否准确有待商榷,但重要的是,布迪厄的研究中没有对其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联系作出理论说明:尽管“惯习”概念让我们可以了解儿童理解和改那些不能掌握这些技能的成人或那些丧失了这些技能的老年人就有被当作幼儿看待的可能,见HockeyandJames,1993。
造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能动性,但同时它也强烈地促使我们将儿童视为知识再生产的结果,认为他们仅仅是被动地接受那些传递给他们的观念。正如“玩耍是童年文化?”一章所论述的,这种观点甚至在用于理解儿童与他人玩耍的行为时都或多或少是失败的。
但是,鉴于社会化这一概念已经主导了童年研究,因此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童年和身体的解释中存在分歧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从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分歧。1934年,莫斯(Mauss)在其著名的开创性研究中,讨论了即使像走路这样的基本活动也受到了文化的具体期待的塑造,这种文化认为儿童通过一种简单的渐进的积累过程“学会”恰当的身体姿态和风格(Mauss,1973)。与此相似,贝特森(Bateson)和米德(Mead,1942)在关于巴厘岛文化的具体化形式的分析中,也没有谈及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成人与儿童之间在所谓恰当的身体行为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童年自身可能被看作在儿童的身体行为水平上呈现出的差异,它不仅是———到现在为止———一种文化中成人的未完成形式,而且也是作为童年本身而存在。正如普瑞德佳斯特(Prendergast,1992,第1页)所说:
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具体化的问题在生命周期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会凸显出来:身体轨迹被赋予象征和道德意义:身体形式就是社会转变的体现……每个阶段都要求我们以一种恰当的特殊的方式关注和调整自己或他人的身体。
虽然这种观点可能淡化了童年作为一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而支持将其视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布鲁邦德兰纳的研究却指出,既承认具体化的重要性,又承认儿童通过这种具体化来理解和建构社会世界的能动作用,这样的视角是很有分析前景的。
这一点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964)提出的具体化发展理论(theoryofembodieddevelopmen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方法的起源是梅洛庞蒂对以巴甫洛夫(Pavlov)和皮亚杰为代表的对童年发展的机械分析和理想化分析的批判。他认为前者将儿童行为简单理解为心理过程,结果导致了一种过度决定论(overdeterminist),正如奥尼尔所指出的,“人类习惯的建立不是一种对既定反射的学习,而是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这些问题理论上与最初的‘学习情景’相似,但实际情况却绝不会相同”(ONeill,1973,第68页)。同时,梅洛庞蒂还批判了皮亚杰关于儿童学习和意识的去具体化(disembodied)即认为经验首先是本能的观点。
这正是图润(Toren,1993)的童年研究所朝向的方向,不过其方法却不同。借鉴梅洛庞蒂的观点以及大致与希林(1993)相似的立场,图润认为儿童是在一个历史和社会中的身体里成长和发展的。她认为,心灵是在塑造它的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发展的,它不仅作为意识发展,而且也作为身体发展,即使在神经系统的层面上也是如此,她强调儿童自身具有的创造性,这使儿童生活在一个和成人世界相关联但又不一样的世界之中,这种观点和希林的消极社会化观点形成了对立。图润随后指出,研究儿童如何建构关于世界的知识,对于关注社会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学研究可能也是如此)至关重要。
正如其他作者已经指出的(James,1979),图润注意到有大量人类学证据表明,不同年龄的儿童对于社会世界的概念和成人对于社会世界的概念正好相反。通过关注社会互动的具体化特征,她指出了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以及它的意义何在。在关于斐济儿童的人种志研究中,这些儿童根据个体在仪式中的位置来判断个体的身份。而成人正好相反,他们是根据谁占据这一位置来判断这一位置的意义。因此,成为成人的过程不仅牵涉到文化知识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抛弃过去生活中已有的知识。
但是,要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作出解释,就必须承认社会关系既是具体化的,又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儿童之所以能够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能“解读”自己和语言过程同时发生(有时是矛盾的)的具体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儿童先建立起一个概念的某一方面,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方面较之其他方面更为简单,而是因为成人的行为———即使是对它的否认———使它更为重要”(Toren,1993,第473页)。因此,对儿童的概念的研究能够揭示社会关系的一些具体化的但被否认或遗忘的方面。
与此相似的一个例子是,欧美儿童认为种族类别是评价性的,而成人却否认这一点。
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1993)拓展了这一不同意义结构和身体表现的观点,她呈现了儿童可能以与成人照顾者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身体经验。
她对丹麦小学中儿童和他们在生病和发生小意外时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儿童如何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她注意到,教师和其他成人认为儿童对在学校中造成的小伤口、擦伤和碰撞淤青的投诉太言过其实。作为对这种要求关注的回应,成人试图教会儿童少惹麻烦,有时是通过说教的方式,有时则是对他们的投诉置之不理。而她对儿童的观察发现,他们确实对身体经验投以特别的关注,通常还要求其他人“看!”但对于儿童来说,这种要求并不是想要得到医治或急救———成人常常这样来解释这种要求。相反,这和所有玩耍游戏中的行为一样,是儿童在邀请他人分享他的身体经验。在她作为一个成人与儿童的互动中,克里斯滕森逐渐认识到,对此的恰当回应不是训斥儿童,甚至也不是为他们提供帮助。对此很简单且不用大惊小怪,就是以看的方式去分享他们的身体经验(见“童年的时间性”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