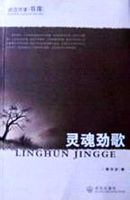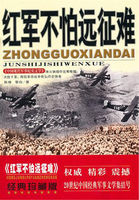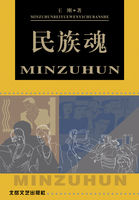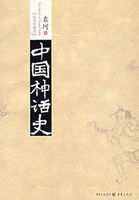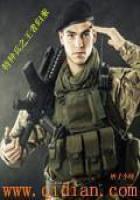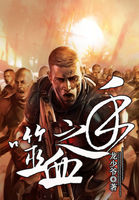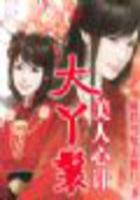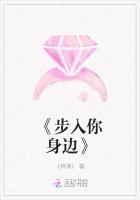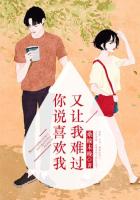所有这些观点对童年的社会理论建构来说都是恰当的。的确,童年一直以来都是结构和行动的二元对立的试验田。因为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关于儿童能力、权利、责任和需求的大部分问题都处于这两极之间。这种推理的可能性是无穷的。但是隐藏在这个理论谱系背后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人世界建构了结构和儿童这一行动者,并且前者对后者起决定作用,或前者使后者社会化。不论儿童的产生是乔姆斯基(Chomsky)所说的“深层结构能力”(1965)的出现,帕森斯(Parsons)的“规范导向需求的适当内在化”(appropriateinternalisation ofnormatively oriented need dispositions,1951),是通过西科勒(Cicourel)的“社会结构意义的获得”(theacquisitionofasenseofsocialstructure,1970),还是通过斯佩尔(Speier)的“互动能力的获得”(acquisitionofinteractionalcompetencies,1970),这种二元对立始终存在。事实上,在许多关于儿童的传统理论中,这种二元对立是成人儿童关系的基础,也是理解这种关系的关键。
同一性与差异性
第二个二元对立是同一性和差异性,它本身是社会学中自我和他者这一对立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新的对立形式意味着一个和他者建立联系又和他者区分开来过程,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自我和身份的定义与再定义的问题。与传统的自我和他者的差异不同,它强调这种差异的变动性。这有赖于强烈的内在感和同一性,以及对固定存在着他者的分类系统持续在场的假设。这种观点并不符合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它在人类学中就引发了一场政治批判。
但是,尽管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在当代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它从传统的童年研究一直贯穿至今,特别是在那些关注童年及其产生的研究中最为明显。从皮亚杰的儿童“去中心化”(decentring),到弗洛伊德的从本我到超我的过程,再到G.H.米德(G.H.Mead)的主我与客我之间的部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观念和有关儿童的话语密切相关。我们发现,如果个体是一种自我指向(selfintent)的轨迹,那么它只会对于所谓的集体性的需求和意义产生赞同或反对的情感,上述话语都不过是对这种观点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因此,和其他人一样,儿童获得同一性的过程,是一个和秩序问题发生联系的过程,这样自我和非我(not self)定义才能得以维持。儿童(通常)通过与成人他者的互动而认识自己。因此,这一过程的空间性既是认知性的,又是互动的,并和始终存在的反思性问题交织在一起。
连续性和变化性
在连续性和变化性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二元对立?儿童一直被视为这一维度的准确指标。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散发出向前看的新的希望,让我们不断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甚至对自己过往的怀念,并让我们期待未来(JamesandProut,1990a)。对于儿童和童年的研究既承认变化性,也承认日常社会关系中的连续性。正如已经指出的,童年空间可能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其样貌和意向不同而已(Qvortrup,1994)。
要抓住这一二元对立的不断变化的性质,“文化再生产”是一个恰当的分析工具。正如“童年的时间性”一章开始讨论的,文化再生产这一概念虽然通过各种理论观点表现出来,但其是指日常生活经验的自然性和暂时性。
这一概念试图表达这样一个动力过程,这个过程揭示出静止的、确定的社会结构的偶然性,以及社会行动内在具有的变革性和能动性。正如布迪厄(1986)在其现代教育系统的研究中所呈现的,文化再生产让我们认真思考社会经验中的连续和变化的必要性和互补性,让我们将儿童视为实体,视为生命历程,视为世代的实例。他认为这是统治阶级通过他们的孩子进行文化“再生产”的一部分,是有助于他们继续保持统治地位以及延续他们隐蔽的权力实践的一种机制(Jenks,1993)。本书中的讨论也表明,虽然儿童被打上了社会再生产的印记或类别,但他们也是文化再生产的主体。
本土性和全球性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二元对立是本土性和全球性,它可能是社会科学最近的兴趣所在。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过去和未来和关于从多样性到一般性的整个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总体趋势,我们这里所见的不是知识和研究主题的偶然汇聚,而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甚至可能是有意识的全球化影响的结果。随着地理局限越来越少,世界不断地发展为“一个地方”(onesingleplace),那么我们之前讨论的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就变得更有指向性了。在生态、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共享的环境中,人们现在关注个体和人类存在的一般状况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要忽视和掩盖物质差异的存在,相对来说,这种差异在人类经验中仍然普遍存在(见“童工”和“身体与童年”两章)。它是要为国际和洲际的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交换和操控主导人类存在经验指明趋势。
当然,社会行动仍然是本土的,对它的解释也是本土的。但是,影响社会行动的历史和发展的结构性力量的来源通常都是没有特定的、可辨认的边界。无论我们研究欧洲和北美的生活方式还是南方的生存之道,是讨论纽约的儿童时尚还是危地马拉的街头流浪儿童、波斯尼亚的儿童士兵或交通安全规则(GreenCrossCode),我们都仍然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塑造和限制儿童日常生活经验的社会是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的(见“一个童年还是多个童年?”一章)。
的确,现代性已经触及方方面面,尽管现代性的具体表现是集中的,但它的影响和形态却是发散的。现代性具有全球化趋势,它被理解为普遍化的经验,对我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儿童既是作为一种中介也是作为一个象征而出现的,特别是在关于社会身份问题和风险与福利问题方面。正如我们关于儿童劳动、健康和身体的讨论中所发现的,儿童已经成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中考察身份性质的来源,同时也是它最基本的产物的危险不断累积的结果。并且,如果我们转向儿童,我们也会碰到从地方性的“陌生人危险”(strangerdanger)到全球性的因特网色情这些用以进行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问题的表现。当我们重新以一种连续统一体来看待这种二元对立,其关键就是它将“童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
在分别讨论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这些核心二元对立时,我们已经揭示出“儿童”和“童年”的大量主题不能避免也不可能避免的局限性。事实上,它们也不应该避免局限性。为此,我们将证明它们与本书展示的童年话语的结合,并且以此来呈现新童年社会学研究对于社会理论可能作出的贡献。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提出,社会理论中存在一组反映了唯意志论、决定论、普遍主义和排他主义四个主要哲学维度的关注点,这四个维度的综合为我们探讨一组更为综合的关于结构与行动、同一性与差异性、连续性与变化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关系的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正是通过在这一社会学理论网络中对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四种不同声音的定位,我们才能知道,关于社会世界可以提出哪些问题,以及当代童年研究可能作出哪些回答。
童年的二元对立
本书主要部分的讨论呈现了研究“儿童”的四种新的不同方式。概言之,它们就是社会结构化儿童;社会建构的儿童;部落儿童;和少数群体儿童。虽然每个主题都是通过这些方法分别进行探究———例如,关于儿童劳动和多样化童年的问题主要采用了结构化方法,而关于儿童玩耍的讨论则主要采用儿童中心的方法———这些方法之间的表面差异掩盖了一系列的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些相似性使它们共同反驳了我们在序言中所讨论的传统的发展性儿童模式的核心分析方法。因此,这些差异和相似性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无论如何,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造成一个分离主义者的类型学。再次重申: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巩固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并为它的发展指明方向。为此,我们将强调这四种话语的重叠部分和一致的部分,而不是区分它们的差异和开启一个僵化的、固定的、分裂的枯燥过程。
社会发展性儿童这一传统概念(在“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节中我们将其作为过渡性理论建构的一个例子)和我们的“新”的儿童研究方法的四重分类(在“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中我们将其称为儿童的社会学概念)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生成”(becoming)和“存在”(being)之间的差别。作为社会化理论的特征的社会发展性儿童模式,总是涉及改变和变化的过程,追求这种本体论的游移不定是成人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点总是事先设定的。因此,发展中的儿童本质上是一个附带现象,它的“生成”说明了它的不完整:
从各种学科和视角出发,以及从各种不同的研究兴趣出发,儿童被理解为一个阶段,一个结构化的生成过程,但很少被看作一种行动或一个连续的社会实践。这种被童年研究所采用的“成长”隐喻符合还未生成这一特征,这种特征也是预先设定的。这样童年就被称为:一种“生成”(Jenks,1996,第9页)。
相反,我们所说的童年的四种“新”话语将童年理解为“存在”。儿童被看作一个人,一种身份,一种行动,一组需要、权利或差别———总之,被看作一个社会行动者。这种儿童“存在”的新的现象,可以从其本身来理解。它不必预先设定为缺乏能力、理性或意义。但是,儿童的“存在”不是静止的,因为它也处于时间之中。和所有的社会行动者一样,它生活于历史之中。
因此,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我们转向一个以生成为基础的概念框架中,就抛弃过去和现在的概念,“儿童本身是积极的,不仅仅是模仿性的,而是作为……它自身建构的主体,作为像任何成人一样自然的主体,这种主体性是指通过选择发起的行动”(Wartofsky,1981,第199页)。
概言之:新童年社会学方法的认识论突破是转向研究真实的儿童或作为儿童的经验。相反,社会发展性儿童模式几乎完全不关注儿童:儿童或是成长的具体表现,或是评估和测量过渡和变化的指标。例如,传统的发展心理学在它将儿童装入一个发展“阶段”或“水平”方面非常突出,相似地,社会化理论从儿童的表现中寻找成人互动技巧的证据,以此作为儿童迈向成年阶段的证明。这种方法忽视了儿童“作为一个儿童”真实地生活在社会世界中的日常的共时性的体验。
为了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洞见,我们将再次讨论关于童年的四种新的话语。通过强调它们的分析性特征,我们将不仅展示他们如何提供了不同的关于童年的观点,而且还将展示这些新的视角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发展性的。正如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即将发表)所指出的,“童年”本身不是一个分析性的类别;它是一种“需要”得到分析的经验现象。在本书中,根据社会学分析中核心的二元对立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对儿童和童年的研究已经实现了这一点。
社会结构化的儿童
这里,理论家们没有采用认为儿童处于社会边缘、等待融入成人社会的观点,而是将童年看作一个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持续的存在于所有社会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
童年是一个完整的形式,这一观点值得与认为儿童逐渐融入社会这一传统观点相比较。我们……选择不同于将儿童视为一个个体人生的过渡阶段的观点: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恒定的形式,即使它的成员不断发生变化,即使它自身随历史发生改变,它也永远不会消失。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的历史变化性解释了它的变动性质,并且它是在任何时刻理解世代间相互影响的必要条件。童年与其他结构化形式———年龄群体、社会阶层等———的相互关系随着社会系统和社会构成的改变而不断发生改变。这样,我们必须密切注意童年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其他任何社会经济类别的结构性变化:它们相互影响,且基本上受到同样的外界影响(Qvortrup,1994,第23页)。
儿童是一个结构性类别,他们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应该被理解为每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完备形式。无论它的现实表现形式如何,儿童一直都从属于社会且处于社会之中,并且将来还继续如此。这里存在着强烈的童年的普遍性和“儿童”身份认同感。童年不是也绝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历史发明。正因如此,在这种方法中,儿童成为独特的分析单元,因此可以和其他构成社会系统的单元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