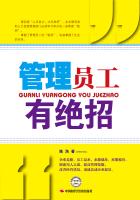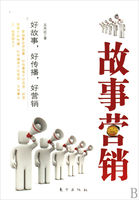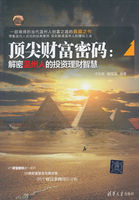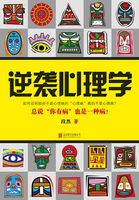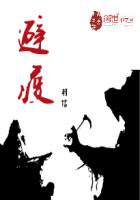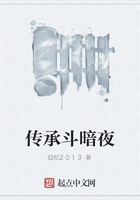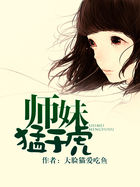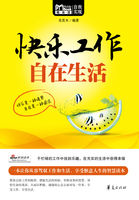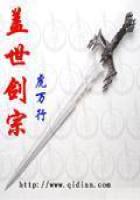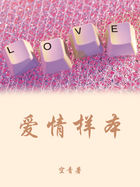邓国良当时也没多说什么,但从那以后,开始对亲戚进行无比腻味的疯狂公关。后来搞得亲戚觉得像被狗皮膏药贴上了一般。尽管多多少少有些反感,但对邓国良这个人却在“被腻味”中逐渐有了了解,觉得他除了闷头和腻人之外,各方面都还过得去,值得交往。
于是,两人渐渐就放开了戒备,终于有一天,邓国良张开了口,说出了替香港兑换点联系海外客户的事情。亲戚就答应他,和自己的战友说说这事儿,尽量试试帮他。结果战友是个豪爽性情无以复加的人,马上答应,以后的海外汇款可通过那个货币兑换点操作。
就这样,当战友的海外亲属再次要给他汇钱时,那个货币兑换店在行动:
由邓国良在国内按照买汇黑市价1∶3.2将6.4万元人民币打给战友,而陈灿文在香港收取战友亲属打过来的2万美元。
这个操作叫做外汇截留。顾名思义,就是把本属于流入境内的外汇截留在境外。
黑市有黑市的规矩。值得一说的是,黑市规矩往往比那些黑字白纸上的明令来得有效。这一点事实上很值得政令制定者反思:如何提高执行力。信义是地下钱庄的基础,而国家机器有强制力,但也不能完全没有“信义”,这个信义翻译成官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叫做“公信力”。也就是说,公信力是政令的基础。否则,法律可能都不如口头承诺!
当然,在执行力上,除了信义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利益驱动大于责任驱动!
比如,邓国良这人就很守规矩,第二天拿着2000元给了高建明的亲戚。亲戚险些花容失色,急忙问这是干什么的钱。邓国良如实告知,每操作一笔汇款,他能得2毛钱的差价。这次幸得他的帮忙做成这笔生意,所以按照规矩,他也是中间人,理应分享利润。
只说了句话,就赚了2000元,亲戚心里想,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然而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钱庄做笔生意才2万美元,太少了吧?这和本书开头写的巨额交易量不相称呀。
实际上,第一,当时的陈灿文还是个小钱庄,基本上就是货币兑换店的规模;第二,真正的钱庄生意不是几天一笔或者每天一笔,而是每天几笔、十几笔、数十笔或者上百笔!
而全国遍布的大大小小的地下钱庄、黄牛党,是根本无法统计的,这也是本书最初提到的热钱无法统计的主要原因。
这里只有一个概念,钱庄的数量,很多!
圈内的人提及地下钱庄的发展壮大,常用蚂蚁搬家这个词来做形象的比喻。
尽管地下钱庄是非法经营,但是有一点这里必须指出:这种蚂蚁搬家式的商业模式,简单而传统,一靠量,二还是靠量。
全世界都行得通的传统的薄利多销原则,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钱庄除了用这种外汇截留的方式在境外储备自己的外汇小金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比如,截留那些要到国内的投资款项,这个操作基础是:当时国家投资管理的理念为只要你有钱建厂房就算是投资,而不管你的钱从哪里来!
地下钱庄就是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模式发展着,长大着,悄悄进行!也就是这样一小撮人,以后大都成为呼风唤雨、调动民间资本的大资本家,成为今天热钱暗流涌动的翻江手,成为中国经济亦敌亦友的灰色地带。
地下钱庄到底操控着多少钱,地下钱庄自己都说不清!
5 钱多人傻,速来
地下钱庄也有发展机遇期。
1986—198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中国的外汇增长开始加速,国家外管局为了进一步维持并鼓励这种势头,专门提高了创汇单位的留成比例,自主创汇的外贸企业或生产厂家,外汇留成提高到20%,企业可以自主处理这部分外汇额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自己就能乱来,外管局还是有规定:所有留成外汇的调剂和兑换都必须在外管局的监管之下进行,必须经过外管局外汇调剂中心的调剂才能交易。
为此,当时的深圳会计管理还专门为了适应这样的形势而设置了一个新的会计科目--“货币兑换”,以反映企业创汇留成的转换情况。事实上,这一科目的设定,已经基本上表明国家默认了外汇市场存在着浮动汇率。比如,早在1986年10月,国家就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允许在经济特区和主要沿海城市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外汇管理部门买卖外汇,并提高了外汇调剂价,规定1美元外汇留成额度为1元人民币,现汇调剂最高限价为4.20元人民币。
这样的外汇政策,一度让外汇调剂市场异常活跃,效果立竿见影。到1987年年底,我国外汇收支总额已达7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由1981年的66.1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75.5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地不断加快,外汇流量也自然不断增加,这为外汇调剂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于是,国家继续趁热打铁。1988年年初,国务院又推出一个决定--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也给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要求,外汇调剂工作是外贸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配合。
政令如山,外汇调剂市场自然不敢怠慢,开始披星戴月地迅速狂奔:
首先,国家外汇管理局一马当先,在北京设立了全国外汇调剂中心,并责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城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或外汇交易所。其次,进一步放开外汇调剂价格,可根据外汇供求状况实行浮动。另外,外汇调剂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均可通过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外汇,而外商投资企业与国营、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之间,也可以相互调剂外汇,甚至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个人外汇调剂业务。
很快,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外汇调剂市场体系就逐步明朗并日渐成熟发展起来。
场内有调剂,场外就有空间。
寻找商机本就是生意人的天职。黄牛们对市场非常敏锐,很快发现,外汇的私下调剂虽然是在官方价格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并且明面上具备1元人民币的调剂额度。但是,实际的货币兑换价格,却是协商出来的!
协商,就是大家有得谈,利润空间本就不小,双方或多方利益均沾的话,买卖没有做不成的。因此,原先勤勤恳恳倒腾侨汇券和外汇券的黄牛们的老黄牛精神被再次激发出来,他们隐约觉察出,所谓“券”这种中间凭证的存在意义已经不大了,被赶出市场是迟早的事儿,这么“有利”的政策条件,直接在调剂缝隙中做文章更有前途。
于是,黄牛们华丽转身,地下外汇买卖生意全盘“钱庄化”,一个灰色的金融产业链条开始布局天下。
6 第一次交易
阴差阳错地当了会计,尽管高建明知道,这个工作不是自己的归宿,但总得给帮助自己的人一个交代,于是,他表面上干得很是踏踏实实,可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郁闷。于是决定静以待变,等待机会。
高建明是个很善于总结的人,早在上中学时就形成了“君子一日三省”的好习惯。每每下班回到自己小小的宿舍,他就会回顾自己毕业后的种种经历。往事历历,教训却只有十六个字:年轻气盛、不谙世事、锋芒太露、自以为是。
他深深体会到,社会根本不是哪个人的一己之力就能改变,相反,人主动去适应社会才是正途,整日怨天尤人,抱怨命运不公,那是祥林嫂,绝不是他高建明。路是自己走的,交通规则(社会风气)早成定式,打左灯向右转,别人看着必然不顺眼。所有的错误和挫折都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造成的,一切,都需要适应和学习。
因此,有时候高建明回到学校,或者遇到后来的小师弟们,都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只要有根棍子,都能撬动地球。就业时千万不要太挑剔,不要自以为是人物,毛泽东逝世前全国人民心里都想,没有他老人家大家可怎么过?国家会怎么发展?到头来,时间照样延续,历史车轮一样继续前行。
但是不管怎样,高建明的个人能力绝对没话说,加上自己讲义气,乐于助人,人脉网络日渐缜密,周围的人群对他更是刮目相看。不到三个月,机会就来了。
蛇口集团正在筹备一家专门的贸易子公司,缺一个财务经理,就将眼光瞄准到总部的结算中心来。结算中心乃至整个集团的同事都非常认可高建明,再加上主任“豪哥”是集团财务领域的大拿,他鼎力推荐的人,自然就上了推荐名单第一位,于是,高建明顺利成为了集团子公司--荣昌贸易公司的财务经理。
这对于刚参加工作三个月的高建明来说是一次职业道路上的飞跃。
但是,升任财务经理初始,外人对他的升职无比艳羡,可他自己却一个劲儿打鼓。
为什么?
搞财务,他一点儿都不专业!
刚刚走马上任,外表的光鲜并不能掩盖他真实的困境。对他来说,别说什么财务了,就连个会计凭证都不会做。好在有豪哥罩着,他经常虚心求教,甚至荣昌公司第一个月的报表都是豪哥帮忙完成的。我们前面也讲过,高建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天资聪慧,学习速度一流,什么事情只要看一次,就学个八九不离十。在豪哥的点拨下,会计业务自然不在话下,很快,他就从菜鸟蜕变成了财务高手。
在政策的推动下,荣昌公司很快就展开了外贸业务,处理外汇调剂和货币兑换这样的业务自然就落在财务经理头上。高建明一点儿没含糊,第一笔外汇兑换业务就办得极其漂亮。
当时,荣昌公司有20万美元的贸易款项,需要迅速变现人民币,等待他用。
这给高建明出了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尽管当时的政策已经相当开放,又是外贸公司自由兑换,又是汇率浮动的,貌似大家怎么干都行,但实际上有一点,必须经手外汇调剂中心完成。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当时国内的金融结算不是一般的缓慢,境外账款最少也要一个星期才能入账!
一边很急,一边很悠然,高建明夹在中间就有点手足无措。
郁闷的高建明再次求助豪哥。豪哥自然义不容辞,这天下班之前,就给高建明打电话,说晚上约了个能帮忙的人吃饭,让他提前预订饭店包间。
下班之后,高建明特意提前早到,在包间里等着救星们光临。
外面一阵脚步声和嘈杂声传来,有个声音高建明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耳熟。门开了,豪哥和一个重量级小个子走了进来,高建明顿时有点偏瘫--
小子不是别人,正是让自己和父亲遭遇美色尴尬的那个亲戚布置的饭局上的大哥大老板邱国建!
高建明心里瞬间涌现出无数个问号:豪哥说的能帮忙的人就是他?他貌似不是什么正道中人!公司的事情怎能由他来插手?
邱国建看见高建明也是一愣,脑海中短暂地快速搜索,也把几个月前的搞笑场面提取了出来。他随即面露微笑,上前握手,还拍着高建明的肩膀,问:“小老弟,还认识哥不?”
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应酬场面高建明也经历过多次,尴尬往事早已不再,现在的高建明俨然一个酒局老手,轻松自然地回答道:“哎呀,原来是邱哥!不不,按照我父亲和您的辈分,该叫邱叔才对呀!”
“别,别,我有那么老吗?哈哈,现在没别人在场不是,还是叫邱哥好了!”
一边的豪哥很是惊诧:“你们认识呀?”
“是呀,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和高老弟就相见恨晚了!这几个月不见,高老弟果然是华丽变身呀,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唉,后浪推前浪啊……”
大家落座,酒局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彼此聊着。酒是打开心灵的钥匙,说来也很奇怪,高建明对邱国建的好感随着推杯换盏逐渐增强,我们前面讲过的第六感发挥了作用,高建明决定不再兜圈子,开始讲到这次合作的事。他把他遇到的困难向邱国建详细介绍了一番,豪哥也在一旁帮腔,说什么做兄弟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何况邱老大就是“及时雨”,此事非得需要邱老大伸出援助之手不可。
总之一句话,高帽子除了绿色的之外,其他五颜六色的都通通向邱国建抛来。
一个人奉承,那叫溜须;两个人奉承,就叫认可。
邱国建做生意多年,在大事面前,虽然早已对这种嘴上抹蜜的话有了免疫力,但也架不住酒精和两个人相互叠加的奉承。最重要的一点,邱国建是普宁人,潮汕地区的人自古就有一种天生的能力--看面相。尤其是潮汕生意人,对面相是否相合非常讲究,而且都能通过第一次接触迅速通过面相、外形、肢体、气质等判断对方是否与自己合缘。如果在对方身上真的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那无论多赚钱的生意,都会避而远之。
我们前面也说过第六感,这种感觉在潮汕人身上来得相当强烈,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是一种自古以来的文化积累,总之,短短的时间内,邱国建也给高建明做了个系统的相面,结论是此人可信!于是当场打了包票,这事儿包在他身上。
常言道:酒越喝越厚,钱越赌越薄。当酒局上升到文化的时候,酒不再是酒,而是一种武器,一种力量。酒中也有颜如玉,酒中更有黄金屋,男女喝酒能乱性,兄弟喝酒则能浓情。
喝到酣处,邱国建豪情万丈,却突然抢着埋单走人。高建明不明所以,还和他推来搡去抢着付账,结果豪哥出面阻止,说邱哥性情中人,谁请客自不必计较。问题是高建明没弄明白,喝得好好的,为何邱哥突然要走。
邱国建一派大哥风范,拿起大哥大打了个电话:“……我不管,你是妈咪,我们又是老交情了,你不给我准备上好的货色,我可饶不过你啊……”
他回头又对高建明说:“兄弟,上次初会,知道你放不开,这次,我好好招待你一下,年轻人,会玩才会做生意!”
高建明突然明白了邱国建的用意,有酒地自有花天。
于是三个人加上邱老大带的两个伙计,又转战“花场”。这是高建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彻底的放纵,他不想在豪哥和邱老大面前表现什么清高、表现什么众人皆浊我独清,因为他隐约觉得,冥冥之中,和邱国建的缘分似乎是上天注定,他们在将来,可能会打不少的交道,那么现在,就应该表现得像个同道中人才行。
具体细节自不必表,无非是轻拢慢捻抹复挑。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入行的代价着实有点大--高建明的第一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送给了风月场,不论日后如何飞黄腾达,这却成了他一辈子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