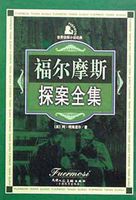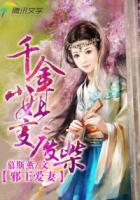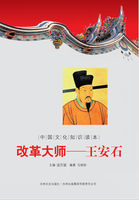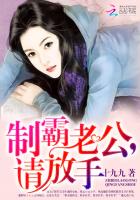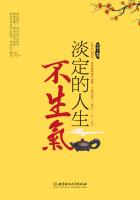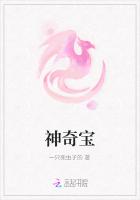老同学梁倩终于结婚的消息,我是在出差到上海开会时,听杭州来的一位同志说起的。会议结束后,我就特地跑到杭州去看她。
梁倩是我十年前大学时的同学,我们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坦率地说,我热烈地追求过她,遭到她坚决而委婉的拒绝。大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她因为成绩好留在杭州一家研究院工作,我则分到北方,后来又结婚,彼此很少联系,可我仍惦念着她的婚姻问题。
到杭州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在研究院问到她的宿舍地址,然后来到保俶山脚她那新搬进的中套新居。梁倩和她的新婚爱人正在忙着烧菜。见了我她又高兴又激动,说我胖了白了都快认不出来了。真的,睽违十年了,我们都已步入中年,梁倩不是也老了许多吗?可喜的是她却似乎比当年还要精神风采。她热情地向我介绍她的新婚爱人。我这才知道这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叫陆文秋,现在宁波地区的一个县里工作,婚期刚满,他明天就要回去。
我们还没说上几句话,呼啦啦拥进来三女三男六个年轻人。屋里立时便热闹起来。姑娘们剥糖,小伙子抽烟。端起咖啡杯后,又学着电视广告里的样子,一齐儿叫着“味道好极了”。从他们那种无拘无束如在自己家里一般的神态中,我猜想梁倩在单位里的人缘儿一定是很不错的。
唧唧喳喳地吵了一阵后,有个姑娘提议要新郎新娘讲恋爱经过,马上受到热烈的响应。但在叫谁讲时却发生了严重分歧,三个男的看中了梁倩,三个姑娘却揪住了新郎:
“梁大姐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清楚,她本来还想‘独身’呢!怎么到宁波出一次差就让你抢去啦?”姑娘们“攻击”得够尖刻的。“你用的什么‘秘密武器’,今天非坦白不可!”
这一说,三个男的也把目标转移到自己的“同胞”身上来了:“是啊!听说您和梁大姐见一次面后就决定了,那倒是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啰!”
新郎红着脸,一副很为难的表情。见梁倩从厨房走出来,他求援地望着她。但梁倩却深情地看了他一眼:
“你就说吧!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还都在恋爱呐!年轻人,让他们听听也好。”她又朝我笑笑,“这又是我最好的老同学,你就什么都可以说的。”
新郎仍在推辞。看来,他是不大善于言词的,或者,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吧?更何况,叫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在这帮刚出校门的大学生面前谈恋爱经过,毕竟有点难为情的,换作我恐怕也会说不出口的。所以,尽管我也很想知道他们那迟来的爱情的奥秘,但也终于忍住了。于是我便说:“算了,咱们还是聊聊天吧!”
“不行,不行!”众人一齐反对。
就这样,新郎用沉稳、平缓但又充满回忆的语调说:
“是的,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不可能直到现在才开始接触爱情的。既然你们这么希望听听我的恋爱经过,而且甚至想知道我的过去与‘爱’有关的事,我就讲讲我过去的爱情故事吧!也许,你们听了会感到有点‘刺激’,但我想,既然是爱情,就不应该仅仅只是刺激······”
我的父亲是宁波城里颇有名气的资本家。他先后结过三次婚,前两次都丧妻而未得子。直到佣人出身的我的母亲成为他的第三个妻子后,我才来到人世。但到我三岁时,父亲几经矛盾,终于下决心把他那经营多年的两家棉纺厂挂上公私合营的大红牌子,以后不久,却带着一个民族资本家对新生活的怀疑和惶惑,以及对寡妻孤儿的忧忡离开了人世。但这担忧在他死后成为多余。我们既不用为经济而发愁受到当时政府保护的资产股份,后来则是利息,使我们母子俩过着一般人无法过到的丰优生活,我那出身贫寒的母亲甚至为此感到惶惑不安,所以好几次真心诚意地捐献出数目可观的钱。也许正因为这样,她被政府表扬,还作为统战对象的进步人士,政治上也受到了礼遇。所以,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是在无忧无虑的幸福的蜜罐中度过的。
但这一切到1966年也就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就结束了。对此已用不着多说,大家都可以想象。总之我母亲被揪了出来,家被抄,银行利息被冻结。我也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被学校当做“危险学生”。连原来几个很要好的同学都歧视我,至少也对我避而远之。
然而在这厄运之中,却有一个女同学仍然把我视作知己。她和我从小就很要好,经常往来,甚至一道进中学时我仍叫她的小名“豆豆”,为此曾引起同学们的笑话。她的家庭和我完全不一样,她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但她却偏偏不避嫌,还安慰我:“你家没问题,我爸知道有问题也没什么!”
在当时能受到这样的安慰,我对她的感激是难以形容的。她的善良、真诚、富有同情心使我对她已有的好感又加深了许多。就这样,我们更亲密了,可以这样说,是恋爱了,而且是相当纯洁、相当真诚的。只是我们瞒了任何人,甚至包括各自的亲人。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迎来人生的大转折的。1971年春天,我和她跟其他几十个宁波知青到奉化四明山区插队落户。我本来可以分配到相比之下近一点、条件好一些的市郊的,但因为不愿离开豆豆,所以和人对调,去了奉化。去之前我俩约法三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两人决不变心;在上调之前,都严守秘密,不公开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
我们先到公社所在地,那是一个名叫“驻跸”的小镇,名字很古雅,望文生义,该是皇帝驻扎过的地方。这很引起大家的兴趣,都想领略一下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哪个真命天子的余泽。吃过中饭后,分到别的大队的人都被接走了,惟独我们六个要去的“像章”大队还没来人接。趁这等待的工夫,大家便到镇西北的一个小亭子里观赏。亭子小,而且破败不堪,一块据说是皇帝题词的石碑已被砸得粉碎,想必是前几年破四旧的成果。想到皇帝也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我们这些年轻人便都有点感慨。
就在这地方,我第一次遇到她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姑娘。
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不,应该说很难描述,倘若有谁把它写到小说或电影里面去,准会被说成是自然主义或者缺乏美感幸而我现在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如实地回顾当时的情景当时我想“方便”,正为找厕所而发愁。并非这附近没有厕所,相反却多得俯拾皆是。大路两旁隔几丈路就有一座,说句不恰当的比喻,就像眼下街上的地摊那么稠密。只可惜实在太不雅观:一律面朝大路,毫无遮拦;又一律都是一顶草棚,底下一只粪缸,上面放一只木架子,可以并排坐两个人,就像旧时那种双人太师椅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人管它叫“石造”。
我不由得犹豫起来:坐在这种“太师椅”上,脏且不说,单是面对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就够使人为难了。但到底因为生理所迫,便也无奈而为之。“人乡随俗吧!”我这么鼓励自己,再说,连这么一个“关”都过不去,还谈什么“接受再教育”?
正当我终于下定决心,选了一架稍为干净一些的“太师椅”坐下去后不久,不料,突然撞进来一个提着扁担的女人。我吃了一惊,连忙低下头,偏过脸。但我却发现,不,应该说是感觉到,那女人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这一下,我犹如一个被人发现的正在作奸犯科的胆小的反徒似的,逃又逃不脱,不逃又不行当时我是一点也不知道此地的风俗:厕所是不分男女的,甚至两个上了年岁的异性熟人碰在一起,坐在同一只“石造”上互相递烟,家常里短地聊天也是毫不稀奇的事我只觉得如坐针毡,吓得“屎不滚尿不流”了。但事已至此,也毫无他法,只得硬着头皮,缩成一团,渴望她赶快离开。幸好她很快就完事当然在我看来已是够慢的了拿起扁担下了地。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放胆抬头一看,见她走开几步,忽然又掉过头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这位阿哥,你可是去象鼻的下放青年?”
“不!去像章!”我别转头,恶声恶气地说与其说是回答她,倒不如说是快点“赶走”她。
“唷!躲到这儿来了!害得人家满裤裆乱找!”她说了这么一句通常只有粗鲁的男人才吐得出口的脏话,“人哪?咋只你一个?不是说有六个吗?”她扭头四顾,目光朝向不远处的亭子,“哦,在那边呐!”又回头对我说:
“俄是来接你们的‘像章’就是象鼻,那是前几年才起的鸟名字!”说完,就往亭子跑去。
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委实使我惶悚交加,直至后来回到亭子里,心里仍然余悸未消,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幸好什么事也没有。她和我的几个同伴正说说笑笑地在绑扎行李。我这才仔细地端详她:这是一个二十余岁的姑娘,穿着一件粗布直襟的旧棉袄,裤子上也补了好几个补钉;五官长得很端正,甚至可以说很漂亮,高挑的眉梢和棱角分明的嘴唇更显得起眼,那脸上透出一股少有的野气,不,甚至可以说是邪气当然,这也许是刚才在“太师椅”上所留给我的印象吧?
扎好行李,她把六人的铺盖全都串在扁担的两头,挑起来就走。
不知是谁问了一句:“怎么不派一辆手拉车来?”
“能拉车,还会叫象鼻?”那姑娘拍拍肩膀,“别说这么点东西,再大再重也用这个!不信?旧年队里去天台买打水机,手拉车拉到这里,再抬进山去,还得把车子也陪着扛回去呐!”
一上路;果然是崎岖山道。不一会,大家就气喘吁吁了。但见那姑娘挑着铺盖跟在后面,又都觉得过意不去。我提议分开来大家轮流背背,但她却执意不肯:
“俄不要,俄吃得消,俄是挑惯担子的!”她一个劲地拒绝,见大家说得多了,又干脆说:“俄不是白挑的,俄是赚‘分’哩!”
她把“我”说成“俄”,那是道地的奉化方言想必大家都看过电影《西安事变》吧?演蒋介石的那个演员不是学了几句奉化话吗?可惜没把那个“俄”字说出来,不然恐怕更惟妙惟肖了。但当时我们这些宁波城里人听了都感到很有趣。特别是豆豆,许是我们中间惟一的女性吧,所以尤其和那姑娘亲密,不时和她说说话。
“俄姓黄,俄村里人都姓黄,俄叫是男。”
“是男?是男?”我们中间有个叫小胖的打趣道,“你是男的啊?”
“看你说的,有个‘男’字就是男的了?”豆豆讥讽道,“那么肖楚女烈士是女的啰?李赫男该入男子乒乓球队了?”
大家哄地笑了。小胖红了脸。那姑娘虽然听不懂大家的意思,但也看出小胖难为情的样子,便笑笑道:
“是啊!俄阿爹就喜欢有个儿子。俄老大,取这个名;俄阿妹叫象男,都有‘男’、俄阿爹说,要是俄妈不死,还能生,不管怎样也要盼个真的男其实嘛,俄就不管什么真男假男,俄就把俄当做了男劳力呗!”
由于从小生长在城里,从未和农民接触过,可以说,这个泼辣、直爽的山里姑娘,是我第一次直接遇到的乡下人。我忽然觉得她很可爱,很有趣,连刚才在“太师椅”上的难堪、尴尬的情绪也烟消云散。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姑娘,在我以后的生活海洋里,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浪!······
进村已是傍晚。真是名副其实。一座陡峭的,形状酷如大象鼻子的山峰下,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十多个自然村落其实每个村落也只有六、七户人家使人联想到世界地图上南太平洋群岛那星罗棋布的无名小岛。
我们先到大队部等候安置。来前我们听说知青下乡按例是住在大队的专门房子的,但这里的房子还没有造,所以只能把我们暂时分头安排在社员家里。对此我们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这样更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谁知道就是在这一问题上使我尝到了下乡后的第一个苦果:包括豆豆在内的其余五个人都很快落实下去,惟独我却被晾了起来,原因是我出身不好,没人肯接收!
这真是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原以为离开城里,离开家庭,便可以做一个自由人,平等人,不想在这里仍被归人另册,受到歧视!
小胖等四人都被领走了,豆豆却仍伴着我。她虽然幸运地分到革委会主任家,但又替我难过。还有那个替我们挑行李的是男,也显出很着急的样子,焦虑不安地望着我,后来,又跑到隔壁队干部们正在讨论的会议室去。过了一会,她又乐颠颠地跑回来:
“俄跟他们说好了!这位阿哥就到俄家去走!”
跟着她去她家的路上,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往往不大会注意别人对你的尊重的;只有在遭到冷落,受到歧视的情况下,才会真正体会到“尊重”二字的价值。我就像一只离窝失群的雏雁,忽然被一个好心人救起,顿时又满怀希望了。
土墙围起的独门小院,一排三间小屋,另加左右两间厢房,这就是是男的家。我们刚进院门,就听见里面一阵骂声:
“你塌我的台!你这贼小娘鬼,俄要了你的命!”
我吃了一惊。又见屋里跑出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是男一把扯住她:
“象男,出什么事了?”
“俄放学回家拾到一些芋艿种,是队里种剩扔的,可阿爹骂俄······”
“没事!”是男朝我笑笑,“俄阿爹死要面子来,你先歇歇。”说完就进屋去。,
我坐在天井的石凳上。那小女孩含羞地看着我。她长得很像是男,犹如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我正想逗她说说话,屋里又传来说话声:
“什么?住个人?你这是干什么啊!”
“你放心,队里付俄们房租······”
“俄不是指这,俄是怕惹麻烦。”
“你听俄说啊!人家还不让来俄家呐!规定要住在正式的贫下中农家。俄是好说歹说才答应这也是看得起俄家啊!
“看得起咋啦?俄不要他们看得起!俄算坏人啦?俄是地富反啦?俄自家看得起自家!”
“阿爹你轻点好不好?你不要这面子?俄要!俄已经答应人家了!再讲,人家成分高,没人要,你总得给人家一个面子嘛你平时一口一声面子面子,碰到人家的面子,你就死人不管了?”
“这倒是······那,那就住下来吧······”
听着听着,我心里顿时变得冰冷,就像一个冻得发抖的人跑进热澡房,却兜头被泼了一盆冰水。原来她家不是“正式”贫下中农!说实话,当时我虽然出身不好,有时甚至有点自卑心理;但也不知为什么,碰到那些同样是出身不好的,虽不致到歧视对方的地步,却又往往是避嫌的。如今,居然让我落到这户“非正式”人家!怪不得她那么主动地把我请来,还不是以我来装点门面?即使不往这方面想吧,至多,也只是怜恤我罢了!
想到这里,我一发狠,提起铺盖就要往外走我根本没想过该往哪里去,这我已不顾了······
“俄来拿!”是男兴冲冲跑出来,接过我的行李,“你先去吃饭,俄给你整理房间去!”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院子里。
“欢迎,欢迎!”
屋里又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汉子,瘦小精巴的个子,脸黑得像千年古铜发了锈。他满脸堆笑地对我说:“反正俄家西厢房空着,正好让你住你看得起俄,俄脸上有光,三生有幸······”
是男在厢房整理房间,还吆五喝六地指派她的妹妹。她父亲陪我吃饭。菜很差,咸菜咸笋咸萝卜。但那汉子却很是热情有礼,一反刚才我听到的他父女说话时的那种冷漠。话语中还不时夹杂几句旧社会官场上或是生意圈内才有的客套话,诸如问我“尊姓大名”,还有“不胜荣幸”、“多多包涵”之类,说到她的女儿是“小女不才”,很显出和他那纯粹山里人的打扮举止不相称。这便益发使我纳罕:“这到底是怎样一户人家?”
吃好饭我来到西厢房。是男正在搭眠床,忙得满头大汗的。我有点过意不去,但又插不上手。
“你放心住在俄家吧!”她朝我笑笑,“俄阿爹是个好人他很看重你呐!”
显然她在暗指刚才他父亲冷淡我的事了。这一来倒使我感到过意不去,但又不便明说。便扯开话头问:
“你爸过去是干啥的?好像很有知识呢。”
“知识?你是指说话酸溜溜是不是?”她“扑嘛”一笑,“你别上他的当!他只对你这号人说说的。说什么俄是‘小女不才’俄是她大女!‘不才’?俄当然‘不才’罗!读了三年‘陈书’,哪来才?俄也不要什么鸟才,又不是让俄去做毛主席。活得畅快就是!还有,什么‘三生有幸’,屁!这辈子都‘幸’不了,还想‘幸’三世?其实哟,他也就只能诌上这么几句,还不是从什么南京总统府拾来的青梅子当然,亏得才只这么几句,要再多些,更让人受不了啦!······”
“总统府?”我吃了一惊,悚然地问:
“你爸,他在······总统府干过事?”
“是啊!村里好多人都干过呐!”是男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罪啦?谁让老天往他们鼻子底下开了个缺口,害得人人都得吃饭!连黄阿富都去过!可偏俄阿爹倒运,把他‘整理’出来了全是黄阿富报复的,诬他的!······”
是男正说得气头上,她父亲却走了进来。“是男,你别胡说!”他瞪了女儿一眼,又歉然对我道,“小女不才,说话没遮拦,请你多多包涵。”
“俄胡说。”是男咄咄地说,“不是他诬你,那你真是坏人啦?”
“俄怕你闯祸呐!”作父亲的小声道。
“你就是胆子小!俄跟这位阿哥噢,你叫陆文秋是不是?俄跟他说说又有什么啦?俄看他就是好人,不然也不会住到俄家来了。对好人就得说实话,还藏藏匿匿干嘛?再说,反正横也一刀,竖也一刀,怕个啥?俄才不怕!他黄阿富有权,‘刀快不怕头大’;俄有理,‘头大不怕刀快’。俄就要骂这狗东西,自己头上生疮,脚底流脓,还专门整治人!好啦,好啦,阿爹你怕你就别听吧!”
“你别怕,放心住在我家吧!”是男说完这些之后,又像是怕我不相信似的,“俄阿爹是好人,他从没做过坏事。俄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你可去问人家!”
我虽然没有去“问”,但不久就证实是男说的都是“实话”:尽管当时她父亲莫名其妙地被安了顶“反革命”的帽子,但村里大多数人却仍把他看做“好人”。
于是,我便“放心”住了下来。
黄家父女待我很是热情,处处照顾我。我们下来后所干的第一种活儿就是砍柴。这本是山里人最基本的活儿。但对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却是最难的了。拿起柴刀,只半天手就起“灯泡”,又不会捆柴把,肩上更压不了柴担。这一切全让是男父女给包了。当时队里砍柴虽然是“大锅饭”,每人一担,但又要过秤。黄大叔见我力气小,便把我的柴担分一些过去,挑到柴场附近,又重新分给我。“后生家太轻了要塌台,不能失面子。”但即使到柴场的几百步路也够我受的了。后来,是男干脆说:“有什么塌台的?人家本来就不会挑嘛!”说着夺过我的柴担,大模大样地挑去过秤:“陆文秋的!他力气小,俄帮他挑的。”社员们听了笑笑,也没说什么。
我在是男家搭了一个缸灶做饭,为了图方便,常常烧一次吃几顿,还常吃剩菜。是男就经常端点菜来。次数多了,我很过意不去。她却说:“谢什么?俄愿意的嘛!”或者:“人家真心给你,你再客气,就反而对不起俄了!”弄得我再也不敢推辞。
那时象鼻很苦,收人低,一般人家除了填饱肚子,极少有鱼肉荤腥。社员们干活时,常常开“田头宴会”,议论吃,什么下饭味道好,什么东西几年没尝口等等,说得津津有味,而且又风趣、诙谐。有一次公社来放《红灯记》,前面放映了一场新闻纪录片,是招待西哈努克的宴会。第二天的“田头宴会”上,人们就猜起电影里真宴会上的蹄髈的大小来,有的说有十斤,也有说起码有十五斤的,争议了半天。我忍不住说这种宴会也许不会有蹄髈,非但没一人相信,反而引起了“公愤”:“瞎讲!介大国家请外国皇帝吃饭,怎么可以没蹄髈?就这么小气啊?这不塌我们中国人的台?”弄得我又好笑又无法声辩。
是男家也很困难,早已是“三年不知肉味”了,我就常常在村里的代销店里买点肉之类送给她家。每逢这时,黄大叔总要客气一番,千谢万辞的,甚至说也不大想吃。可是男却像站在我一边似的,“阿爹别假客气了!昨天还唠叨喉咙都燥死了,还打肿脸充胖子呐!文秋阿哥真心送我们,你不收,他心里还不安呐!文秋阿哥你说是不是?”说得她父亲直脸红,“你看你看,小女不才,疯,不懂礼数,请你多多包涵。”
“你啊!客气起来就漏出酸话来了!”是男笑嘻嘻地说,“俄不疯,俄是吃竹笋长大的!不说弯弯话!”
黄大叔说她“疯”、“不懂礼数”,不能说没一点道理。说实话,连我都觉得她直率得有点过分,尽管那性格是非常可爱的。她仿佛不知道自己是个姑娘,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女人似的。且不说一切男人干的活儿她都不让,耕田耙田,迭草篷上屋顶全都能干,敢干,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像男人那样到象鼻潭洗澡。村里自古以来的习俗,男人可以到潭里游泳,赤屁股光身子也无所顾忌,而妇女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没人敢去,她们通常关在家里用木盆擦擦身。而是男却敢冒村里之大不韪,偏到潭里去游泳,结果男人们没有办法,只得到村后的水库里去洗,把个象鼻潭让给她“独霸”了。这事我们这些知青开头不知道。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小胖几个人去象鼻潭游泳,见突然跳下一个女的来,一面游着一面叫着:“好,总算有人作俄的伴了!”慌得我们别转头不敢看她,她却水淋淋地钻出来,还说笑我们:
“连你们都怕?还说城里人见过世面,原来也是躲在裤裆里的虱子!还不是一样的人?只不过比俄多只‘麻雀儿’罢了,有什么希奇?俄还比你们多两只‘馒头’呐!”说得我们逃也似地溜走,她还在后面哈哈地笑:“走光好!俄独个儿更舒服!”
我们几个住在不同人家的知青,常喜欢到我的宿舍来聊天,扯一些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山海经。是男也总是过来听,有时见我们说得有趣,她听不懂,就又羡慕又丧气地说:“唉,都怪俄只读了三年‘陈书’!”她说的“陈书”是留级的意思。她小时也上过学,但由于母亲早死,上学时便得带妹妹去听课,所以读不好,留了两次级,以后就索性辍学干活了。但尽管她只读了三年“陈书”,我却发现她相当聪明,慢慢地她也能听懂我们所说的不少知识,还常插上嘴来提一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总是很幼稚,但却大多很奇特精彩,妙趣横生。
“俄问你们一个问题,”有一次我们闲谈中说到南方语言的差别时,她忽然插嘴问:“为什么台州人说的话和俄们这里人不一样?但台州的鸡叫起来却和我们这里一样?这是啥道理?”
大家听了满堂大笑,我也忍俊不住,说:“那当然啊!不但台州,连美国的鸡叫跟中国也一样呢!可说话却听都听不懂。”
“俄是问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都面面相觑。虽然都知道这是一个极为平常极为简单的问题,甚至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一下子要说出个“为什么”的道理来,竟不是那么容易。刹时里,大家都难住了。
“怎么?你们也说不上来?俄来说说看怎么样?”是男扑闪着双眼,正儿八经地说,“俄一直在想哩!不但鸡,其他动物像羊啊,狗啊,牛啊,都是这样的,惟独人却不一样。什么道理?俄说,那是因为鸡牛羊狗都没有失去本性,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发出来的声音当然一样啰!人呢?却变了,失去了本性,就不能想怎样就怎样,自己把自己缚住了。拿女人家洗澡来说,女孩可以到河里洗,大了就得躲在屋里,谁都知道河里舒服,却偏要自己找苦吃。其实,人也不是一生出来就这样的,小孩一落地,哭声都一样,这就是本性。大了就变了。那天俄看见阿利嫂四岁的儿子在门口喂鸡,自家鸡人家鸡都在一起,他问大人,‘人家鸡要不要喂?’阿利嫂给了他一巴掌,‘笨蛋!怎么喂人家鸡?’其实小孩没错啊!鸡嘛不管谁家的都想吃嘛!是大人心坏俄也不是说阿利嫂坏,换成俄也是这样的。俄是说,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却最坏,比鸡,比狗都坏。再拿说话来说,不但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话,连同一地方人,甚至同一个人,碰到不同的人,也会说不同的话俄是指不是真心话,而是假话,不像鸡,一张口就是一样的声音,从来不假叫······俄也在想,这也不能怪人,也是没办法嘛!说真话的人要吃苦头啊!拿俄阿爹来说,当年要是为了黄阿富的事不说真话、实话,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被‘整理’了······”
听了这段长长的解答,我们几个人都相顾默然。她说的那番道理虽然不那么确切,甚至有点文不对题,杂乱无章,但却发人深思,细细嚼来简直有点哲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