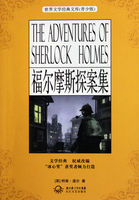“他不是带着几宫娘娘去了行宫么,就让他在那儿多呆会儿。”玉琉珖戏谑道,“三哥回去,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会让事情变得麻烦一点而已。
“可赤丹王子……”玚仍有些不放心,赤丹虽说带了数十万之众,亦可说是东胡的精锐之师,若是赢了那还罢了。若是输了,那又该如何?
“玚,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婆妈了?”玉琉珖轻笑了声,浅啜一口那血色的酒酿,接着道:“也许,玥比你更加胜任随身亲侍这一职务。”说完,回头看了眼站在凤箫身旁玥。见他毫不理会,又笑起来。“你们这两兄弟还真有意思。”见着玥的身子僵了僵,才终于满意。
“如何,你守着你的主子也好几日了,不累么?”将手中的琉璃盏递过去,“来陪我喝一杯如何?你哥哥平日里太一板一眼,我看得都烦了。其实,以你的身手,何必在这里守着一个女人。”
“王爷……”玚在一旁很无奈的唤了一声,看了眼站在那边的玥渐渐黑了脸,终于垂下肩去,闭口不语。
“凤箫,你可知道,三哥为何要调掉马头,回燕然去么?”也不等旁人回答,便接着自顾自的说道:“三哥明明如此的重视小姐,不惜为佳人大兴兵事。为何事到临头,却又退回燕然了呢?”仍是无人回应,屋内只有灯火摇曳。一只灯蛾轻扇翅膀,绕着烛火飞舞了一阵,在墙上投下一抹黑影。随后,只听“呲”的一声,那灯蛾便从空中坠下来。落到地上,扑打着双翅,挣扎了半刻,便再也不动了。玉琉珖看得入神,心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过了半晌,又道:“其实我早料到,三哥定会率军前来。而且,会来得很快。所以,这几日,我夜夜都睡不好。你看,我准备了这么份大礼给他。”长身而起,也不在意华衣委地。斜倚窗边,天上月渐西沉。玉琉珖眼中露出一抹倦色,“我以为,凡天下王者,都如父王那般,为保江山可以牺牲一切。可是,你却想要拥有一切。为你的绝色美人,为你的亲信忠臣,为你的黎民百姓,为你的璋辞国祚……你好像一切都为了这天下苍生,实际上,却只是在为自己。”
转过身来,对凤箫道:“凤箫小姐,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人。你爱他吗?如果你知道十四年前,他对你的家人都做了些什么,你还会爱他吗?”轻笑起来,“我好像忘了,你原本就不爱他。爱,可以让一个软弱的人变得无比强大,也可以让一个强大的人变得无比软弱。三哥原本是一个强大得,让人觉得可怕的人。可是,现在,我抓住了他心头最软弱的一块地方。怎么办呢?”但不管他如何说,凤箫都只是端坐窗前,不怒不笑。
“如果,三哥见到这样的你,他会怎样呢?”伸出手来,将玥手中的剑推回鞘中。清脆响亮,震得耳膜发胀,似乎要刺破这安宁的夜晚。还是一惯从容浅淡的笑意,玉琉珖轻声叹息:“不管你试多少次,结果都一样。”然后摇了摇头,叹道:“其实,你根本不用着急,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回到,三哥那里去。”
宁延台轻轻呼出一口气,他觉得四周太安静,静得连他的心跳声都听得一清二楚。伸手,在胸前摩挲了下,隔着厚厚的犀甲,指尖也能清晰的触到那如鼓的脉动。
自从赤丹被子夜一剑刺中,那些胡国蛮子就像发了疯似的,杀红了眼。他们带的五万守军,已是所剩无几。他好容易在陆风的掩护下,带着一队人冲出来。而胡军的攻势却在此时停了下来,世界便像静止了般,连呼吸都变得沉重。抬眼,看看远处的天空,已渐渐泛白。他知道,当阳光在地平线上划出第一道金痕,胡军便会如浪潮般的涌来。这样的地形,恁凭如何的绝世高手,怕也是很难逃出升天。
也许,他只能向上天祈求,赤丹在此时已经一命乌乎。没了主帅的敌军,哪怕再多,至少他能拼死将其他人送出去。
不远处,陆风正在默默的摆弄着手中的火器。这东西的确威力无穷,只是不适合近身战。也许,宁延台在心里想着,等这场杀戮结束后,他可以向今上提一提,将这些火器改良改良。若是,他还有命活的话。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苦笑了下。
悄悄的看了眼身旁的延楼,也许是天色朦胧,让他的脸色也无法看清。
“二哥……”小心翼翼的唤了一声,却又不知说什么,把眼光投向他身后模糊的身影。那里躺着的,正是重伤的子夜。翠小小的身子蜷缩在一边,像是睡着了。
想到翠,延台不禁有些疑惑。当子夜伤重不醒,众人都以为她回天乏术之时,翠却从怀里掏了颗药丸塞到子夜口中。原本僵青的脸色,竟然又渐渐透出生气来。看着翠熟练的为子夜搭腕号脉,延台竟不知心中是喜是悲。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竟比战局更让人手足无措。
“子夜小姐被震碎了经脉,原本靠着我的丹药便可将之修复。虽不能变得如从前一样,但只要好好将息,养上一段日子,大可以行动自如。只是……小姐腹中的胎儿怕是保不住了。而且,小姐自身还带着一种毒素,虽短时间不会制命,却也是深入骨髓。”翠说着,略有所指的看了眼延楼,接着道:“这样的毒,倘是平常,不会轻意让人察觉。若是顺利,只会造成妇人小产至死的假像。”
延楼身形顿了顿:“什么叫做,‘若是顺利’?”似乎为将要知晓的事实,露出无比痛苦的神色。
翠却没有回复他的问话,径直说道:“现在,这丹药也只能保住子夜小姐一息尚存。若要将她救活,怕只有传说中不周之巅的仙草了。”
“你刚刚不是说,丹药能保住她的气息么?”延楼搂着子夜,怕一用力怀中的人儿就会灰飞烟灭一般,身子止不住的轻颤。
“但,这跟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此时的翠,露出与以往不同的严肃神色,“你可以不相信我,但宁大人应该知道,是谁造成这样的局面。”
是重伤子夜的赤丹?是帅军征讨的今上?还是故意挑衅的静王爷?
延台又悄悄看了眼身旁的兄长,自从那之后,他只将战势做了一番部署,便再没有开口说话。而眼前,也只是静静的监视着敌军的动向,对子夜竟是不闻不问。延台不禁在心里问:二哥,为何你看起来并不悲戚,亦不愤怒?你真的,爱子夜嫂子么?
“三弟,”嘶哑的声音从身旁传来,延台不由得一震,便又听到他说:“敌军若是攻过来,不可恋战,你尽量带着兄弟们冲出去。只要再坚持一阵子,他们便会回转胡都。”
“那你呢?”延台小心翼翼的问道,想从他脸上找到蛛丝马迹。
延楼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轻声道:“我想,我这个将帅的头颅,应该能将他们拖延一段时间。但也不会太久,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准时机。”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那……”延台话还未说完,便被延楼一把按住,生生的顿住了。
“别忘了,我们是璋辞的将领,自有责任。”见延台还要说什么,又紧接着道:“你放心,二哥不会那么轻易的说出那个字。”
“责任……”延台心中想着,那子夜嫂子又算作什么?他竟不知道,自己敬重的二哥如此铁石心肠。
天边渐白,远远的传来胡军冲锋的号角。延台听到刀剑出鞘的清脆声响。延楼从他身边站起来,手中的长剑在晨光下泛着冷冷青光。当阳光将天幕与大地一分为二,将天空染成青蓝紫红,延台看到,那个肩负着无比荣耀的男子,尤如从天而降的神祗,英勇而威武。他好看的脸庞带着肃杀之气,只是,两鬓如雪。
接着,他又听到,那个男子轻轻的开口,说道:“不周之巅么……”
“二哥……”延台突然被哽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如何的用情至深,让你一夜白头?
玉璃珲看着满地尸横,心中发狠,斜挥一剑,将迎面冲来的敌将砍倒在地。喷涌出来的血液,还带着温热,飞测到犀甲之上,很快与之前的血迹融混到一起,将他的衣衫盔甲染红。阳光下,他一袭红衣炫烂无比,如浴血战神,让人敬畏。
当他赶到颖水之时,只见到被踏毁的营帐,以及遍地战死的将士。那一方土地早已被血浸成红色,浓重的血腥味让人作呕。
“陛下,宁大人并不在这里。”苍玄青立在他身后,一袭青衫在风中轻轻飘荡,面色亦甚是淡然,丝毫没有一夜赶路的狼狈模样。
玉璃珲只是微微挑眉,静待他的下文。
苍玄青轻抚了下胸口,沉沉的咳喘了几声,又接着道:“之前接到细作回报,胡军统帅赤丹被子夜小姐重伤,现下生命垂危,已被连夜送回胡都。留在这里的,只怕是想为王子报仇的发狠凶徒。不过,经过一夜苦战,宁大人所率之宁军怕也是伤亡惨重。想来,现下他们应该已退至燕然关外。”平缓的语调,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眼前的情势,并不如他们想像的那般危及。
“留下一队人,不分敌我,将这些将士好好安葬。”将手一扬,大声道:“其余各部,跟随朕御敌燕然!”
快马加鞭,不到半刻便将胡军截住。这些胡蛮看似凶狠,却战得毫无章法。想是,主帅不在,又见对军只得几千人马,便一味的求狠杀戮。竟不想,如此失了先机,被延楼他们拖至燕然关外。等他们想要将璋辞军队一举歼灭时,却不想援军已至,自己反而被两面夹击,悉数被擒。
玉璃珲骑在马上,看着战场两军死伤无数,看着被俘敌军面露恨色,看着延台一脸悲伤,看着延楼两鬓斑驳。不禁闭了眼,长叹一声:“静王!”
战争。
孰输?孰赢?
正是余阳西沉,树影婆娑之时。胡国王宫之中,那曲徊婉转的长廊,在精致无比的大理石地面投下浓墨般的身影。玉琉珖披了件月白长衫,斜倚在雕栏之上,衣襟大开,露出精壮的胸膛。胡乱束在脑后的长发垂坠下来,散得慵懒闲散。修长的手指扣住一盏琉璃杯,轻轻晃动其中珀色液体,发出阵阵醉人香气。望着渐露颓色的天际,目光变得悠远。
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是这样的一个黄昏,他躲在鸢尾丛中轻声哭泣。母妃仙逝不久,他便看尽了世态炎凉。父皇不爱重他,兄弟姐妹也冷眼相待,就连宫人们也轻慢他。虽说他是皇子,但没了母妃的庇护,他什么也不是。小小的他,并不懂得宫中的险恶争斗,却也知道了恨。他恨那些阳奉阴违的奴才,恨那些自私自利的血亲,恨那个为了巩固中宫地位假意仁慈的皇后,更恨高高在上冷血无情的父皇,还有他一心只想着如何讨父皇欢心的天真的母亲。其实,他最恨的,却是弱小的无法保护母亲的自己。
记忆中的母亲,是美丽而温柔的。他常常坐在长庆宫中那开满繁花的庭院中,看母亲甩着长长的云袖,舞出无比华美的身姿。回眸,转身,折步,玉指轻扬。只是那样美丽的母亲,却总是带着淡淡的哀伤。她有时会看着他出神,他知道,母亲其实是在看父皇。他虽小,却也懂得,父皇并不是他一人的父皇,而美丽的母亲也只是父皇后宫三千佳丽中的一人。他们之间,隔着太多人。
父皇很是宠爱德妃娘娘,常常与她游湖赏荷。而对德妃所出的三子,更是青睐有加。宫中早有传言,父皇欲废长立幼,将大统传与这宠妃之子。
“皇后娘娘中宫之位稳固,太子亦是颇有才华,就算陛下如何宠爱,也不能坏了祖宗家法。”
“皇上将三皇子无时不带在身旁,同出同坐,教他治国之道,太子却让皇后娘娘自己教养。再说,这祖宗家法也是自家的祖宗家法罢了。”听着宫人的闲语传言,母亲也只是静静的翻看乐谱。仿佛,这宫中之事,与她是全然无关。
就是这样的母亲,却也难逃红颜的薄命。
那日,皇后传话,说是镜湖中芙蓉姝美,邀母亲一同赏花。且说,圣上亦会驾临。母亲穿着她最爱的宫装锦服,高高兴兴的去了。却不曾想,赏花宴之后,母亲一病不起,医石无用,只拖了几日,便香消玉陨。他记得,皇后前来探病时,脸上挂着那若隐若现的笑意。想到宫中之前,几位妃嫔也是如此,薨逝得离奇,顿时觉得母亲死得冤枉,便将所想告知了父皇,却被训斥了一番。
而那时的他,除了躲在花丛中悄声哭泣,还能如何呢?
轻笑一声,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那芬芳的花果香气萦绕唇齿,最后沉淀出厚重的铁味。玚持着那玉嵌琉璃壶,静静的为他斟酒。那艳红的汁液缓缓的倾泻而出,在杯中不停回旋,发出清脆的声响。
“你看,”天边残阳退尽,月上枝头。玉琉珖一手指着天上明月,风将他月白的广袖拂起,像极了夜空中的一片云,轻轻悄悄的飘荡。“那天,也是这样的月亮。”
那天,也是这样的月亮。他躲在鸢尾丛中偷偷哭泣,却遇到了雪柳。她瘦小的身子被老宫人拖拽着走过来,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那时的雪柳并无姝色,可以说甚是狼狈,眼睛也哭得红肿。那时的雪柳还不是雪柳,也没有现在这“第一美人”的名声。即便如此,却仍是他喜爱的雪柳。因为,那时他遇见的是那样的她。
那时雪柳在宫中供职,服侍一位不得宠的贵人,境遇可想而知。那日正逢贵人心绪不佳,找着借口要处置她。玉琉珖遇着她时,正要被老宫人遣去浣衣局。他虽不被看重,却也是位皇子,开口要个宫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也正是如此,他才知道,他是位皇子。就算是父皇不爱重他,兄弟姐妹冷眼相待于他,宫人们轻慢他,他仍旧是皇子。他有他的身份在,从一出生就注定了的。所以,他第一次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他将雪柳带回长庆宫,赐予她名号,他将以前他没有得到的情感全部倾注在她身上,让她得到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幸福。
他想,他确是爱她的。
只是,现在想来,若是当初雪柳没有跟着他,也许现在又是另一番境况。
“玚,你可有后悔过?”
“王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