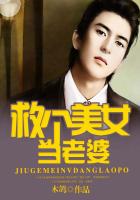“你看,这便是我们的圣主。”苍玄青走过来,与她并肩而立。看着玉璃珲接过珀递上的一盏酒,上前几步,越过众人,轻挑锦袍跪下来。这里,正是璋辞儿郎浴血的战场。玉璃珲举杯,以慰在天之灵。倾杯,黄土上划出一迹墨痕。
“这一段历史,定会被后世所称颂。”
“而你,便是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不是么?先生。”
苍玄青转过头来,笑道:“是了。”顿了阵,又道,“你都记起来了?”
凤箫点点头,“先生何故要骗我们,蛾儿哭了好久。”
“那丫头从小被我惯坏了呢。”苍玄青失笑着摇头,“箫儿可怪我?”
“先生从小教凤箫凡事平静以待,且,若不是先生,凤箫怕早就饿死街头了。”凤箫转过去,看着远处那抹玄色身影,道:“有些事,现在想起来,却不知道,好也不好。”
“那件事,原来你还太小,不敢说给你听,才封了你的记忆。现在你也大了,自然能够分辨。如何决定,但看你的心意。”
“原来如此。”凤箫点点头,以前不明之处,现在终有了答案。
“话虽如此,”苍玄青顿了顿,慢慢说道:“他为你做了这许多,望你不要负他才好。”
露台上,玉璃珲靠在软榻上歇息。虽时至冬季,燕然因地处大漠,天气依然温暖。加之这里的百姓常年食牛羊之肉,身体并不十分畏寒,故而多数人也只穿了件薄袄。玉璃珲却因为之前的伤,损了元气,既使是此般晴好的天气,仍披了件银狐的大氅。雪白的狐裘,将他整个包裹起来。
过了一会儿,有人上了台阶。丝履轻软,裙裾翩翩,玉珏相击,钗环簌簌。玉璃珲含着笑意,静静的听了一会儿,却并不起身。
脚步声在他身后停下,踌躇了阵,终没了声响。玉璃珲轻笑了声,坐起身来,“箫儿。”转过头,正看见凤箫手上托着个沉香木盘,上面放着一只玉碗。
“黛墨让我把药送来。”凤箫突然觉得局促起来,恢复记忆后,竟有些害怕面对他。
“过来。”玉璃珲却笑着招手。凤箫走上前,将药碗递过去。玉璃珲接了也不喝,只放到一旁的矮几上。
“黛墨说,这药趁热喝才好。”
“不碍的,”玉璃珲抚了抚胸口,淡淡的笑起来,“这伤并不至命,也不急在一时。”说着,伸手拉了凤箫,“箫儿陪我说会儿话罢。”
凤箫点头应了,坐到他身侧。
虽说是说话,两人却静坐着,不发一言。
过了半晌,玉璃珲才道:“你听。”凤箫侧耳,只听到漠上呼呼的风声。“风里,有细碎轻响,像是锦瑟的声音。”凤箫静心听了阵,果然听到风里有些微微的响声,清脆细腻。
“那里有一片蓝铃,”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深黄的大地上,有一片浅浅的蓝色,并不显眼,要细看才分辨得出。
“长期呆在宫里,这般平常的景色也是不易见到的。世人都说,天子至高无尚,享尽世间荣华。却不知,寻常人家的细小幸福,对于君王来说,却是奢求。”玉璃珲转过头来,看着凤箫好看的侧影,看得入了神。
“怎么了?”凤箫回过头,摸了摸自己的脸。
玉璃珲却笑着,将她的手握进自己的大掌,“和你这样并肩坐着,我不知在梦里见过多少回。现在,我却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梦中。”
凤箫拉着他的手,放到自己脸旁,“你看,你摸得到我。”
玉璃珲点点头,“是了。每次梦里,想拥你入怀,梦却醒了。现在,你便坐在我身旁,我摸到你了,你并没有消失。”
“傻瓜。”凤箫笑嗔,两人的眼睛却红起来。
“箫儿,你可怪我?”
凤箫摇头,“有些事,并不是你力所能及的。当年的真相如何,我并不知晓。”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真相,若是不能原谅,箫儿,你可以杀了我,但不要离开我。”玉璃珲等着凤箫的回答,心慢慢痛起来。
“我……”
“陛下。”珀在不远处,恭声奏道。随后便是一阵脚步响,苍玄青拾阶而上,转角便看到玉璃珲正和凤箫坐在一起,不禁呆了呆。凤箫见他们似有要事商议,便站起身来要告辞。玉璃珲却笑着拉了她的手,和她并肩而立。
看着他们握在一起的手,苍玄青眼角轻颤,却很快垂下眸去,“陛下,一切准备妥当。”
“让延楼率大军先行,我们慢慢跟上去便是。”
“是。”苍玄青领了旨,躬身一揖,却看到那矮几上的药碗,已完全失了温度,不禁轻皱了眉头。“陛下的药,还是按时服用的好。”意有所指的看了眼站在玉璃珲身旁的凤箫。
玉璃珲却只是摸了摸胸口,淡笑着道:“方才与箫儿说话,竟忘记了。”
“药已凉了,臣这便唤人热了来。”上前端了那药碗,退了下去。渐渐不见了玉璃珲与凤箫并肩而立的身影。
凤箫看着他缓缓离去,不知为何,总觉得他踏在石阶上的足音,听起来格外悲伤。
北伐的大军还朝时,璟城下了今冬的第一场雪。
素白的雪花,在风中翻飞,瞬间便将天地染成一色。玉璃珲率着一众将士,缓缓进了午门。虽说天气寒冷,但一早道旁便站了许多百姓。即使从午门到凤阙的这一路上早用了黄绸束道,众人仍是翘首以盼,希望能从中窥得圣颜一二。
新帝辰睿甫一登基,便展示出他的不世之才。平静王乱,收胡之地。即便,今上发兵缘由早有种种传言,但众人仍宁愿相信,这便是他们的圣主明君,定能为璋辞带来空前的繁荣。
玉璃珲白马金鞍,一身戎装,行在最前头,珀与宁延楼紧随其后。再来,则是身着玄甲的铁甲骑兵,直属于君主,个个都是万中挑一的精英,也是皇帝的亲随部队。经此番大战历练,各部将士面上多了些沧桑,却脱了早前的士族贵气,显得沉稳干练。无论如何,经历了一番生死,人总要成熟些。接下来,便是三辆装饰华丽的车撵。众人暗自猜测,哪一辆里坐着的是今上奉为帝师的苍玄青,哪一辆里坐着的是令今上冲冠一怒的红颜,也是璋辞将来的凤主,宁家的幺女,凤箫。而另一辆里,又坐着什么人物呢?
众人隔着黄绸,又因圣驾降临,均跪在地上,看不真切。却隐约见到车内人影绰约,似是个女子。听说,胡王有一公主,名曰黛墨,亦是绝色。今上此番征伐东胡,难道……一时间,各种猜测骤起。
玉璃珲一还朝,并未大肆庆祝。而是让众人解甲回乡,与家人团聚。第二日,才发了圣旨召告天下,免各地赋税一年。
“陛下,”苍玄青收了方枕,“此刻看来,那蛊似乎还算安份。只是,若要……”
“先生,”玉璃珲一手止了他的话意,“你知道的,只这一事,我绝不答应。”
“若长此以往……”
“箫儿好容易回到我身边,我怎舍得放手。”玉璃珲笑起来,眼中却有说不出的痛苦神色,“再者,为她,我已弃那几万将士于不顾。”
听他如此说,苍玄青不禁一颤,失声叫道:“陛下!”
“先生,虽说那时我身受重伤,但若我不愿,又怎会如此。”玉璃珲抚着胸前的伤口,轻道:“一切皆因我起。”
“陛下莫要如此说,那计策是玄青定下,那几万将士……”苍玄青止不住全身颤抖,连声音都轻颤起来。
“先生,若无王命,延楼又怎敢妄动。”玉璃珲轻叹一气口,“为了箫儿,让他们送了性命,我却不悔。不过,你放心,日后,我定会还他们一个繁华盛世,以慰他们在天之灵。”
两人正说着,门外传来珀的声音,低低的道:“陛下,李总管来请旨了。”
“让他进来罢。”
李禧禄进得门来,见了驾,便又听到玉璃珲道:“不用急,晚些时候送到宁府去便是。”
诺了声,跪接了那道圣旨,也不多言,躬身出去了。
苍玄青也并不知道那旨上写的是什么,心中疑惑不已。却抬头,瞧见御案上放着的一幅澄心纸上,书有“长信”二字,心中便猜出一二。
“陛下,此事……”
“我为箫儿引兵千里,伏尸累骨,若世人骂我昏庸,我便认了。却也不差这一件。有生之年,若能与她长栖此宫,吾愿足矣。”玉璃珲指尖轻轻从字上划过,面上带着浅浅的笑意,竟让苍玄青看得心中一酸,差点落下泪来。忙躬了身,用那广袖遮了眉眼,低声道:“臣愿,万事皆遂圣意。”
且说,凤箫随着宁延楼回了位于璟城西市的宁府。
远远的,便见那朱门上金书的“宁府”二字,院墙似是比之前长出了好几倍。凤箫暗自皱眉,心道:她名义上是宁府的女儿,将来入主凤阙,再加上此次大战获胜,宁家二子也建功不小。若是扩了家宅府邸,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看这规模,远远超过了城中公卿王侯的制式。且观这院子,落成也不在这两日。怕是,早在御驾亲征之时,便已动工了。忽又想到,一路上听来的碎语,原太子有结党之嫌,宁家长子正是太子太傅……
怕是,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要起了。
几人进得门来,府里的管事早率了一干仆众等在前院。延楼刚迈步进来,门房的小子便喊开了。
“二爷,二爷回来了!”这一喊,竟隐隐带着哭腔。众人都迎上来,还不等说话,便先落起泪来。
“这是怎么来的,我不是好好的么。”延楼笑道,但心中还是生出无限的感慨来。虽这府上家仆他并不熟识,一年也见不上几面。却毕竟他与大哥亲厚,故而大家亦将他当作家主一般无二。
“二哥!”这边话还未说完,便听身后有人喊了句。延楼转过身来,便见一声锦袍的延亭从厅里跑出来。
“啊,四弟。你也到璟城来了么?”延楼上前,搂了搂幺弟的肩膀,笑着说,“多日不见,四弟似乎是壮实了不少。”
“二哥。”延亭却只是复唤了他一声,再说不出话来。
延楼见他这样,轻笑了声,“哎呀,我道只是丫头们爱哭,不想宁四爷也感伤起来了呢。”
“二弟,你在前线,大家都很担心。”这般说着,延阁也跟着从厅里走出来。延楼收了笑意,上得前来,“让大哥担心了。”
“父母亲也忧心得很,派人来问了多次。前些日子得了消息,便遣了四弟来。你也别调侃他了,快些让人到兰城去报个平安。”
延楼应承下来,指了个身旁的小厮,让他快马送信去了。一切停当,便又有童子来请,只换了身衣裳,跟着他去了延阁的漱玉斋。
“日后,你准备如何?”延阁端了青瓷茶盏,细细吹开面上的茶沫,品了一口。
“过几日,今上朝会,我便想向今上奏请辞官。”叹了一声,又道:“只是,武陵一脉也算得上我倾尽毕生心血所为,此番去了,也有些舍不得。”
延阁听了,点头道:“是了。你十八岁上便封了武状元,去了武陵,一呆便是七年之久。再者,你与那些兵士素来亲厚,如今辞去,定是不忍的。”
“不过,我意已决。”
“子夜这般,也值得你如此作为。”延阁顿了顿,又道:“你选择这个时机离去,也是好的。只是……”
“父亲那边,大哥可安排妥当了?”明白延阁意中所指,不免担心,他这一走,家中便少了一人照拂,将来之事,更是艰难。
“老四业已辞官,过几日便会回到那边去。父亲赋闲多时,早不问朝中事。三弟远在燕然,此次又立了大功。再加上……凤箫定会护他们周全。”
“如此便是了。”延楼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大哥心计已定,弟弟便不再多言,只是苦了大哥。”顿了顿,又道,“只是凤箫,将来怕是……”
“将来的事,咱们谁也说不准。有今上在,想来,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伤她分毫。我们能做的,也只在于此。”说到日后之事,两人竟生出无数的悲伤来。
延楼摇摇头,轻叹道:“咱们宁家可尽是些痴情种。”似又想到什么,笑道:“之前说三弟,此次不只是立了功,怕是不日也会娶个不得了的弟媳呢。”便把阵前种种说予延阁听了,兄弟二人都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