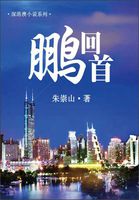夜读鲁迅杂文集《坟》,其中有一篇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文章,是在当时(1924年)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稿,谈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要求出天才”的论调,据说“出天才”的办法之一是“整理国故”。鲁迅对此颇不以为然,我们且看他是怎么评论此事的: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绝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读了鲁迅这篇讲话,我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几年我也写了几篇提倡学国学的文章(国学和国故大概是一回事,当然在争论中会显出差异),而且我确实也是老头子了,但是我这个老头子的“国学”基础却甚差,所以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不要忘弃国学,何况现在青年人的新学问比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讲话时已经多得不可同日而语了,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
但是仔细想想目前提倡国学研究即保存国故的情况,仍觉得未尝完全妥帖。譬如说,现在所谓“国学”是否就等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最早人们提出的是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只能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或一大项。王国维提中国国学的两大源头:一是孔子的学说,一是老子的学说。两千多年来,国学可说是五花八门,头绪繁多,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大体说来,孔子的学说即儒学占上风,有的甚至把它归为宗教类,至少是将“佛藏”、“道藏”、“儒藏”三藏并列。儒学本是入世之学,被历朝历代奉为经世治国之道,但孔子其人早被神化,如今一部分人要把他奉为教主。本来,中国的国学流传到国外,是老子的学说占上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这种情况。
从16世纪起,老子的《道德经》就风靡西欧,那正当西欧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哲学重镇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名家都重视老子。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孔子不在其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传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道德经》。
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儒学被一部分人奉为当今显学。
现在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同样需要我们从古籍中发掘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基因(包括某种理性精神和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支撑点之一,这正是国学重要性之所在。但是,何谓国学,在我国博大的传统文化中,在门类众多的国学领域中,究竟从何处去找寻这种东西呢?这就是很费周折的事了。
听说,现在有的大学已经开办了国学院,在首都就有三四家,而且颇有蔓延之势。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进行选择和安排课程的,据说有的在用心钻研四书五经,《道德经》是否也列在内则无所闻,大概也会有的。重新“整理国故”一事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大学中,这是鲁迅始料所不及的,但鲁迅当年反对“国故派”无疑是对的,我们今天为了继承传统、开创未来而重视国学亦属情理中事,因为时代和目的毕竟不同了。就目的而论,一为了复古,一为了开拓未来,或者说,为了有益于新文化的成长,而非做“国故派”。但是依我看来,要真正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或者真正从国学中学到一些东西,非有现代科学眼光和批判继承的功力不可,仅仅抱着“猎古”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
从目前重视国学(其中又特别重视儒学)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自从共产党当政,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国家的显学,而且上升到了指导思想的地位。但是几十年来经过由几场错误“运动”所造成的国家的深重灾难,特别经过苏联垮台东欧变色的历史巨变,马克思主义的声誉直线下降,特别在青年人中间,几乎到了无人过问的地步,有的甚至公开提出要搞“去马克思主义化”。意识形态就如一座被层层泡沫包围的空城。其实,说空也不空,这几年,每一代领导人几乎都提出了自己的“指导思想”,排起来成一大串,唯独不见了马克思主义。现今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络程度,以及儒学之骤升到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学者已经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源”,马克思主义是“流”。这种说法令人瞠目不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西方学说,它源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的历史学说(其中首次提出阶级斗争思想),以及德国哲学等西方文化土壤及其传统;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首先应当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世界性学说,它要随着世界潮流的改变而更新自己的内容,要适应于时代,绝不可墨守旧说,故步自封。
我们是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事做好了呢?在革命时期在有的问题上可以说做到了,譬如以农村为革命基地,和西方的城市起义传统大不相同。但是,总的说,没有做好,相反,是“左”倾教条主义长期盛行。
过去,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一,是没有真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甚至加以歪曲尤其是片面理解唯物史观而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内争和整人;第二,盲目崇奉“国际”而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第三,由官方独断,不允许自由研究,这就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此三者,马克思主义不能不陷入困境。
现在,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研究,重新认识,尤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性,这将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进行,单由官方设立几个研究机构是远远不够的,提倡独立的、自由的研究更加重要。
由此,我想到,凡热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特别热心创办国学院的共产党人,他们不应以另一种方式重走“整理国故”的老路,不应仅仅以获取国学知识为目的,更不应将儒学重新抬上显学的地位(批判继承是必要的,同时也要有创造“新儒学”的自由),而应当温故而创新,立足于当前的国情、世情,从国故中开出新学来;重要目的之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国情相衔接,尤其要在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哲学(这是国学的精华)中吸取营养,以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切实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而非经典原理学,中国也早有“六经皆史”之古训,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两者适当相沟通是有可能的。不知国学院的朋友们以为如何?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