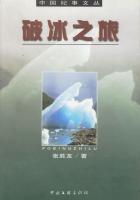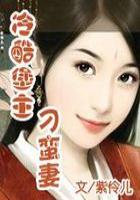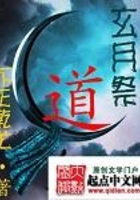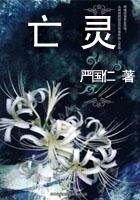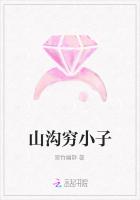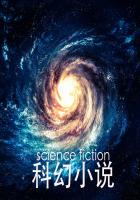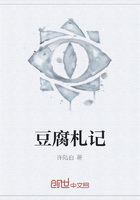这表示,祝是祭祀时以言辞事神的人。由此可知“不歌而诵”源于祭神,用于祭神。《周礼》所载职官,大夫以上均有为王“诵”命或宣诵的职能。以史官为例,周代史官的职务主要为掌祭祀、掌典仪、掌册告、掌记事,而宗伯为之统,他们既是神职人员,又是国家的行政人员。史官的册命文告职能也兼人神两面,既代王宣读文告册命,又代王主持祭祀仪式,并行占卜、祝祷。重视神事的原始性与重视人事的时代性相互结合,互为表里。据此可知,周代史官实兼有巫祝宗卜之事神职能与代王宣读文告册命之行政职能。可以推断,先秦时期对大夫等朝廷官员长于“诵”的赋政能力的要求,与上古时期巫祝卜史事神的特长有关,大约就是由此演化而来。随着神权观念的消退,巫祝等神职渐次退出国家的职官系统,宣诵的技能作为“乐语”也逐步与祭神仪式分离,成为贵族乐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巫祝之官代王宣诵王命的言语技能,成为“大夫”的必备素质,得到提倡和强化。《诗·大雅·民》云:“天子是若,明命使赋。”又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朱熹《诗集传》说《民》之作,是“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从诗的末章也可以看出,这首诗是尹吉甫“作诵”,赞美仲山甫作为“王之喉舌”,“赋”政于外的才能。《传》曰:“赋,布也。”《笺》:“赋,使群臣施布之也”,“以布政于畿外,天下诸侯于是莫不应发。”诗中的“赋”的意思是把王的政令口头传布到四面八方。先秦时代的官员必须具备发布政令必备的语言能力,还可以从对贵族的教育内容中看出其端倪。晚到春秋时期,孔子还以“言语”对作为教育子弟的四科之一。也可见语言能力是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管子·立政》载古代王命的传布,可以看出官员“赋”的重要性,兹引述如下: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早晏之时。宪法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法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诗·风·定之方中》,《毛传》曰:“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布,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有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为大夫的标准是具有在任何场合都能铺陈讲说于民的表达能力。
“命龟”、“施布”、“铭”、“造命”、“赋”、“誓”、“说”、“诔”、“语”九者,虽然说其场合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据其中的“语”属于《周礼》所说的“大司乐”所掌、用以教国子的“乐语”这一事实来看,所谓“君子九能”的实质,都是有节奏的陈述。所以春秋时孔子以“言语”教授弟子,使弟子“诵诗”以明“专对”之学。此外,《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娴与辞令,博闻强识”;《左传》载行人的“赋诗言志”等,都说明“赋”,也即当众演说,诵陈政令,是朝廷官员必备的素质。孔子告诫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班固则干脆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此处的“赋”并非赋诗,还不是文学活动。孔颖达《正义》谓“赋”为“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是不确切的。挚虞《文章流别论》云:“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赋陈其事。”可谓一语破的。三“赋”由铺陈物类、宣诵政令,进而用于各类文章,波及讽谕、娱乐,然后逐渐与文学发生关系。《国语·周语上》引邵公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韦注“瞍赋”一语曰:“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除听政以外,恐也有娱乐的作用,盲人讲诵、说唱故事以资娱乐的现象在各国文学中都很普遍。枚乘的《七发》写远游之乐的一段说登高远望,听“博辩之士”“比物属事”之乐。赋云:“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这里说的“比物属事,离辞连类”的“博辩之士”,实即后世辞赋家。其“原本山川”的技能,则似乎表明他们与上古的巫祝有着某种师承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赋由诵陈政事的政治功能,渐渐兼具了娱乐的功能,这是实质性的飞跃。导致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广泛的运用于先秦韵文中。“格物”、“方物”,就要“铺陈敷布”,略同于叙述和描述。其特点在于直陈。它是文章发轫之初最普及的表达方式,也是先秦文章中用的最多的表达方式。以《诗经》为例,孔颖达说:“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谢榛《四溟诗话》也说:“余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比一百一十。”根据《诗集传》统计,《诗经》共1141章,其中赋727章,比111章,兴274章,兼类29章。赋最多,占637%。足见铺陈敷布本是文章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不歌而诵”是“赋”法的表现形式。早期文章,有赖口耳,故多借“不歌而诵”的乐语形式以利记忆。“不歌而诵”多施于各类文章。春秋时行人的“赋诗言志”,也是不歌而诵在外交场合的一种特殊的运用。因为所赋多为诗篇,所以这一现象对文体的赋的产生起了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歌而诵”,“铺陈敷布”两个特点的“赋”法,本源于祭祀仪式,后来逐渐因为巫祝地位的下移而普及,也是它为各类文章所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先秦文章(包括诸子、史传及诗歌、说理文、民间游戏文等)中赋法的运用十分普遍就不足为怪了。这都是作为文体的赋的源头。战国之际,文体逐步分化定型,这也表现为语体即表达方式成为文体的决定性因素。这时出现了“赋体的诗”。《周礼·春官·宗伯》:“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和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章太炎《六诗说》认为此“赋”是诗体,是通篇以赋为表达方式的诗。《诗序》作者“六义”之说根据《周礼》而出,实质是一样的。因此,有人据上说“赋自诗出”也是有道理的。广泛流行于民间的“隐”体,运用赋法,隐括谜面,揭示谜底。
经荀子之手,隐遂以赋名篇。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肯定荀况在赋的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是符合实际的。就这一点来说,说“赋源于隐”,“赋就是隐语的化身。”“描绘物体的形状和特征,正是隐谜的主要写作方式。”“在隐藏谜底的情况下,于是就‘铺采文’了,‘铺张扬厉’了。”(9)可以说是部分地揭示了问题的真相:即运用了产生于祭神仪式的“赋”法的隐,是文体赋的一个来源。“赋体的诗”的阶段,“赋”在单位篇章中只能描绘一种事物,虽然比起片断的“赋”,容量已经增加,但当面对更为复杂丰富,过程很长、细节繁多的事物时,仍然需要改造自身——吸收“楚辞”的语言词汇优势、游说辞及散文的谋篇布局——于是篇幅拉长,语言进一步文雅化。最终在宋玉、荀况赋为代表的战国赋的基础上形成了汉代的新体赋——大赋。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这一方面道出了“赋体的诗”变为“赋体”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这一转变中“赋”法的变化。赋的两个要素,“敷布铺陈”和“不歌而颂”都较前有了新的气象。前一个特征在“赋体的诗”中只有针对单个事物的描绘,而且只重外貌形状的细部刻划,没有时空整体上的位移。而“赋体”则因篇幅拉长,可以描绘多种事物组成的纷繁复杂的场面,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绵延性。体现出尚多尚博的倾向。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赋博也。古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至西汉以来,诗赋始各有专家。”刘氏此说也已经触及“赋”由原始形态的“方物”、“序物”,演变成为“序物以言志”,即以描写和叙述功能为主,兼具议论甚至于抒情等多种表现功能为赋体。从现代文体学的角度看,一种文体的构成要素中,表达方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以某一种表达方式为主对其他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构成了文体在表达方式方面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质。因此,考察文体语言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主要的表达方式,是揭示文体实质的一个重要途径。铺陈事物的赋法,在祭神仪式上,在《诗三百》中,和在《左氏春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由序列物类,到宣诵王命,再到赋诗言志,体现了“不歌而诵”的赋法由产生于原始宗教,用于政教,并最终演变成为文学文体的过程。注释:(1)参邓国光《周礼“六辞”初探》,刊《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第137—158页。(2)关于赋体本质特征的探讨,可参陶秋英《汉赋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冯俊杰《赋体四论之二——赋体的生命要素》(《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马积高《略论赋与诗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骆玉明《论“不歌而诵谓之赋”》(《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等。(3)裘锡圭《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12页。(4)叶舒宪《〈山海经〉与禹、益神话》(刊《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及《方物:〈山海经〉的分类编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5)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十一云:“助、彻、皆从八家同井起义,借其力以助耕公田,是谓之助,通八家之力以共治公田,是谓之彻。”他的《周彻法名义解》又说:“谓之贡者取以下共上之义……即公田所纳亦谓之贡也。”吕振羽、曾仲勉等学者也认为“贡”、“赋”本相同,“别而为二,只是文字跟着社会发展而分化。”“在赋的方面,农民除去一小部分劳动时间,在自己的‘分有地’即所谓‘私田’上劳动之外,则以一部分劳动时间支付在领主的土地即所谓‘公田’上去劳动。……其次便是农民要向领主提供无定额的贡纳物。……在西周,从《诗经》上所能考出者,为兽皮、猪肉、野味、蔬菜、羊肉等类。”见曾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62页。(6)参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4册,第1194—1197页。(7)日本学者谷口洋《试论早期辞赋中的神怪与悲哀——从“游行”主题看战国秦汉间宗教情感的蜕变》一文认为,汉赋中的纪行和田猎题材,是由远古时期人间统治者或巫祝祭祀神灵的游行宗教仪式演化而来的。该文详细描述了这种题材在先秦到汉代的演变过程,对本文的论述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论文收入《第四届赋学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8)参朱晓海《某些早期赋作与先秦诸子学关系证释》,收《第四届赋学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9)朱光潜《诗论》,《朱光潜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