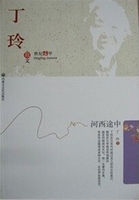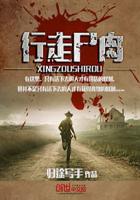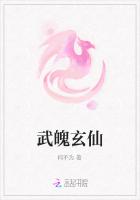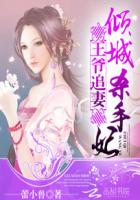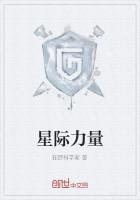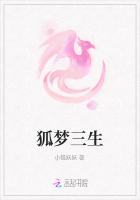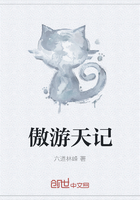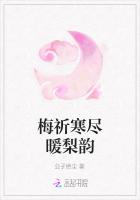君子所履,小人之所视。’”同书《非攻中》引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非命中》引****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战国策·秦策五》引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从以上诸例看,典籍所引的“诗”,有的是韵文,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有的则叙事而带歌颂。牛鸿恩认为上述例中,作者是把“诗”作“志”字来用。结合《左传》、《国语》常见的“志曰”或“志有之曰”的内容,“志”就是记事记言的古书的泛称。(5)《国语·楚语》载楚庄王时申叔时提出的教育太子的功课,内容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和训典。其中的《故志》,王树民先生曾加以考证,他从《左传》中辑出有关《志》的佚文共十四则,通过分析其内容,王先生指出:“大致早期的《志》,以记载名言警句为主,后经发展,也记载一些重要的事实,逐渐具有史书的性质。”(6)前人认为《逸周书》是孔夫子删书之余,其中的《殷祝》、《周祝》等据学者研究,亦为格言警句的汇集,有些还杂有对前代故事的追述。刘起《〈逸周书〉与周志》(7)一文也探讨过这一问题,结论也与王文相近。这给我们理解“诗言志”、“诗,志也”的含义以重要的启示。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在歌乐舞一体化的表演中具有的抒情和娱乐的因素,但这个发展阶段上的“诗”主要被用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朝章国典,是可以肯定的。因此,“诗”辞的内容,一定也与上文所说的“志”相类,具有指导、规范人的行为的神圣意义。这一点还可从文献中对“诗”字的运用和解说中得到证明。《楚辞·九歌·惜往日》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8)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王逸注云:“君告屈原,明文典也。”明言“昭诗”即“明文典”,其具体的作法就是“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也就是说叙述歌颂祖先的功烈来勉励楚人,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富国强民。这是屈原昭诗的目的所在,从中也可窥见:“诗”的本义原是书之竹帛或者说载之口耳的祖先功烈和事迹,以及与治国修身相关的神圣的格言。以其取韵诵的形式而便于记忆,故有“诗,志也”的说法。三“诗”又有“持”义。“持”者,主司事也,即主持某事。孔颖达《毛诗正义》于郑玄《诗谱序》下疏云:诗一名而三训。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饶宗颐先生《固庵文录》有《诗一名三训辨》一篇,据《礼记·内则》:“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及《仪礼·特牲馈食礼》:“主人左手执角,再拜稽首,受,复位。诗怀之……”《郑注》,指出“持”“承”义同,“承”由“持”来。孔颖达一名三训,实为二训。饶先生广引铜器铭文中的例证,详加考证,得出结论认为,在先秦典籍中,“诗”从“手”从“音”从“口”,“寺”声,字形常作“持”、“”,其本义为“治事”、“司主”。《邾公经钟》:“分器是寺。”“寺”训“持”。《广韵》:“寺者,司也。官之所止。”《释名·释宫室》:“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是寺、持之训,有主持、司事之意。(9)在先秦,史主祭礼等仪式上的记事和诵事,因此长于文彩,与诗关系密切。孔子曰“文胜质则史”即是由此立说。前文所引闻一多认为上古之史即是诗,史官即诗人也是如此。从职司上说,巫史是主持专司各种仪式韵诵的主体。白川静《释史》以史为“祭祀祝告之义”。姜亮夫《释史》以为“巫史同为领导庶民辅翼君上之知识阶级”。戴君仁《释史》以为,“史是知天道者”,“史的参与祭典,宣讲符命,应是他的原始任务”。沈刚伯《论语上所说的文史与文学》认为,“史是祝史之事”,史“掌丧祭之礼,撰读祝辞诔文。”(10)以上诸家都认为,史的职掌在于专司祭礼、传诵史志。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据王安石“诗为寺人之言也”的说法,又结合“寺”“志”在形和声两方面的相通,寺人盖由巫、史充任,专司仪式中的韵诵,以记事(志)。从这一意义上说,“诗”原本是具有政祭合一性质的礼仪圣辞,所涉及内容都是带有神圣意义的:简言之,汉语中“诗”的概念与“谣”“歌”等有不同的来源。它最初并非泛指有韵之文体,而是专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所颂之“言”,即用于礼仪的颂祷之词也!虽然《诗经》中的风、雅、颂已均被视为诗,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只有颂才最切近“诗”概念的本义。(11)上面的说法亦可从文献中找到旁证。《史记·孔子世家》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此处以诗三百篇与《韶》、《武》、《雅》、《颂》并举,此雅颂显然不是诗三百篇中的雅颂。《雅》、《颂》与《韶》、《武》一样均为乐舞之专名,说明二体似乎由来已久。后借用以指称《诗三百》中的类似作品。这些作品用于祭礼,载歌载舞,故亦称为雅颂,由其依附于仪式,并体兼乐舞而得名。钟嵘《诗品》:“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正是指“诗”之古义而言。综合以上所说,诗既指在某种仪式上所用的颂祷之辞,又指巫史等以口诵方式于祭祀礼仪上诵读祝颂之辞。四总括文献所述,颂诗的功能主要在于:一、历述祖先的开国创业之功勋,以垂范后人;二、辨昭穆世系,强调族内的等级关系,借对天神和祖先的祭祀维护人间宗法制政权的统治;三、歌舞的娱神而祈求福佑。(12)但当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颂诗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条件发生变化时,先秦诗歌就由颂的阶段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即“辞”的阶段。以屈原辞作为代表的一组作品足以代表这一阶段的诗歌在总体上的特征。这个问题,宜于从对一个相当熟悉,而又长期为人所误解的观点的辨析谈起。这就是孟子提出的“诗亡于春秋”说。《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对这里的“诗”指什么?“诗亡”的原因,古今学者作了种种解说,但皆未达乎一间。举例来说,如明代学者焦《焦氏笔乘》卷四,“诗亡辨”条云:窃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自昭王胶楚泽之舟,穆王迥徐方之驭,而巡狩绝迹,诸候岂复有陈诗之事哉?民风之善恶既不得知,其见于《三百篇》者,又多东迁以后之诗,无乃得于乐工之所传诵而已。至夫子时,传诵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尽著诸国之民风之善恶,然后因鲁史以备载诸国之行事,不待褒贬而善恶自明,故《诗》与春秋,体异而用则同。(13)从上文可见,焦氏理解的“诗”显然是指包含了先秦“歌”、“谣”及《诗经》中风、雅、颂在内的所有的诗歌。他的诗歌的概念是诗歌走向独立后的诗歌观念。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孟子所说“诗亡”是指王者巡狩采诗制度之亡。按:巡狩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事,实专指风诗而言。既然《诗经》中多为东迁以后诗,孟子又怎能说诗亡于东周呢?焦氏对于“诗亡”原因的揭示并不符合先秦诗史的真实。还有顾镇《虞东学诗》卷首《诗说·迹熄诗亡说》亦云: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狩述职;巡狩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师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诗亡也。焦、顾之说实有所本。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卷四云:“《孟子》‘王者之迹熄’,‘迹’当作‘’,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均以此处之“诗”为《诗三百》篇。
从先秦典籍中所载的逸诗和歌谣的数量之多这一点来看,广义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停止。难道是孟子错了吗?事实上,先秦典籍中主张“诗亡于春秋”说的,并不止孟子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观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我们对孟子所说的“诗”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孟子所说的“诗”,实指“颂”。《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歧注云:“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颂声不作,故诗亡(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孟子身处战国时期,他认为东周时,真正的诗已经亡了(“诗亡然后《春秋》作”)。那么,在他的观念中,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国风,显然是不属于他所说的“诗”的范围的。他所承认为诗的,恐怕只能是颂和雅了。今观颂和雅,多出于周公、召公等政治上和国家祭礼上有绝对权威的人士之手。他们都是王政的维护者,宗教典礼的主持者,他们所作的诗——在祭礼及其他仪式上所诵或所发的“言”,是与王道密切相关的,因此孟子才将“诗亡”与“王者之迹熄”联系在一起。颂的衰亡,从其形态来说,主要是其乐舞因素的衰亡。而乐舞因素的衰亡是由颂赖以存在的礼乐文化的衰亡所导致的。周室东迁以后,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周天子的权威动摇了。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认为:春秋战国之交,世风大变,才是造成“诗亡”的重要原因。他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14)作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工具的礼乐制度被打破了。颂诗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政治文化土壤,不再占有主导的地位。另外,仪式文化在理性精神普遍出现的时代,逐步地走向世俗化,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新的仪式。在这个过程中,其原有的神圣性、禁忌性减弱,相反,原本就存在于仪式之中的狂欢性、大众性逐步增强。这样,依附于仪式的颂辞,就分化为各种形式的韵文文体,如“昭穆”、“系世”之演为史诗,敬授民时的月令之演变为农事诗,各种禁忌及宗教伦常之演变为社会道德规范等。再往后,仪式与仪式颂辞间的关系变得松散,颂辞脱离乐舞,只以文本的方式存在,进入到以辞为用的阶段。注释:(1)郭绍虞《谚语的研究》,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2)刘师培《论文杂记》,舒芜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1月版第110?—111页。(3)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言》,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第140页。(4)《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卷,第11页、12页。(5)牛鸿恩《〈战国策〉等书“诗云”臆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6)王树民《释志》,载《文史》第32辑。(7)刘起《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8)此句之“诗”,洪兴祖《补注》引一本作“时”。朱熹《楚辞集注》本作“时”,引一本作“诗”,注曰“非是”。游国恩《楚辞讲录》认为:“今按作‘诗’者是也。王《注》:‘君告屈原,明文典也。’是古本作诗之证。《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说:‘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尝疑《九歌》为怀王时祭祀鬼神之歌,所谓‘受命以诏诗也’。”(9)饶宗颐《固庵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10)以上释史诸篇均转引自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文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2月。(11)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12)参拙文《颂为仪式叙述说》,刊《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13)(明)焦《焦氏笔乘》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14)《日知录集释》,(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67页。